(阅读提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中华民族最出类拔萃的一批人,有胆识,有才华,有接受新思潮的智慧,有对中国救亡之道的深刻思考。从曾妈妈和她战友的身上,我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岳母曾志于1926年入党,第二年就赶上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湖南则是“马日事变”中对共产党员的凶残大屠杀。她参加过湘南暴动、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保卫黄洋界、大柏地决战、古田会议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原型”——这些人的理念、追求、操守以及个性中的共性,即使在后来的和平生活中,也一直保持原先的样子。时移事易,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员当然是与时俱进了,不过,略做回溯也会给今天的人们很多启发。
老照片
头一次看到的曾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是她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的留影,我还听说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生离死别去照相馆拍下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的相片被当做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照片中的她天生丽质,一副出自书香门第淑女的气度。看看这幅照片再想想她所处的环境,令人震撼也引人浮想。
照片上,曾妈妈的青春靓丽与当下花季时尚少女别无二致,衣着发型也够时髦。如今的年轻人在物质繁荣的氛围中各有追求,其中也不乏热血青年,但死神的阴影毕竟离他们很遥远。而70年前的这位美丽少女,却自愿选择一条血雨腥风的道路,其间巨大的反差难道仅是由于时代相错,一者生于乱世,一者恭逢盛世吗?
那时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有时敌人由前门冲进来,她翻过后墙脱逸。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被俘,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二十多岁时的曾妈妈比不少同龄人似乎更加成熟,智勇双全。她曾身揣双枪飘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也曾在国民党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宴席上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分析天下大势,即使被怀疑也拿她无可奈何,根据是“只有共产党才这么能干”……
1928年的湘南赤潮中,曾妈妈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全身包红。当我听到这个传说时,笑着对陶斯亮说:“不论用当时或今天的眼光,曾妈妈都够‘酷’的!”
我见到曾妈妈时,激扬澎湃的岁月已成为过去。曾妈妈又经历了“文革”的丧夫之痛,以及协助胡耀邦为全国重点冤假错案平反的巨大操劳,她已满头银发,身体羸瘦,却神清气闲,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
不等价
1983年秋季的一个傍晚,吃过晚饭,曾妈妈对我说:“理由,你有时间吗?跟我去招待所后面的工地看看。”黄昏散步是曾妈妈的习惯。这阵子,她住的四合院,因为老房子装修翻新,就和家人临时安顿在招待所。
我和曾妈妈走出招待所,沿万寿路向北走去。暮霭渐渐降临,眼前的景色也变得荒寂。我们走到一片菜地前,她向前一指,说:“你看那里在盖房子!”我跟着她踏过田埂,经过几座荒芜的坟头,看到矗立着几栋尚未竣工的建筑物,低矮的四层楼,简单的砖混结构。至此,我仍猜不透老人家的意思。
曾妈妈笑着说:“我问过了,这是中办搞的。这里离亮亮上班的地方很近。我想把南长街的四合院交上去,把家搬过来。你也可以把作协给你的房子换到这里。你看好吗?”
我恍然大悟。当时陶斯亮是空军总院的医生,这里的确离她上班的地点很近,骑自行车只需十来分钟。而我此前也曾向曾妈妈表示,我是文人习性,不惯于人多热闹。看来曾妈妈把我的话也当回事。但这是一桩多么不对等的交换啊!
回看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城市建设的格局,万寿路是相当偏远的郊区。作协给我的房子比万寿路要方便。再说,曾妈妈的四合院和单元楼又怎么比呀?那是两进四合院,西靠中南海,东向紫禁城,离天安门只有举步之遥。在既定观念中那里似乎更符合陶铸遗孀的身份和中组部正部级待遇。
我能理解曾妈妈的思路。她一向替别人着想,对规格待遇之类的观念十分淡泊,心清似水,净无杂尘。时值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她有刻意走向平凡的深思。出于对岳母大人的尊重,也出自我喜欢清静,对这桩稳亏不赚的交换当即达成共识。我踩着田埂说:“这个主意很好哇!”
但这次换房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长久。几年后,陶斯亮调至中央统战部工作,上班路途遥迢,反倒离原来的南长街只隔一个街口。而我也去了南方,面对新的环境。曾妈妈在万寿路长住下来,安之若素,其间中办请她搬至好一点儿的楼区也被她婉拒了。
布口袋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中顾委被认为权倾一时,但她只是去开开会,听听文件,平日很少再谈政治,而专注于家务。家中开门七件事,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副食品。于是,不支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曾妈妈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摊位绵延不断。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既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使然。这么一来,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上世纪80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女婿似乎宽容一些,我也当真骑车跑过几趟,可惜这样的心血来潮不能纳入曾妈妈的“计划经济”。
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二十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为脑震荡。
休养时我和亮亮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
曾妈妈已是古稀之年,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纸半张
曾妈妈晚年的风韵曾被许多人描述过。业余诗人说“岁月沧桑没有抹去她年轻时的妩媚”,专业诗人说她“纤柔秀丽,优雅脱俗”。不过,试图从家居布置中找到与她气质相协的审美情趣将很失望,真是乏善可陈。
她的家居更像历经沉淀后去精存芜,杂乱无章的劫后幸存。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印子,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这时我想到,应该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亮亮告诉我,那样结果一定是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桌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桌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岂止半块桌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两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两个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不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在笑吟吟的婉谢之余只差一句话:谁要送礼就跟谁急!
工资袋
我少年丧父,青年丧母,那时经济环境不太好,我一直为自己未能尽孝而内疚。与曾妈妈相处后,按照中国的传统,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也想藉此作为心理补偿。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
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亮亮听了已哽咽难言。我理解医生的压力,也心怀救母之切,镇静下来对医生说:“这位老人很坚强,她一定会配合治疗,请医生尽其所能。”
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而我在南方的工作处于胶着状态,便开始了北京与南方往而复返的不尽航程,每次都拖着整箱辅助化疗的进口物品。为了方便看曾妈妈,我索性不回万寿路,径直住进离北京医院最近的新侨饭店。见了曾妈妈第一句话是问她想吃什么,然后就和司机去找餐厅等着厨师烹饪。然而,这年春节她说了一句话令我难过好一阵子:“理由,我对不住你,让你们春节也没过好。”我觉得这话太见外了,亮亮则说是因为妈妈什么时候都替人着想。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此前有六十多位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感慨万千。这些年去过许多国家,对信仰的理解多了一些角度。在西方人看来,信仰是安顿灵魂的地方。当有人问到你的信仰时,最害怕的回答就是没信仰,对方将一脸茫然。只要你说出不论什么信仰,就给对方提供一个框架,就会轻松地与你沟通。曾妈妈真把信仰当作她安顿灵魂的地方了。
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曾妈妈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我想: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著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显庄严。
(摘自《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和我的父亲陶铸和母亲曾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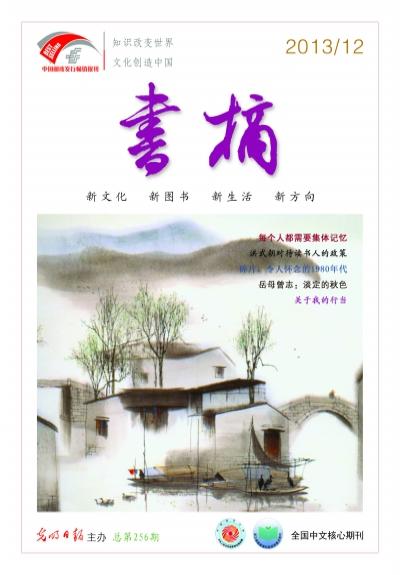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