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简单的心
她在超市门口卖糖炒栗子。
好几次,我经过,她都站在摊位里,忙碌地招呼顾客。
有一回,我买她的栗子,瞥见她靠在一旁的拐杖,我再看她的腿,这才发现,她有些残疾。
她的拐杖,靠着墙。拐杖头是皮革制的,里面鼓鼓囊囊,塞满了海绵。我见过许多类似的拐杖,只不过她的不同,她的拐杖头上蒙着一个布套。
“也许是夏天汗多,包着布,就能经常拆下来换洗?”她殷勤地给我装栗子,而我正琢磨她的拐杖。
几天后,我在公交车上碰到她,她撑着拐杖。
她穿一件水红色的衬衫,领子处垂下两根飘带,在胸前打成一个蝴蝶结。
我看着她,总觉得她有哪里很特别,我再仔仔细细打量她,这才发现,她拐杖头上的布套是水红色的。
今天,我去超市,特地经过她的摊位,她的拐杖仍靠在一旁。
今天,她穿一件豆沙色的上衣;今天,她拐杖上的布套是豆沙色。
她正给一个顾客称斤两,脸冲着我微笑,有人对她说:“大姐,给我半斤糖炒栗子。”她“哎”了一声,嘴上答应着。手也没停,从电子秤上拿下装满栗子的纸袋递给前一个顾客,收钱、找钱,动作流畅。
我说:“我也来半斤吧。”
我于灯下,捻着一粒冷却的栗子,又想起她的拐杖。
现在这个时间,她快睡了吧。
睡之前,也许她要做个面膜,也许只是拿吃剩的黄瓜擦擦脸,她会准备好明天摆摊要带的东西,明天要穿的衣服,相同颜色的布套,明早起来就要给拐杖套上。
当她躺下来,安心入睡,她精心导演并亲自出演的一天已经落下帷幕,而明天,她还会一丝不苟于每个细节,用她认为美的方式,她有好多美的秘密,那拐杖也不过是其中之一。
人生总在告别
1996年,我读高三。临近高考,为放松,班里组织了一场毕业晚会。
我们聚集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舞厅,彩色球形灯在头顶亮起,同学们一个个走上台表演节目。
一个男生说:“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就给大家念首诗吧。”
“十几年前,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但是我很感谢,他笑得真好。”
显然,男生有备而来,朗诵完《一笑》,他向控制音乐的同学使了个眼色,瞬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充斥整个房间。男生说,快要分别了,再见也许再也不见,只希望十几年后,大家想到彼此时,还有“一笑”般温暖的记忆。
如果说此前我们还在嘻嘻哈哈,《送别》歌毕,我们集体沉默,进入了将要离别的伤感情境。再然后,不知谁先开始,我们渐渐哭成一片——那一天也成了我心中的毕业纪念日。
我没和那男生说过话,毕业后,他和大多数同学,我也真的再也没见。
后来,我在一本白话诗选中翻到《一笑》,“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如在耳边,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与离别相关的惆怅。
这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但很快就要离开。两年的朝夕相处,我和学生们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亲密无间,如何说再见,我想了很久。
一天,上完课,我对学生们说,我要走了,并复制了高中毕业时的那一幕:“我也许不会再见着微笑的你们,但是我很感谢,你们笑得真好。”我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送别》潺潺流出,学生们跟着我唱,“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有女生掏出纸巾按住眼睛。
过了不久,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发现桌子上有一个玻璃瓶,瓶子里装满五角星,每个五角星打开都是一张纸条。其中,一个孩子写道:杨老师,真舍不得你走,道一声再见,再见也许再也不见。
我有些难受,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我们总在告别人生的某个段落,总在告别一度同行的人。
想起以上两件往事,我正在朋友父亲的葬礼现场。
满眼是花圈、鲜花和挽联,如果说有什么特别,那便是来吊唁的人,大多头发花白、风度翩翩——朋友父亲是个人缘很好的科学家。
葬礼还没开始,人们聚在走廊下。
我站在一角,听老人们叙旧。
有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与朋友父亲一起上大学时的情景;有人提起30年前曾与朋友父亲合作一个项目,“七人小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
我对着手中的生平简介,判断他们曾出现在逝者的哪个人生段落;我仔细捕捉他们的语言,听得最多的是“好久没见”——既是和彼此,也是和逝者之间的寒暄。
哀乐起,听司仪指挥,我和众人鱼贯而入,献花、鞠躬、与亲属握手,刚才还聊着的老人们此刻脸色肃穆,满眼是泪。
“张大姐!”我步出吊唁厅,见一位拄着单拐的老者向穿深蓝毛衣的同龄女士招呼道。
“小李!”女士神色悲怆,此时却又有些惊喜。
“来送送老佟。”老者道,老佟即是朋友父亲。
“还能最后看老佟一眼,”女士叹息,“老齐、老江,我连送都没送,再见就再也没见。”
记忆的阀门被撞开,自己曾经历的一幕幕生离与眼前的死别交错、集聚。
这是人生吗?
我们一再告别生命中的某个段落,告别一度同行的人,道着再见。
我们在目光中远行,又目送他人离去,最终都等来彻底的告别,在这个世上,再也不见。
“张大姐,我送送你。”老者在我前面,撑着拐。“好,下次再见还不知什么时候呢!说不定是你来‘送’我。”女士感慨道。
哭声、哀乐在我身后继续,“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关于人生关于离别,我竟无端有些苍茫感。
认识最久的人
一个朋友,很久没见了,彻底失去联系。
有时候,我会想起他,在百度上搜他的名字,无奈,名字太普通,如潮信息中,我总分辨不出哪条是他的。
我们失散五六年了。
一日,我收到一封邮件,他发来的。说来传奇,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我写的文章,其中一个细节只有我俩知道,于是,他认定那个笔名后藏着一位故人,他再百度那笔名,找到我的邮箱。
然后,我们发现竟一直生活在一个城市:再然后,两个人穿越半个城,在暴雨天约着见面。在彼此生命里,我们都曾出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失散,大概是太赶着去未来,大概是身边的人太多,无暇刻意留住谁和谁的友情;“有一天,我拨你的手机,发现停机了,这才发觉很久没有联系了。”他说。我挠挠头,“我也是。”
分别时,我们相约不会再轻慢对方,一个人感慨:“在这个城市里,你是我认识最久的人。”另一个人心里有点酸。
一个朋友,很久没见了,联系方式都在,只是她都不用了。
比如电话,从来都关机,比如QQ,头像永远不亮,就这么一去三年。
这个夏天,一个晚上,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条私信,只有四个字:“是我,蔷薇。”蔷薇也不是她的真名,是当年学校论坛上,她的ID。我迅速点击鼠标关注她,我想起2004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围着一张大圆桌,隔着一堆人,我把ID和真人一一对上后,惊喜地喊着“蔷薇”、“蔷薇”,还频繁冲她举杯。
第二天,在一间幽静的茶馆,我们鸡一嘴鸭一嘴把这些年发生的事交代了个遍。她突然放下筷子,她说,她离婚了,早在三年前。
玉容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
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人间蒸发,刚想安慰,她却挥挥手,“那段时间,我有点自闭,现在走出来了,要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找回来。”她眨眨眼,给我看手机里新男友的照片。
一个朋友,很久没见了,联系方式十年没变,可我总疏于联系。大学时,我们是彼此的影子,毕业后,她回家乡,我去异乡。起初,我们通电话就是几个小时;渐渐地,过年过节群发短信时,对着通讯录,我才意识到她还在。
其实,一年总有一次,我回老家会象征性地约她,但我的老家和她所在的城市隔着几小时的车程,我们约了又约失约再失约,几个小时拖了八年。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是谁?我第一反应想到她。
又有一天,午睡,白黑甜的梦乡醒来,我拍着床板,突然觉得她会答应,她还在我身下的铺位。
再回老家,我们再约,时间、地点再一次难以调度,她说:“要是太忙就下次吧。”
“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是谁?”
“要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找回来。”
我想,别下次了:转身去了长途车站。
来回七个小时,相处的时间不到五个小时。五个小时里,我忙着见过她的丈夫、儿子,在她亲戚开的饭馆里吃饭,听她说才带完的高三,一切都平静、琐碎得像昨天才分开。
直至临别,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只剩我们两个人相对,我没来由地说:“这辈子,我除了我老公就只有你。”她静了一会儿,应:“我老公听说你要来,换了好几件衬衫,他知道你对我很重要……”
那天,于归途,我短信她:“从未失去,却总感觉又把你找回来。”
当是时,皖南一片烟雨,大巴穿行在层峦叠嶂间,我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翠绿变成墨绿。
我想起写在杂志上的旧事,与旧事相关的故人,“在这个城市里,你是我认识最久的人”——他的感慨。
我想起蔷薇,想起许许多多,在一路狂奔,一门心思往前奔的日子里,我不知不觉丢了,当时当地丢了也不以为意的朋友们。
年轻时,我们深信一期一会,用“滚石不生苔”、“随缘”解释一切不够珍惜的行为。
渐渐地,生活稳定,总有一个瞬间,我们想看看来时路,却没有参照物;想回忆自己最初的样子,可共语者无二三,连自己都有些迟疑。
于是,那些丢掉的老友、陈年的情谊成为维持内心平静、稳定的针剂;找到他们、被他们找到,就像回归一种原本我们就属于其中的秩序,又温暖、又心酸;念旧、恋旧、怀旧,把“旧”圈在身边,越旧、越久,就越踏实、越安全。
大巴在山区曲曲折折、兜兜转转,我打开手机,更新微博:“要像燕子衔泥般,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找回来。”
少顷,有人回:“可惜,我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丢掉了。”
呵,关于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做着类似的事吧。
(摘自《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32.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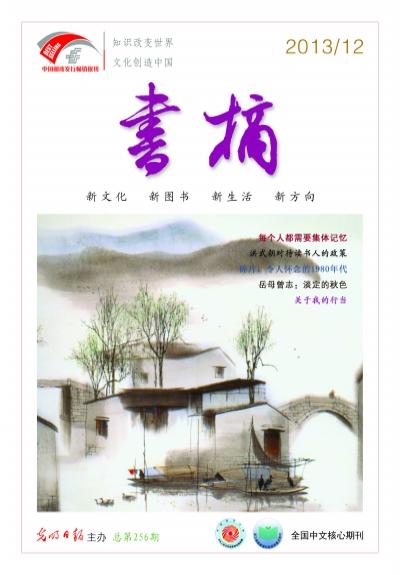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