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文坛为之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80年,丁玲忽然间对老朋友沈从文进行了不点名的公开批评。
上世纪20、30年代,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二人关系密切,曾在京沪两地同住,一起编刊物《红黑》,堪称文坛“三剑客”。1931年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甚至以丁玲丈夫的名义,冒着战火危险,护送丁玲送子回故乡常德。1933年,丁玲被捕失踪,沈从文参与营救呼吁,在听到丁玲已死的消息后,又在《国闻周报》连载传记作品《记丁玲女士》(后以《记丁玲》为名由赵家璧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沈从文一向被认为温和,且不赞同胡也频、丁玲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式,但他仍然在作品中正面描写丁玲与胡也频的社会活动,抨击国民党当局杀害胡也频和丁玲。后来证明,丁玲未死,艰难度过几年的软禁生活后,她只身逃往延安,旋即成为革命作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沈从文不是“右派”作家,但他早就被视为与左翼文艺相异的代表性作家之一,1948年郭沫若发表著名檄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被列入了遭受猛烈批判的行列。1949年春天,在经历了刻骨铭心、死去活来的一次波折后,沈从文淡出文坛,倾心于古代服饰史研究。后来,他虽偶尔参加文坛活动,与文坛的大小风波、左右旋转基本无关,与丁玲被打入逆境,更没有任何关联。丁玲平反复出不久,将他拿出来作为第一个直接批评的具体对象,的确令知情者为之诧异。
黄永玉先生告诉过我,是他在1980年3月给表叔沈从文送去一本新出版的《诗刊》,上面刊发丁玲《也频与革命》一文。在纪念胡也频的这篇文章中,丁玲对沈从文将近五十年前创作的《记丁玲》进行严厉批评:
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些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三期)
在1981年发表的另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中,丁玲仍不点名地讥讽沈从文是“绅士”、“准绅士”:
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他不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涌上浪头,但却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提着脑袋迎上去的,绝不后退。难道这是盲目的吗?难道这应该被讽刺为简单无知吗?
(《胡也频》,《文汇增刊》,1981年第一期)
从一开始,丁玲就很清楚,自己的文章将伤害对方,对沈从文会是一个打击。可是,她仍决定这么做。《也频与革命》尚未发表时,她在写给出版过《记丁玲》一书的出版家赵家璧信中,称自己是怀着恻隐之心来写这篇文章的:
你对《记丁玲》的态度和办法,我觉得很好。我的确想写一篇文章逐点加以改正。而且应该在沈从文在世的时候,否则后人会说沈从文以为你死了(他写这书时正是谣传我已经死去),胡诌了你一顿,你又在他死了后才来改正,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呢?可是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近年来因为他的古代丝绸研究有了点买卖,生活好了些(也还是不那么满意的),我的文章的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或许有点不人道。我是以一种恻隐之心强制住我的秃笔的。最近在给《诗刊》写了一篇短文《也频与革命》,稍稍点了一点,说这篇《记丁玲》是一篇坏小说。不过其中另有一点,仍将在某一天说清楚。以后再看吧。
(丁玲致赵家璧,1980年1月27日)
陈明先生也谈到过1980年发生的这一幕:
那一年,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们,见面几乎都要谈到这本书,他们把这书当作是研究丁玲的第一手材料,是丁玲、胡也频少年时期的挚友沈先生写的,当然是权威著作。他们从书中某些情节,引出来一连串的问题。这促使丁玲考虑,应该写篇文章,指出书中失实之处,以正视听,防止以讹传讹。但顾及沈先生的健康和情绪,她一再犹豫,没有动笔。过不久,《诗刊》要选发胡也频的诗,约丁玲写一篇文章。1950年,丁玲曾写《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详细记述了胡也频烈士在短暂一生中的苦难与光荣。《诗刊》的约稿,引起了丁玲更多的感慨。她想这次的文章,应该准确地阐写也频和自己与革命的关系,澄清《记丁玲》一书中散布的错误和影响,但这必然会碰到沈先生。该怎么办呢?她又一次犹豫,又一次沉思。最后她决定了,写一篇短文,并不对沈先生逐条批驳。同时,她更认为,文章既然要碰到沈先生,就应该趁沈先生健在时公开发表,明人不做暗事,以便沈先生有不同意见可以表明,而不应等到别人百年之后才说出去,使人无从申辩。
(《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原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也频与革命》发表后,丁玲将该期《诗刊》寄给日本汉学家中岛长文夫妇——几个月前,正是他们送来了《记丁玲》。丁玲在写给中岛夫妇的信中,称自己“没有更多地批评”沈从文:
寄上本期《诗刊》一册,其中短文《也频与革命》,是在读了你们给我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后而写的。沈先生早年曾是我和也频的朋友,但因他抱有的思想、立场和我们的不一样,他是不能正确理解我们的。对此,我并不苛求。不过他不应该在传说我被害之后, 以我们为题材,胡说八道地编撰小说,这种近似造谣的行径使人感到不快。因为沈先生年事已高,现正专心从事文物研究,我不愿以过去的旧账,影响他今天的工作情绪,我在短文中并没有更多地批评他。
(丁玲致中岛长文夫妇,1980年4月)
不管如何,丁玲与沈从文的友谊彻底决裂,在两个人的晚年发生了。
沈从文的反应可想而知。面对丁玲的尖锐批评和指责,沈从文为之惊讶。他不解,他困惑,继而气愤。他不相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从未看过他这部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尤让沈从文委屈、也令外人不解的是,二十多年来,对丁玲的身心打击最厉害的,是1955年、1957年审查她、将她打成“右派”的人。知情者也为之不解。与丁玲有着历史纠结的那些人,如周扬等,如今仍活跃在文坛,丁玲不去批评他们,为何反而转过身,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沈从文?
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往远处延伸,可以发现,丁玲以对沈从文的批评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有着某种必然性。
作家林斤澜先生向我讲述过他亲历的一件往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在京召开,被打成“右派”但仍保留着中国作协理事身份的丁玲,出人意外地受到邀请,从放逐地北大荒回京参加大会。会议期间,中国作协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举行过一次作家联谊会,就在这一会场上,林斤澜同时看到了沈从文和丁玲。
林斤澜看到,仍然身处逆境的丁玲,在昔日熟悉的京城文坛人群中,显得孤单寂寞,人们几乎都不愿意与她交谈。只有老舍在休息间歇,主动走过去与丁玲寒暄。似乎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的麻烦,寒暄时,老舍特地提高声调只是询问丁玲的身体如何,北大荒的气候如何。老舍的问候虽然简单,却让一直受冷落的丁玲,一下子异常兴奋,开心地笑了。
沈从文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与丁玲寒暄。散会之后,丁玲去公交站等车,这时沈从文从后面急忙赶来,他的家正好就在东总布胡同附近。林斤澜走在他的身后,也准备去等车,他不便离得太近,只是在不远处注视这一幕。在向我讲述时,他以一个小说家特有的细节捕捉能力和敏感,回忆和分析目击的情景——沈从文脸带笑容,热情地谈着什么,眼睛一直看着丁玲,显然表露出一种关切。是询问北大荒的生活?是邀请丁玲到家中一叙?……详情无法得知,但可以断定是沈从文关心着丁玲的近况。可是,丁玲此刻却丝毫没有老舍与她寒暄时的那种兴奋,她始终板着面孔,而且不大愿意和沈从文交谈,眼睛不时望着别处。随后,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在沈从文与丁玲的交往过程中,林斤澜所见虽只是一个细节,却颇能反映出当时情形下各自的心态。除了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个人恩怨之外,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丁玲看来,她尽管被打成“右派”,但她和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沈从文,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来自老舍的问候,她会感到兴奋;来自沈从文的关心,则另当别论。即便身处逆境,她依然有着清醒的政治意识,不屑于同革命阵营之外的人表现出亲近。换言之,即使她蒙受冤屈,她也不会将自己视为与沈从文一样的“天涯沦落人”。
林斤澜的回忆,足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读,在1980年新的时代转折之际,丁玲为何会借对一位老朋友的指责,来彰显自己的革命性。“右派”之冤屈,加深着她心中之痛,心中之痛,必须借对革命的热情拥抱来化解,从而证明自己的历史清白。
丁玲的指责,对沈从文无疑是意外一击。在写给徐迟的信中,他曾私下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
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料,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篇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地做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丧失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
(沈从文致徐迟,1980年7月2日)
除表示不满之外,沈从文还在信中说,因为他在《记丁玲》中用不少笔墨描写了冯达(出卖丁玲并与之在南京同居),才招致丁玲的指责。他说道:“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这一分析,与丁玲遭遇的历史审查两相参照,似乎可以对丁玲采取言说心中之痛的方式,多了一份理解。
两个人的关系自此彻底破裂。他们只是偶尔在公众场合见上一面。沈从文说过,他是尽量回避丁玲,不愿意与她出现在同一场合。在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们相遇了。沈从文说,丁玲特地走过来找他,邀请与她同桌吃饭。沈从文谢绝了,宴会结束时,才和丁玲握手告别。沈从文后来解释说:“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但是面子上我还是照顾她了。”(转引自周健强《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
自这次宴会后,沈从文与丁玲不再相见。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华来到北京,有关方面宴请招待,凌叔华提出请30年代的两位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婉言谢绝,凌叔华只好随后单独前去拜访。
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谁是谁非,难以说清。即便我前些年曾写过一本《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试图详细描述其中的历史缘由,但我深知,恩怨真相与人物心理,旁人永远不能了解透彻,梳理清晰。不过,此刻,当书写上世纪80年代文化记忆时,在动笔描述丁玲晚年做出“向左走”的选择时,我觉得不妨从丁玲指责沈从文的意外举动入手,来理解这一选择的背后,一直隐藏着的、困扰不已的历史之痛。
痛,在心中,到底该如何言说?
(摘自《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7月版,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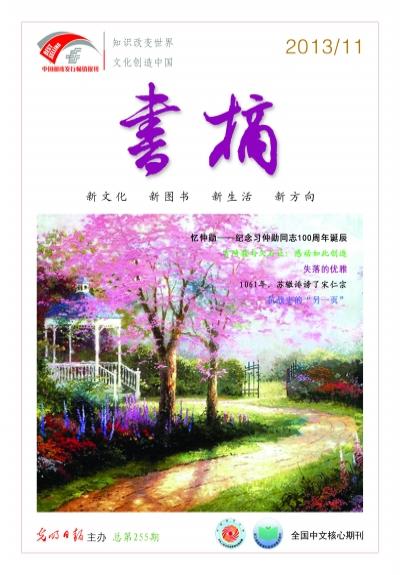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