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竹光浮砚春云活,花气薰衣午梦轻。”竹影婆娑,忽明忽暗的映照在茶几上,窗外不时飘来的花香与鸟啼,唤醒了喜欢晚起的主人……这句诗是对中国古代文人闲情逸致的典型描绘,他们在琴声花气中养活了一团春意思,在顽石纸砚中寄托着一个个迷离的幻梦。
琴 曲
琴曲的好,犹如文章。
庄子写文章,仿佛拿笔在虚空中画圆,上下纵横,不滞于物,却又汪洋恣肆,清虚寂然。司马迁笔底奇气是为人有骨鲠,气厚而雄。韩愈的本事是无话不能把入文章,结构精研,恰到好处,尤其善于说理。可我偏生不爱听人说理,对于韩文,多读几篇,便再也提不起兴趣。魏晋南北朝人的文章我喜欢读,周作人认为六朝文章的妙处是“六朝人是乱写的”,并举《小园赋》中“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为例。风樯阵马的行文里,不经意放一笔,淡悠悠,用心似不用心,整个便一下活了。
琴曲也是,传统名曲,听《平沙》,觉得仿佛是读两宋文章,或赏龙泉青瓷,雅致素洁,渲陈有章,精于转折开阖,莹然有纹理,犹如釉面上鳞鳞有开片。听《广陵散》,类似《史记》里的列传,叙事铺垫,曲折回环,至高潮处,心里被陡然揪起,跌宕欲摧,为之惊骇。《阳关三叠》我不喜。《梅花三弄》刻意表现梅花的清,略嫌做作。倒是管平湖钩沉打谱的唐写本《幽兰》曲,声微而意远,淡宕幽邃,静夜里听来,仿佛读六朝人文章。
古琴曲里我喜欢的还有《阳春》。
《琴史》曰:“刘涓子善鼓琴,于郢中奏阳春白雪之曲。”明人杨抡《太古遗音》说此曲:“师旷所作也。昔天帝使素女鼓五弦之琴,而奏阳春,故师旷法之而制斯曲。盖取万物回春,和风淡荡之意。想其青帝司晨,细柳拖金,春光始漏泄矣;既而满山黄碧,万卉芳芬,春色弥宇宙矣。人际斯时,或借童冠,或抱瑶琴,或张油幕,或驾兰桨,虽所乐不一,其与物同春之趣则均耳。”但我更相信此曲是后人伪托,或是后来经六朝唐宋人修润过。
石 语
石不能言,它们会说话。说些造化中的奥妙微义、日头下的天地玄机。
秋日午后,斜阳下的那些鸟儿,站在院子里竹丛边湖上雀跃,偶做侧耳的倾听,怕也是能听懂石语罢。
我与石,多半是在深夜凝视,所以石头跟我说的也可称作夜话,很多奇妙的语言,精辟对话,当是都忘却笔记。修润之,或是些值得珍藏的对话录。
曹侯定是懂石语的,石头和他心有灵犀,他也与石头喃喃语。暮年呕心笔墨,写为《石头记》。
昔在狮子林,觉得四处闹哄哄。其时冬雨阴暮,柳丝干枯,游客稀,独自在里面走,总觉石头在笑闹,摇头晃脑,神色憨顽,哪个是有洁癖的倪云林?!
留园有个五峰仙馆,供着一个灵璧横峰,惊世绝伦,五个峰,恰比五个仙人,馆因石名,真是好。
我在天津也见过一个类似的山子,六个峰,整看像只手,名之“六峰仙馆”太跟风,心想干脆名之“枝山手”好了,明人祝枝山,天生六指,笔端元气,也许正是多此一指而来。化为峰,峰峰应是生花妙笔。
石头中有种叫玉的,琢磨之,成为好物。但其中混入恶俗者——翡翠,亦名之玉,又最值钱,我独不喜欢,曾连带其他玉石一并疏远了。昆明街头满是翡翠卖,花花绿绿,活像绿头苍蝇。人间世俗的眼,总是雅俗难就,既有大雅的在,又多琳琅繁华的俗,这恰也是种好,是人世间的不即不离。
风砺石有种近玉的,多夹杂质,太湖灵璧没有这样的质地,风琢砂磨,各色样貌神态,虽不纯净,却更见本真自然。
新得风砺石山子,小到可以成为袖中抽出的烟云。
有峰有峦有岭有涧有岗有崖有沟有岩有洞有丘有壑……古人画理画法分得细,每种皆有所指。缩小到山子,皆以此为品鉴准则。
传统山水画,至今气数基本是尽了,画者一概不论这些,也多不识此类名称所指,以为画的像真山水便是得了笔墨气韵,故而今日画山水者,鲜嗜此,要么也只是欣赏象形图案,如鹅卵石之类。
以前见黄宾虹画册,其中有他玩过的小太湖石山子照片。玲珑通透,蜷伏着,曾在案头静静看老夫子一笔一墨,写来万仞山、千江水。
也算是块福气石。
观 云
云水多变。论形,水怕是比不过云。所谓行云流水——流水于地,变换其形,随缘尽性,除却人为冰雕塑造,一般形色变化虽多,终不及云;云霞游天,自由舒卷,四季流转巾,变化却是无尽。
书道玄机,怀素自道悟之于“夏云多奇峰”,不过是言语无奈处借云之变来打比方,真正到了高妙处,谁又言语说得来呢!山水画里,最是讲究留云法。虚空浮幻的东西,是如何画好?只留一片白,把给人心自去关照。佛拈花微笑,顾左右而言它,《诗》里也有比。一比、一兴之间便开出几千年汉文明的活脱生气。
云之变,是为虚柔而无定形。随顺万物,动静相宜,故而平淡悠远、瑰丽缤纷皆可以。昔人枕肱有歌“人情若流水,名利似浮云”。儿时读唐诗,尤其爱王维“坐看云起”这样的句子,汉人看人世的智慧,对有生的洒然,每在歌里诗里漾漾荡开。
年前收一小湖石,几经摩挲,竟出来些旧气。小贾说石因人而得灵气,自是恭维的漂亮话。兴时我把万物作云看,这石也不能例外,故铭之“朵云”。置之案头,早晚明霞当窗之际,晏坐观之,“朵云”或在一侧瞅我。若是真有灵气,也把我来做云观么?
蝉 砚
三足蝉形歙砚,青琅玕,铮铮然。和明时期的蝉砚比,蝉的特征不明显,内敛含蓄,尚有宋韵,是有些类似风字砚变过来的模样。
古人做事多不苟,恭敬虔诚,手工业时代这是从业者必须的品性。心手合一,人心活泼,性灵的妙义便得以完全地留在器物上。
古器物,造型对称绝对是意上的对称,细细测量,又有小出入。比如这双砚足,砚池,皆是这样恰恰好。今人做,绝对对称了,却呆板。每个时代都有各自性格,凡沾人手的,皆同那时代的人。今人多表面油滑,内心则木肤肤,有多少心灵生活?!无趣、无聊,不好玩,还不如这砚。
心灵手巧的人手很绵软。据说齐白石暮年一双老手,柔软如棉。劳手累心,一辈子不曾停歇,能僵住?我见过纪录片,老人画个虾子须,画到纸外面,还再接一笔,绵韧入纸,就像纸与笔相吸相黏。
手软石硬,世间正有这样的用心与相互怜惜,石便多了些人世温情,便可称作砚。
老歙砚多银星,是表面氧化的缘故,厚者有一层所谓金皮,磨开来,里面青莹润透,这多半是好砚,很多时候碰到老砚,我带个小砂纸,主人允许,就磨开一小片,看看内部。这在常人看来,有点赌石的意思。不过古砚年深日久,墨垢包浆积得厚,不这样,有谁知道质地呢?
人也这样,尘世间莫不包浆秽垢积满。相逢一笑,相互磨,即便无缘,磨洗了,也多清净,何尝不好。
瓶 花
明人张丑《瓶花谱》开篇引用梦蝶斋徒的话——“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
此谱所记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等条目分类,其中以品瓶一节最为繁要。明代人插花尤重上古铜器,“古铜瓶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宋瓷有写意模仿三代铜器者,更是古雅,到晚明时,宋瓷也已成稀罕物。故谱中道:“尚古莫若铜器,窑则柴、汝最贵。”佳器总比鲜花珍贵,故此喋喋,可见古人于玩物之专注可爱。
书中关于荷花一条说:“初摘宜乱发缠根,取泥封窍。”去夏摘得十余茎荷花,养在瓷罐。不到一夜竟全部萎了。有此讲究,应该是经验之谈。
古人插花审美,最求自然,其理通于我国的书画。
“插花需要花与瓶相称,令花稍高于瓶。忌太高,太高瓶易仆;忌太低,太低雅趣失”。 “小瓶插花,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止一枝,则须择柯奇古,屈曲斜袅者。欲插二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者。或两枝彼此各向,分凑簇像生,用麻丝固定之”。
“瓶花虽忌繁冗,尤忌花瘦于瓶。需折斜欹花枝,铺撒小瓶左右,乃为得体也”。
“瓶中插花,止可一种两种,稍多便冗杂可厌。独秋花不论也”。
日本插花将这些讲求进一步细分,推到极致,有时看看,未免太过纤巧,少了花草自然之性。
明代画家陈老莲,早年曾求学于理学家刘宗周,生活上却放浪不羁,是走名士风度的路线。加之画中人物又个个奇古倨傲,所以陈一直给我的印象是相貌清癯,性格怪诞。但是画我却一直喜欢。
老莲和张丑生活在同时代,画中描绘的瓶花,细节刻画,皆取舍不苟。其中铜瓶瓷尊之类所贮鲜花,可为这类闲书做注脚。所见画中所供有梅、竹、菊、水仙、竹节海棠、玉兰、牡丹、芝草、芙蓉、荷花、山茶,更有虬曲枯枝相间红叶,插在半人高落地螭虎瓶内,最得逸趣。
对于今人,插花最难的怕是这条:“折取花枝,须得家园邻圃,侵晨带露,择其半开者折供,则香色数日不减。”今日市场上的鲜花基本是靠空运。一枝一朵,早非明人花圃中折取的自然姿态。况有几人“家园邻圃”?即便是冬日里南山折来贩卖的腊梅,捆扎剪裁,难看极了。范老师谑称之“狼牙棒”。
幽栖逸事,庶几尽矣!
(摘自《银锭桥西的月光》,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3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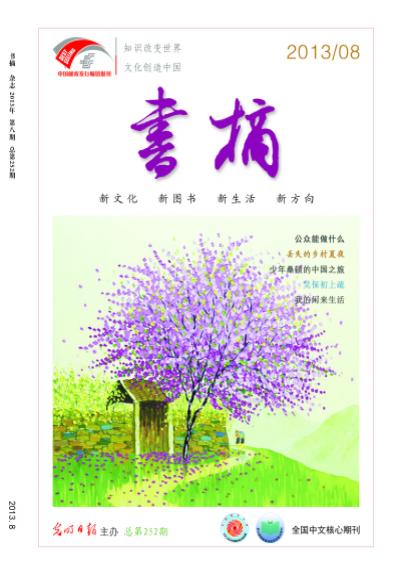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