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彼时有缺,也有光华。古今对照无定论。被吞没和推远着的价值观,如夜空中流转星光逐一熄灭。我们也许已忘却抬头看一看天空,寻找星辰轨道,感受它遥远时空之前迸发的光耀。而这光耀仍在等待……
[按语]:
《古书之美》以古书沉淀百年的厚重与优美,呈现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倡导读者回归质朴、平和的本初心境,通过了解、亲近、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而淘澄心性、陶冶情趣。其主体内容为著名作家安妮宝贝对著名藏书家韦力的长篇访谈,以随笔的形式容纳访谈内容,展示了古书在版本、纸张、装裱、刻印等方面的含蕴精致之美,怀缅了古书历经百年递嬗的艰难历史,并向前人著述之严谨、工匠技艺之精湛、古法用心之体贴致敬。
问:先简单地纵向梳理一下中国历史上古书收藏的脉络。
答:古人有一个小笑话,有个人夏天乘凉,坐在外面晒肚皮,别人问他做什么,他说他在晒书。博闻强识是智者的前提,学富五车,不是装五车书,而是装在脑袋里。书籍代表人类进步,它是鲜明智慧的总结。
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藏书者,应是老聃,他曾任职过周朝类似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官位。说明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时候,中国已有图书的收集整理,并有专人管理,可算是国家图书馆的雏形。中国私人收藏的规模,是宋代,因为宋代是中国版刻艺术成熟的起点。宋代产生了一系列大收藏家,如欧阳修、王钦臣、叶梦得、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他们收藏大量传统文献,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直到民国,藏书家越来越多。这便是中国的藏书流脉。
历代对藏书和藏书家都很看重。有一种独特的文献体叫“地方志”,唯中国所独有,是指每个地方都有记载当地风物的记录,其中有一个“文苑传”栏目,专门记载当地著名的藏书家。
从流派上讲,宋代是不同目录版本学的起点,自隋唐以来,文献家们重新整理典籍,进行新的分类,确立了科学的分类步骤,比如四部分类法。直到今天,我们的古籍仍然按照这个方法分类。
问:以前的藏书人和现在的藏书人,在状态或身份上应该有些变化吧。
答:古代藏书的状态有其特殊的原因。从隋开始有了科举制度,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开始了整个社会从文的时代。
对文化的崇拜,产生了对它的收集和整理。那时若一个人有学问,便能考取功名;有了功名,就有了地位;有了地位,就有了钱;知识权力金钱是一体的。这间接说明,在那个时代,无所谓藏书人是否有钱人,因为有钱人基本上都是有知识的。
但现在的社会发展有所不同了。有钱的人和有知识的人不再是一体的。如我这般小人物都能得到,对我而言是幸运的,对社会而言是悲哀的。这么好的东西,如此轻易聚在一个小人物的手上。可见,这个社会的收藏体系是有问题的,它本应由能力更大者来完成。
问: 那我们来讲一部你所钟爱的宋版藏书。
答:讲讲《施顾注苏诗》。这部书刻于宋嘉定六年,是今天留下来最早的苏东坡诗集的刻本。 书里有清初著名藏书大家宋荦的收藏印,顺治十二年宋荦第一次游江南时,购买了大量珍本善籍,包括不少毛晋汲古阁的旧藏。除此之外还钤有许多著名藏书家的藏印,是典型的从大家到大家的流传。这部书也曾为康熙朝权相明珠之子、纳兰容若之弟揆叙所藏,后来又归了苏斋。“苏斋”是翁方纲的号,他在乾隆四十年得到这部刻本,特别高兴,同时又得了苏东坡一个帖,就把这两件搁在一块,建了宝苏斋。此后在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生日这一天,他都会请很多名士到家里共同祭奠这部书,在书上写跋语和题记,称为“祭苏会”,一直延续到民国罗振玉还在祭奠。这也是我所见过的题跋最多的一部书。
问:你认为自己的收藏较为注重哪些标准?
答:任何收藏都不能脱离一个基本点,就是物以稀为贵;其次是看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第三看艺术性,比如古代的版画艺术、装帧艺术。任何一件收藏品的价值都不能违背这“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问:书买回来之后会进行修补吗?
答:古书流传至今,大多经过历代藏家的改装。为了防止被虫蛀,我从德国买来一台能调到零下十八度以下的大冰柜,把书装密封袋里搁进去冷冻二十四小时,以冻死所有虫卵。在修书时,我用的是自己以仿古方法造的纸。因为目前市场上的书画纸,是卖家把化学纸浆往手工纸浆里勾兑而成的,无法永久保存。这种传统工艺,从伐竹到出浆,再到造纸,最快需要两年半。如果一套书原本用的是竹纸,就不能再用竹纸修,因为竹纸发脆,修书的纸必须柔软,软于原物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否则反而会把原物撑坏。
我用古法复制古书,前提就是不讲成本。造古纸,找人刻版,再按古法印刷。我自印了一个系列的十部,需要一部一部地刻。
问:你做这十部书有什么用途呢?
答:让古书在这个世界上有所留存。多年后人们说雕版失传了,我说未必,请看看实物。我是个很拧的人。
问:因为很多东西会让你打消念头。只有认准了,才能把事情做好。
答:我们所受的教育已使我们习惯在做事情时本能地衡量——第一是目的,第二是划不划算。如果有这些观念,什么都干不下去。一个人能打破自己的固有观念才能真正打破了魔障。我为什么做事?就因为要做,没有目的,没有那么高的理想,也没有那么多的算计。
问:你也一直在为报纸撰写相关书籍的专门介绍吧?
答:一篇篇在写,让大家了解我怎么看待每一部书,或者说我为什么会藏着这部书。一种取舍就代表一种世界观,你怎么看待、怎么把握这件事、你认为什么是好的,都能被折射出来,如果细品,就能品出。古人把收藏叫“选学”,是专门的一门学问。如果你不能将收藏升华,只停留在聚物的层面,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一个仓库保管员而已。
问:出席过一些藏书界的公共活动吗?对此抱什么态度?
答:我性格比较复杂,一方面不喜欢做抛头露面的事情;一方面又很矛盾,希望对这个行业有所推动,影响一部分人。比如毛泽东“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词句,其实应和了陆游的词:“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是一种姿态和境界。从这两阙词可以看出我性格的折中。
对于今天的藏书活动,我希望暗地里推动,而不喜欢站在台前,以高调的姿态应对世事。人之所以独立为人,就是要有独立的思想。但今天太多人不喜欢自己思想,而用别人的想法来代替。我的原则是不上电视、不做录音、不照相。我可以参加活动,但不要大声示众。
问:在这件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财力、精力,除了对个体发生作用,比如对自己的内心,你进入它的世界,它也影响着你,还有可能以某些方式发挥更大的作用吗?除了妥善保留典籍,是否还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人群或者社会有所推动和帮助。
答:近二十年来,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在内的大汉学圈有个共同论点,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藏书家。因为大量书都归了公藏,民间的筹码极少。我今天的藏书量,按照卷数来说早超过三十万卷。古人以十万卷为一个标准,我的藏书,哪怕在三百年前的乾隆时代,也称得上颇具规模。没有传承,凭空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现有质有量的积累,在这个时代很难。
事实胜于雄辩,少说多做才能把一件事做成,这是我做事的信念。我一直在做相关专题的影印出版,因为很多孤本能被相关学者看到的概率很低,我开放地把书看做社会公器,相关研究者都可以使用。我也在做系统的总结,出版自己的书,尽量让这些东西为人所用。把这些典籍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是我的愿望。怎么让“你”知道历史典籍的重要,而不是“我”。我一直在这样做。这是我对古书的看法和做法。
问:长期以来藏书、读书这样一种方式,是让你更开放,还是有所封闭?
答: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我能更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小时候看电影,里面有坏人、好人,那个时代是两分法,一切都是非黑即白。长大之后随着读书,慢慢明白了客观性,觉得大多数人是介于好和坏之间的,有时候为善,有时候为恶。我们缺乏可观的教育,但通过读书,会逐渐明白这一点。读书越多,越能客观看待社会,古人云,读书 使人明志,明志二字就代表着客观;另一方面,随着读书的增多,心态更加平和。平和意味着开放,而非仇视,让我更能明白存在就是合理的真正含义。
问:如果你去一个孤岛,只能带三种东西,你会带什么?
答:我小时候看过《鲁滨逊漂流记》,那时就特别向往这样的逃世,年轻时也有这种潜质。但鲁滨逊毕竟有一艘船和其他东西,才能活下去。现实中一个人单纯的逃世是不存在的。我至少要有水、食物和其他的许多许多。
问:可见你目标明确。让你做失控的事情是很难的。你关注当代的书吗?
答:我关注当下的一些事情。但因为要兼任不同角色,比如赚钱,读书,研究,看拍品,所以很多事无暇顾及。出世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行为。人处事不应该脱离社会现实。这也是我始终警惕的一点。
(摘自《古书之美》,新星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49.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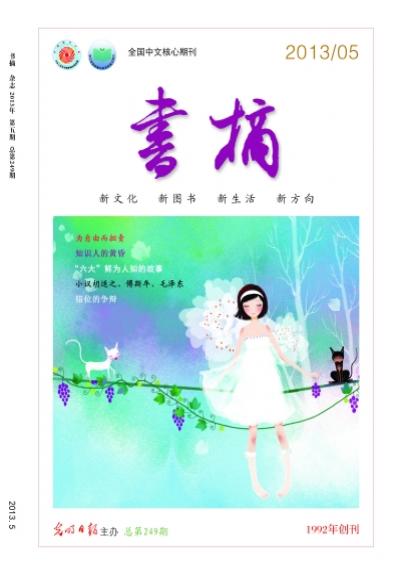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