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菲雷波斯篇》中说:“早先时代的人,比我们更好,也比我们更接近神。不得不提到的是,一些年来,人们事实上看到一场普遍的过去之恢复在西方社会出现:无数年轻的信仰复兴运动……时装和审美趣味系统性的‘曾经相识’,各种各样的寻‘根’,个人的、文化的、种族的或社会的根,对于文化遗产的激情……”这样看来,在所有的时代和历史进程中,人们都普遍对过往充满怀念与崇敬之情,他们通过使过去复兴来寻找自己的来路,通过对过去的重新演绎而显示自己的独特的、区别于此世的品位。所有人都在内心有一个恒定的标准,他们认为过去的是更好的,早先的、旧的、死物充满着时光的味道,显示着另外一个比现在更加美好的世界。
终于,新青年们开始了复古运动。回看过去,二三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对我们有着更加强烈的吸引力。复古的潮流一波又一波,力量也愈发强大,由何勇颈上的红领巾,到音乐节的创意市集当中的一些上世纪的女士衬衫的销售,到鼓楼东大街上Mega Mega Vintage店里特有的旧服装的味道,再到满街的毛泽东头像、老式的劳动人民、工农兵招贴画,你永远无法拒绝复古在暗中慢慢流动扩散,由普普通通的衣食住行,到音乐、电影、艺术品,再到日常生活当中老式照相机、留声机、上世纪发式、服装的复兴,“老物什”也逐渐成为另一派全新的暗流。这股复古的风潮,是对过去的一种想象中的复归,是对过去的乌托邦式的向往。正如伍迪·艾伦在电影《午夜巴黎》当中所要表达的,所有被拴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人好似都对自己的时代颇为反感,倘使能有一个机会,一架马车,带他们回到过去,那他们将兴奋不已、梦寐以求,并极愿留驻在过去那个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青年被旧事物吸引着,不论是想要从中一探真相,还是纯粹为了其远道而来、逃离此世喧嚣的静谧,抑或仅仅为了与众不同。
“昨夜星辰”相较于而今充斥周边的此时此刻,总是显得唯美,充满了遥远的不可抗拒的光晕。让先锋们在疲惫之余稍有和缓之意,而他们的开拓,就在这旧有的故事当中成型。那里是他们想象中的来途,是他们梦里的温柔乡。追溯过去的复古是永远无法被抛弃的,而这也并不和先锋之开拓精神相违。新青年们永远跳跃在人为的时间之间。
服装风格
新青年们愿意选择古装和复古的装扮,即在外表上与众不同地宣称对这个时代的不再依赖,宣称独立,宣称“我不属于你们”。 这种“属于过去”却绝不是倒退,反而是非常激进的。风格与时装更成了复古的一大风潮。
复古在日本出现,最初只是少部分年轻人,穿上世纪的衣服,将自己打扮成古怪的上世纪人。逐渐,它成为了服饰界的潮流。古着是奇异的、浓烈的,有大量时间的旧气味,其中当然也不乏许多来自英国的低调与绅士、淑女风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朋克蓄意破坏传统审美——表现在愤怒地将都市生活的碎屑(别针和垃圾桶衬里)与校服、短裙、芭蕾舞裙的肮脏碎片一起再生利用——的时候,复古对传统审美的破坏则显得更清淡和易于接受。
古着颇不合时宜的跳色大毛衣、蝙蝠衬衫和吊脚裤,掺杂着波普和夸张的几何图形,跨出时间的门槛跳人人们眼球。大众现在所拥有的审美是传统的,而复古是最简单的对传统审美的破坏,在选择旧衣饰的时候,它呈现的是不同于这个时代的风格,并在同时破坏了普遍意义上的传统审美。它放弃了遵循发展的传统,打碎了时间的线性关联,给传统的现代人审美打击。
总之,它让更多女孩愿意被形容为“尖儿”和“在”,而非传统的“美人儿”了。
复古出现的时候,不但成为了小众的某种形象代表,而且被小众广泛地接纳、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一段时间之后,它甚至逐渐脱离了亚文化的范畴,其风格、特征逐渐成为为大众所接纳的时尚。
普遍意义上,在复古的形式因为其优越、动人而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时候,它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为小众所独有的亚文化标志,而成为了商业社会下的一种元素,成为了装点大众生活的商业符号而已。如今的通俗文化对复古的认同,即将复古的某些元素摘取出来,糅合现代的特质,使复古成为不今不古的中间状态。于是,这种状态被愈加广泛地称为“复古”,即对过往的复归,这种被更多人接受的定义将复古从亚文化的怪人们的小圈子里剥离出来。
事实上,任何意义上的复古都不是完全的复制,所有的复古产品都糅合了现代的特质,正如康纳指出的:
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不是依赖同样产品的无休止复制,而实际上是依靠边缘文化或对立文化形式的异己能量所提供的东西来维持的。时装也对亚文化风格进行整理、简化,有时甚至多样化,以供市场的需要。
老相片
老相机的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偏远的时光、颇有意味的质地、沉重的机械感制造了与当今飞速发展的科技制品完全不同的时代感。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记录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城,天安门前面聚满了人群,穿着相同的蓝色系的服装。在这些人群中,有一个又一个的高架,摄影师坐在上面,打着阳伞,人们排好队去镜头前与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合影。一个姿势大概要摆上几分钟,调整很久摄影师才会按下快门。大概他们要留下地址,等着摄影师将相片邮寄给他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人们在拍照的长久的等待中,在巨大的闪泡打出火花的时候,是如此享受一张小小的黑白相片带来的快乐。
感谢科技进步和商业发展,如今的我们早已忘记拍照曾经是奢侈和漫长的等待。胶卷仿佛已经成了上个时代的符号,宝丽来甚至已经停产相纸,但实际是:旧式相机和胶卷的质地反倒让新青年们爱不释手——各类手机应用中少不了做旧的胶片风格;真正的老相机也令许多人着迷,当今的新青年们对双反海鸥、牡丹仍然兴趣盎然,重新拿起爷爷辈的相机,仿佛能够被相机的取景框拉回那个年代,将此刻的时光塑造成远方的模样。
独立乐队与拼贴艺术
摇滚乐业以复兴,老歌新唱、回潮和封面曲目的形式,与时装也一样,是文化历史的灵活销售性的最佳例子。在近年中,新技术形式的发展加快了这一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民主化,是摇滚乐的文化痕迹能够在物理意义上以模仿作品和拼贴的形式被拆卸和组合;那样做所需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短,而且更加难以控制。
在摇滚乐当中,现代歌手更多以拼贴的形式将老歌与现代元素进行卓有成效地剪接。新先锋们通过拼贴和组装,让老先锋们宣布死亡的东西重新复活,虽然依托着旧样貌,却因为与现代的组合而被赋予了全新的、不同于从前的生命状态和意味。
中国在几十年前的确有一阵子,一群先锋们走上街头对传统大肆破坏,将“先锋”视作目的而非本质,打着这样的旗号伤害了许多旧文化、老传统,最终,这些老先锋们与许多旧时光一起消失和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先锋派们集体性地回望,为过去平反,反对的是他们上一代的先锋们。例如,在王广义的推动下,街头一度出现的“政治波普”艺术:大肆放置的毛泽东头像、与可口可乐等消费品广告拼贴的“文革”时期的招贴画、宣传海报等,都无疑是新先锋艺术家们对过去神话的批判。提出了“政治波普”的栗宪庭,在一次访谈当中谈道:(美国政治波普)是流行的、通俗的、大众化的符号;而中国政治波普则是借用了“文革”的政治符号,将它与当下流行的商业符号并置,找到了一种很荒诞很幽默的关系和趣味。“政治波普”把政治流行化了,消费掉了,俗化了,并通过特有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这就是它的意义。
以上的种种情境,需要注意到的是,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均生发于一小撮人,其后便在不经意间走向广阔大众。这里存在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即亚文化到底要不要保有亚文化的姿态?当它的特质被小众广为传诵而后被更大规模的受众所知,成为潮流与时尚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属于亚文化了。尽管它具有亚文化的某些特质,但这些特质只能被应用为时尚的一种元素。正如我们的理想最终被世界当作一个商业符号一样,当亚文化的边界慢慢模糊消失,其自身也逐渐为外部世界所改变。或许,在它开始征服大众的时候,它自身便也不复存在了。
当然,不论如何,我们都是在沿着前代的脚步拾级而上,当一种亚文化不再属于亚文化团体的时候,另外一种亚文化会出现。何况,在这种亚文化被应用在广阔的大众文化当中的时候,仍会如那昨夜星辰,在遥远的天边照耀着今世的你我,熠熠生辉,永不消逝。
(摘自《新青年“独立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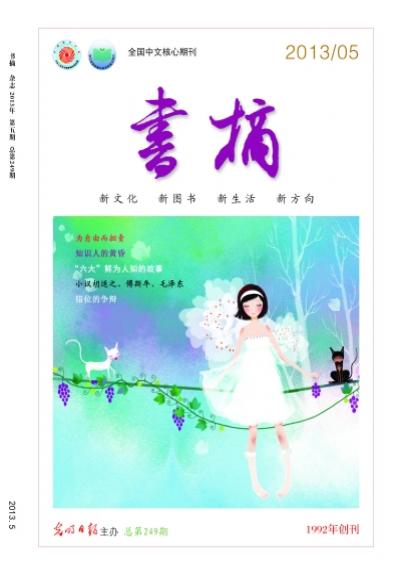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