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曹寇说:“从更深层面来讲,写作源于我毫不欣赏我的生活。”
曹寇只写事儿,不说故事。他写那些无聊的、杂乱的、鸡零狗碎的事儿,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的真相,不作,但是力透纸背,因为坚硬的文字背后,有真实、真诚和真相在打动我们。
对于农村子弟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之后的应届生都热衷于考中专。这事就我所知,大概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正如“过来人”所知,在那个城乡二元结构近乎水火不容的年代,“跳农门”和甩掉大扁担是农村子弟唯一可以被理解为“出息”的道路。路遥那篇脍炙人口的《人生》,高加林的悲喜剧就产生于城乡差别之间,高加林芝麻没捡到(做城里人梦的破灭),西瓜也丢了(村姑巧珍嫁给了别人)。当然,路遥结合了当年的“五讲四美”运动歌颂的是只知道扳着手指数猪的巧珍那“金子一般的心”,却在对高加林涕泗滂沱的悔恨中有意淡化了城乡差距这一残酷的现实问题。
现如今城乡差别仍然严酷,否则青壮年不会抛荒良田到城里卖苦力,不过,区别还是很大,眼下农村子弟凭借明暗难辨的“能力”确实可以在城市里混个人模狗样,但那会儿却囿于严格的户口制度难以享受城市福利。拥有一个城市户口既是梦想也是荣誉。我们那儿有句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长得不丑,就是农民户口。”
也就是说,走正规渠道成为城里人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出去”,而在考出去这一点上,考中专和考大学可谓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转户口、国家分配工作。若有不同,就是大学生比中专生好听点,工资起点也高一些,不过也就这样罢了。
考不上,还有一个办法是复读。我的大姐是高考复读生,复读两年,亦未有果。我所能记得的是她每个月从城里复读班回家一趟,带给弟妹一点花卷和馒头之类的副食品。鱼米之乡,面食难得,争抢之际,粮票告罄。
大姐的“可耻下场”在先,我的哥哥既然也未能考上中专,父亲即希望他能直接“走上社会”。不过,哥哥也算命不济,仅一分之差,所以在老师和母亲的鼓励和说服下,他决定复读一年,光荣进入了“初四”。虽然初四年级的师资主要还是哥哥过去的老师,但他们的班级不能够设置在校园,而是租赁了民房。因此,他们的课表与在校学生课表完全不同,需经教务处调度,机动性相当大。比如说,他们根本不需要每天早出晚归;听说老师们相当和蔼,以致连迟到早退也不存在,谁有事没事懒得去上课的话,也没人追究。此外,他们的教舍也相当简陋,只有一块平时作为挂件的可移动黑板,而且基本不太使用(以做题讲题为主)。因没有足够的桌椅,师生们或站或蹲,累了而没有凳子的话,他们索性爬上农民房东家的粮食麻袋上盘腿而坐……
正是因此,复读班在当时的我看来,自由得令人向往。哥哥据说在这复读一年里并未用心,常和重新认识的同学们互相串门。或许正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遭遇使他们结成了远胜于校园同学之间的更为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他们仍有人情往来。
鉴于上述,鉴于我的姐姐和哥哥都没有考出去,鉴于别人家的孩子总归有考出去的,为了争口气,1993年我相对顺利地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录取通知书送达的当天,我和父亲正在田里干活。老实说,我一点儿不喜欢干农活。平时父母邀请我下地帮把手,都尽量被我以“要看书”为借口拒绝了。在我看来,中国农民这种精耕细作的传统劳作方式,唯有使用“当牛做马”、“不是人干的”才能加以形容。这时候浑身泥土在田里跟庄稼拉拉扯扯,完全是因为借口不复存在、考试结果吉凶未卜罢了。送通知书的是学校的一位老师,他风尘仆仆满头大汗的样子看起来比我和父亲还要艰辛。就河沟里洗了手,惊恐万状地接过通知书,父子二人认真看了几遍,才想起来对老师表示感谢。所谓感谢,也无非是父亲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那会儿长期抽一块五毛钱的南京牌香烟,比之当年盛行一时的红梅(五块)和红塔山(十块),完全拿不出手,与眼下这张使一个人命运发生改变的录取通知书很难相衬。所以我看到五十多岁的父亲在递烟的时候居然面露羞愧,而那位老师接烟也十分勉强。但还是点上了,呛人的劣质烟草味儿将我们笼罩,让人深感忧伤。
确实如此,这是那年头农家最大的喜事。每年此时此刻,都会看到中学教师们骑着自行车在乡村大道上鱼贯而行的场景,继而他们消失在鞭炮齐鸣中——那是考上中专的学生家,家长们出于真心实意,以大鱼大肉的筵席表达对老师们数年来给予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就在几年前,哥哥的同村同学考上中专时即是如此。当时我和哥哥正在路边用铁叉晾晒柴禾,见赶赴谢师宴的老师们由远及近,哥哥神色慌张,丢下铁叉飞也似地躲进了家里,并掩上了门户。他没有考上,而同村的同学却考上了,这确实对一个乡村少年自尊心是一次重挫和考验,他无法面对教师们赶赴酒宴的场景。不知道是这个原因,还是家里实在请不起酒宴,或者是我的反对,1993年的夏天,我家没有响起鞭炮之声。九月份的某个早上,我孤身一人默默地离开了家离开了村子,经过一番舟车劳顿,然后成为一名中专生。
值得一提的是,去学校报到之前,我突然变得“勤劳”了,几乎每天都跟着家人下地干活。于今看来,我愿意将这种乡村少年陡然的“懂事”理解为一种矫情,只是它是客观存在而已,不构成羞耻。我要说的是,这也是我对家人记忆最清晰的一段时光。
姐姐已经嫁人不提,母亲依旧浑身泥巴地在田里干活。哥哥则已经去学了汽车驾驶,为他之后多年的出租车司机生涯做起了准备。而祖母,那个14岁作为童养媳来到我们家的时年83岁的苦命女人,每天都坐在阴凉下帮助我们剥蒜头,以便让我们将一枚枚蒜瓣等距离地插到田里。她希望我将来工作拿工资了,要去下坝街(当地一小集市)买一根刚出油锅的热油条给她吃。而我的父亲,不再对我咒骂不已,他诚恳地提醒我,不要偷他的烟抽。“抽烟有害健康”,他确实说了这句随处可见的话,我不能确定他是用什么语气说的,但我顽固地认为这位老农民是使用蹩脚的普通话念的。
然后,就是,在未来数年的中专生活里,我因为祖母和父亲的死,两度回家奔丧。祖母死时,适逢中秋,菱角鲜美;父亲死时,即将过年,大雪纷飞。
(摘自《生活片》,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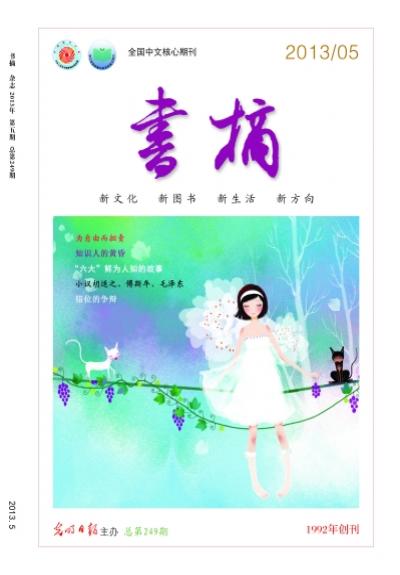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