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无主义”定性我爸,他若活着一定反对。我爸心思活泛情感丰腴,对我的冠名,不会按字典教条去自排自查,但草率笑纳我的定性,又有悖他明敏的天性:万一我拿他开涮他却认了真,万一我跟他学术他却玩了笑,都坏兴致。我们父子间“逗”智“逗”勇,不论我把他奉为启智的师长还是当成打趣的兄弟,他对即时的兴致都很珍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即使反对我给他贴虚无标签,他也不会正面迎战。他多半会狡黠地眯起细小的眼睛,似攻似守亦进亦退地说:我只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个有五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辈子的工作几度变化,始终不离解释和传播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与功绩。但现在我明白了,他拒绝虚无主义这顶帽子时,躲避的可能更是“主义”。
一
我爸一般不玩深沉,天生不会,后天又拒绝假装老辣。多数时候,他是透明的孩子。如果记忆没欺骗我,我得承认,我平生听的第一个黄段子是我爸说的。他不是特意说给我的,是他喜气洋洋地说给一个朋友时,我听到的。当时我十几岁。当时他朋友欲笑又止,然后满脸深沉:这有孩子!我已记不得那段子的内容,当时也不可能明了那段子里的象征暗示与比喻引申,但我能记住它带给我的怪异感觉,能记住在我爸朋友深沉表情的对比之下,我爸的一脸坏笑花团锦簇。
许多家长假模假式,戴着面具教育子女,好像孩子是群众只供瞒骗,而他们是领导,嘴巴里边全是舌头。我爸不,他从来都把我看成平等的伙伴,陪着我理解人性的弱点与生活的污秽,即使已成共识的“幸福”“美好”,他也不把它们硬塞给我。我十四五时,有一次逃学在家抽烟,被恰好中午回家的他抓了现行,他一脸阴郁,满腹悲伤,沉痛地与我谈漫长的话。他只讲道理,没大喊大叫,通过讲今比古分析人的嗜好与习惯,让我判断什么该养成什么应避免。他反复自责,说他抽烟的恶习影响了我,信誓旦旦地决定戒烟,要以此为我树立榜样。可当天夜里,我把长长的检讨交给他后,他竟有点嬉皮笑脸。他先说,他像我这么大时也偷偷抽烟,又和我商量,如果他不戒烟,却反对我抽烟可不可以。又有一次,我十六七时,一早晨家人还没起床,两个警察就来抓我,说我在商店抢钱,把我押往派出所的小黑屋子。中午姐姐给我送饭,说我爸班都没上,一上午光在家唉声叹气,他这个一向好面子的人,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这么龌龊,竟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可当天晚上,我获释回家,发现我爸并不难过,只努力掩饰脸上的骄傲。原来,他已从警察那里问清楚了,我没抢钱只是打架,因为打架的地点恰好在商店,我顺手使用商店砍肉的片刀与卖白菜的钢叉时,不能不撞翻装钱的匣子。我爸的骄傲在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勇于与一个欺负我的成年人宣战。在他看来,当一天囚徒只是小节,大节是为什么身陷囹圄。
我爸不扯道德主义那一套,不凡事上纲上线小题大做。他认为人性的弱点只可抑制无法剔除,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唯有强化人的理性。但在他那里,理性又不是教条不是戒律,只是春雨淅淅沥沥。他信奉开卷有益,把读书视为理性的温床。有一次,我和姐姐光顾读书,没做该我们分担的家务,恼火的妈妈撕破了书。我爸下班后,很严厉地批评了妈妈,说咱的孩子可以不喜欢家务,但不应该不喜欢书。当然他转脸又笑嘻嘻地对我和姐姐说:更应该的是,书读得好家务也做得好。我爸做家务不行,他笨拙、懒惰、油瓶子倒了都想不到扶。记得那天妈妈连夜糊好了破损的书页,但故意不讲理地说:他们读的都是“毒草”。我家当时的几箱子书,封面上,基本被我爸做了标注:“大毒草供批判用”,是他希望如遇抄家,这些书可以曲线脱险。我爸也故意不讲理:对呀,是毒草呀,可咱的革命小将不读一读,怎么批判呢?
二
我爸爱说话也会说话,不论私下聊天还是公开演说,都机敏幽默有表现力,他自诩是得了点康德“谈话的美学”之真传的。他的一生,既因工作需要也是兴趣所在,不断涉及的大部分话题,正是——至少在一定层面上——玄奥并且僵硬的东西:主义。
“政治”一词出现在中国,有一百多年。在汉语言的浩浩长河中,百年的历史太过短暂。短暂易导致生吞活剥,生吞活剥则消化不良,于是,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一直狭义,三喂两喂,就把它豢养成了个危险的东西。可政治又是活跃元素,特别喜欢突出和挂帅,还绑架主义,这样,主义就也危机四伏。可以把主义暨政治这种叵测的东西说得深入浅出又收放自如,言之成理又引人入胜的,我爸是第一人。我不认为我的判断太井底之蛙。多年来,与我爸有过往来,提及我爸,他们都会赞叹一句:你爸讲话太精彩了,听他作报告是种享受。顺便说一句,唱赞歌的都是前辈,他们没理由讨我的好。再顺便说一句,我爸从来不是官员政客,只当过业务小干部,他的所谓“讲话”或“报告”,除了私下的海阔天空,再就相当于现在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宣读。那时没学术,更不讨论,我爸的“口头论文”不论多长,“发表”后,唯一的报酬是口腔快感。
我爸擅说却不擅写,几乎没留下署他名字的像样文章,而他发表的所有文字,都只能将他定性为一个拾人牙慧的传声筒而非识见独到的解惑者。先是在个市级革委会写作组吃香喝辣,模仿“梁效”“罗思鼎”的文体风格与署名方式,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大块文章。然后调回出版社重操编辑旧业,组织多路人马撰写国内第一套多卷本的《马恩选集简介》,“工农兵三结合写作组”是他们的集体署名。后来,“文革”结束,我爸的作文生涯也告结束。我动员他写下去,说你不写列宁写别的呀,他以列宁一篇文章的题目与我戏谑:不急不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他没做到“少些”,更没做到“好些”,“坏些”的文章也没再写过。
自童年起,我就渴望以精神的方式成名成家,在并无稿费之说的年代,甘愿匀出些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的大好光阴,去吟诗作文舞文弄墨。我爸欣赏我学习的自觉,却像反对我逃学旷课打架斗殴一样,反对我吟诗作文舞文弄墨。他动员我拆装半导体或钻研微积分。我是个什么料他很清楚。我笨得往墙上钉颗钉子都钉不直,一百开外的加减法都得笔算,考大学时,苦学半年我数学只得二十几分,他已然满足于我的超水平发挥。但他太不愿意我吟诗作文舞文弄墨了——当然更不愿意我当工农兵。他不认为我的偏科是不治之症,他觉得,既然我十三四岁就能代替生病的老师给两个班的同龄人上语文课,若再花点心思,在数理化方面高人一头没准也行。他给我讲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多么残酷,以屠刀和绞索形容美妙的白纸黑字。他希望他教我背诵的诗文成为我修养的底色,他希望他鼓励我阅读的小说成为我了解世界与人性的窗口,但他惧怕我成为为他人涂抹底色和凿壁开窗的人。1979年我考取大学时,在为我送行的隆重家宴上,他竟硬生生郑重地说,在我三十岁前,能完成他的两个希望他就满意:一,入党;二,生孩子。如今他要求我做的两件事我至今没做,他反对我做的一件事我始终在做。
以前我认为,摆弄文字只涉志趣,只涉声名,现在我知道,它更指向思想的自由与精神的独立。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远远大于各种主义。我爸定然清楚这点,正因为清楚,他把自由与独立视为僭越,而僭越的风险,在他那里大过一切。他要保护儿子,就要剪掉儿子僭越的翅膀。入党和生孩子都政治正确,他相信,只有走在随大溜与过日子这条康庄正道上,他那满脑袋奇思异想的儿子才有太平。以此推想,不难判断,一旦我给他扣上帽子,不论虚无还是实有,只要挂着主义的飘带,他就不会贸然领受。他同样清楚,作为一个志愿放弃自由与独立的人,对于主义,领受即亵渎。
三
从我爸二十多岁的照片上看,他身材匀称,白净清秀,严肃的表情刚硬深邃,炯炯的双目有穿透力。那双后来的小眼睛竟不见小,坏坏的笑容也隐而不现。谜底由我妈揭开。我妈说,每每照相,我爸总顾忌眼睛太小影响帅气,就不敢笑,光瞪眼,照片上的端庄只是谎言。我猜想,我爸后来那种识人的本事,大约就源于自我解剖:照片上下的他判若两人,哪个才是真实的他呢?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不要轻信,越是天花乱坠的东西越要警惕。那时“感动中国”的英模典型比现在多。那时没有“做秀”一词,他把做秀称为“整事儿”,那时候,我特别佩服我爸那双笑眯眯的小眼睛,它总能戳穿某个大人物或小人物所“整”的“事儿”,让许多“正经”变形为滑稽。
我爸是吉林省东丰县刁地主家养尊处优的四少爷,十五六时,在国高读书。十六七了,经过一番小小蓄谋,冬季某个飘雪的深夜,他溜出设在县城的学校,并未返乡与家人辞别,就与其他三个同学混出国军关卡,去共军那里拜了码头。这次雪夜出走,是一次主动的信仰植入,它完成的,是我爸心理上的成人典礼。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爸对主义的选择,并非源自一时冲动。土改时,不再饥寒交迫的我爸他爹被贫下中农乱棍打死,镇反中,也曾忧国忧民但参加了国民党的我爸他大哥被政府枪毙,对这样的失亲之痛,我爸这个前候补地主现中共党员,没激荡出半点人性波澜,这足以见出他信仰的坚定。必须说明,由于当时他被党派往大学读书,大学里的党领导比较迂腐,虽然教他阶级论,但人性论的余毒尚有残留,曾主动建议他回家看看。我爸谢过组织的人性,真诚地捍卫了党的阶级性,他表示,只有党是他的亲人,他爹他大哥只是敌人,除非工作需要,否则他不会再回那个罪恶的老家。工作没需要他回过东丰,五十多年里,他也就真没再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东丰距沈阳不足两百公里。
我指责过我爸冷血动物。他没不高兴,他很正经地做了两点解释:第一,人人都有局限,局限无以弥补,既然超越不了历史,时过境迁后,以打完一巴掌再送个甜枣吃的方式自我原谅,是稀释罪责,是为下一次屈从局限预留台阶,而他,更愿意让往昔那个过激承诺成为难收的覆水,既为汲取教训,以避免以后再陷局限,也为自行剥夺还愿的机会,以求更长久地自我惩罚;第二,这一辈子,至少四十岁前,他对他爹和他大哥,真的只有仇恨没有怀念,他发自内心地与他们划清了界限,可他们从来不放过他,总为别人打他充当暗器,他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引他们之火焚烧自己。基于我对他这个人的了解,我相信他这回的正经里杂质较少。其一,既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又为不失去内心的依凭,他对他青年时代即信仰并且追随的东西,必须持续地保持尊重,况且,这个东西的衍生品还给了他许多实际的好处——补充一句,对我爸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庞大的体系,不只是动听的口号或权宜的策略;其二,他始终相信,文化大革命的病毒会再度肆虐,他非常害怕他爹他大哥还纠缠他,尤其怕我和姐姐受他们株连——再补充一句,我爸知道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没说下一次“文革”也有打倒刘邓陶和粉碎“四人帮”,他的观点是,两片树叶差异再大,也都是树叶而不是别的。
翻过我爸的生命档案,从本质上说,我爸只是一个崇智的、向善的、对人类文明心怀景仰、对精神生活抱有热情的普通读书人,如果时代赐予他机会,他会乐于研究问题,如果时代切断他退路,他则甘为行尸走肉。
(摘自《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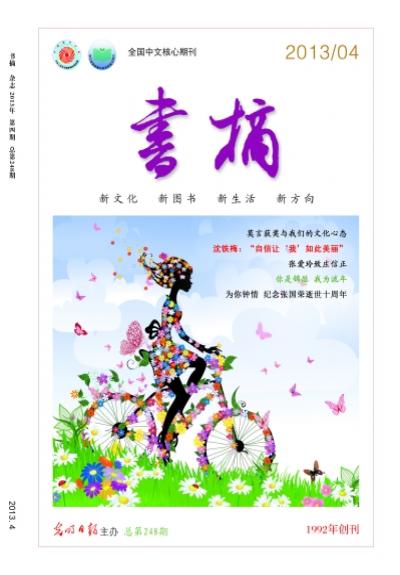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