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切都在变化,都在显露真形,都会余下一缕淡弱的尾音,唯有大自然给我永恒的启示。——作者
曾经:大地上的文友
我上大学之前没能成功地拜师,却得益于形形色色的文友。这是一想起来就要激动的经历。那时我在山区和平原四处乱跑,吃饭大致上是马马虎虎,有时居无定所,但最专心的是找到文学同行。我在初中的文学伙伴离我很远了,并且他常常有心无力,渐渐知难而退了。一说到写作这回事,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的人,他们都叫成“写书”,或者叫成“写家”,说: “你是找写书的人哪,有的,这样的人有的。”接着就会伸手指一下,说哪里有这样的人。
我在县城和乡村都先后遇到过一些“写家”,这些人有的只是当地的通讯报道员,有的是写家谱的人,还有的是一个村子里为数极少的能拿起笔杆的人。真正的文学创作者也有,但大多停留在起步阶段,就是说一般的爱好者。他们年龄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八十多岁。
不论这样的人住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只要听说了,就一定会去找他。有一次我知道了一个真正厉害的“写家”,他住在一座大山的另一面,就起早背上吃的喝的翻山去找了。原来这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白发白须,不太愿意说话。他年轻的时候在城里待过,所以算是经多见广的人。村里人都说他“文化太大,不爱说话”。他仔细问了我的前前后后,又翻翻我的“作品”,这才多少接纳了我。
原来他正在写的书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是“三部曲”。他将其中的“一曲”给我看了,我发现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主要记载了一生的经历,夹叙夹议。他说这叫“自传体”。其中我记得最有趣的是写当学徒的一段:东家女儿看上了他,他至死不从,以至于半夜逃离……“这闺女原是很美的。”他在一边解释说。
我照例坐下来读了自己的作品。他闭着眼睛听下来,像吃东西一样咀嚼着,又吞咽下去。这样半晌他才睁开眼,说:“你好歹毒啊!”
我吓了一跳。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在表达一种极度的赞扬。他伸手抚摸自己摊在炕上的作品,说:“你看,我写得多歹毒啊!”
那些年我发现散布在山区和平原的各种“写家”可真多,他们有的富庶有的贫穷,有的年纪大有的年纪小,但一律酷爱自己的文学:写诗、散文和小说;有的还写戏剧,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的车间或村子里演——看他们自编的戏剧简直有趣极了,那些特别的情节和场景永远都忘不了。有一次我被一位山村里的黑瘦青年邀请,说今夜村里就上演他编的一部大戏。
那出戏的演出离现在几十年了,记忆中内容大致是与村里坏人斗争、群众取得了胜利之类。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手拿一个大红苹果从台子一侧上来,而另一边是一对青年男女亲热地上场。“二流子”斜眼看着那边的两个人唱道:“我手拿大苹果,她爱他不爱我……”那婉转悲切的唱腔让我一直不忘。我无比同情那个失恋的“二流子”。
还有一次我住在一个小村里,房东的女儿恰巧就是一个“写家”。她刚十七八岁,公社广播站就已经播发她的好几篇稿子了。她胖胖的,穿了大花衣服,平时爱说爱笑,只是一写起来就伏在桌上,谁也不理,一边写一边流泪。我们交换作品,她喜不自禁,一边看我抄得整整齐齐的稿子,一边红脸掩面,说:“哎呀哎呀,你可真敢写啊!”我知道她看到了什么:那是写青年男女刚刚萌发的、若有若无的情感,是这样一些段落。
我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写家”是在半岛平原地区。记得我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人就不顾一切地赶了去,最后在一个空荡荡的青砖瓦房中找到了他。他几乎没怎么询问就把我拖到了炕上,幸福无比的样子,让人有一种“天下写家是一家”的感觉。他从炕上的柜子里找出了一捧捧地瓜糖,我们一块儿嚼着,然后进入“文学”。他急着先读,让我听。可惜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了,一摞摞积起来有一人高,字数可能达到了一千万字以上。这个人多么能写作啊,这个人的创作热情天下第一。为了节省纸张,那些字都写得很小。
天黑了,他还在念。一盏小油灯下,他读到了凌晨,又读到窗户大亮。奇怪的是我们都毫无困意。
那一天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大写家”,是一位必成大事的文学兄长。他大我十多岁,结过婚,只因为对方不支持他写作,他就与之分手了。他曾给我看过她的照片:圆脸,刘海齐眉,大眼睛,豁牙,笑得很甜。
分手的时候我在想,为了文学而损失了那么好看的一位女子,这值不值呢?想了一路,最后肯定地认为:非常值。
现在的标准
在三十多年前,每年都有全国小说评奖,一次评出二十篇小说。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哪一个作品能够得奖。就像打赌似的,每个人列出一个二十篇作品的单子,只等新闻联播公布结果。可见那时的文学公信力之强。一连几年,大家猜中的都在十几篇以上。这与今天完全不同。如今不要说在校的大学生了,就是著名的专家也猜不出。原因就是现在的文学标准改变了,变得空前复杂了。
有人可能说现在的作品多了,出其不意的情况也就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作已经是五花八门,这就不好掌握统一的标准了。其实文学怎么会有其他的古怪标准?它只能是一个文学的标准,只能是坚持这个标准的问题。如果社会变得混乱无序了,没有是非了,文学的标准当然也不会有。
有人固执地说现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因为随处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说不清了,无论什么事物,说好说坏都可以。还有人认为“真理”也是不存在的,世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这样的时代难道不是很可怕吗?因为到处都是这种“相对”,人们也就不再需要去追求真理了,因为凡事此一时彼
一时,可以得过且过。生活在这样的人群里还能再谈文学、还值得再谈文学吗?不可能也不必要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追求真理的族群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关于写作,没有文学的标准,那就一定会有其他的标准来代替,比如商业的标准、对某种利益集团有用的一些标准。这都与文学无关——不,这只会对文学产生极其严重的伤害和扭曲。文学是人的心灵之业,对文学扭曲了,对人也就扭曲了,这个社会也就变得畸形了。
过去我们大致都知道什么作品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现在则不知道了。那时候我们还幼稚,只二十来岁,没有写出更多的书,也没有读到今天这么多高论,可是我们还算清楚地知道自己向往什么、什么能感动我们,怎样的作品能够引领我们的心灵走向更美更善。现在反而犹豫不决了,我们有可能变得更高深了,文化的文学的视野也比过去变得开阔了不知多少倍,结果却变得这样的无所适从。这种现状降临到我们身上是真正的噩运:丧失了判断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法弄得清哪些是好的作品,哪些又是不太好甚至是很坏的作品了。
有时候我们刚刚被一部作品深深地感动过,比如说被它的语言、被它的故事和人物、被它蕴藏的某种东西给激发起来——可是我们一直信赖或比较信赖的专业朋友看了却很生气,说这分明是一部很坏的作品……
类似的例子或正好相反的例子数不胜数。这样时间久了,我们就给弄糊涂了,不断地怀疑自己。最后,我们不得不试着放弃一直秉持的一些标准。
有人会说世上再也没有比艺术这种东西更难掌握的了,它有一万个标准、有千变万化的奇特因素。可是我们也知道,它尽管复杂,仍然还要我们去读、去感受吧,仍然还要落在我们的良知里,被我们的知性过滤和筛选一遍吧。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怪异,也并不等于没有标准。
如今网络上滚动着无数的“文学”,书店和地摊上也摆放了无数的“文学”。各种读物像海洋一样涌过来,这一切在有标准的人那里哪怕稍作停留,也会让人心烦意乱。这种拣选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能把人累得崩溃。所以一个适时而至的办法,就是认同这个时代的无标准说。没有标准是最好的,最省心了,怎样都行。
也许现代真的不再需要标准,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来到了一个重商主义时代、物质主义时代,人们不需要文学也能活得挺好。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这大约也就是非人的时代了。动物不需要精神生活,只要满足了口腹之欲,它们一定是很高兴的、欢欢乐乐的。(摘自《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定价:3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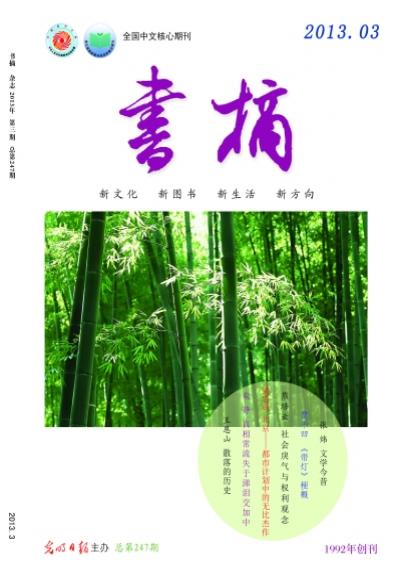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