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娃,原名理昭,是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的老伴;是十二岁就去了延安的老革命;又是晚年诗情迸发、“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诗人。她一生传奇,越到老年,越清醒。
我的老家在陕西临潼县离县城很远的双泉村,赵姓。爷爷那一辈,在村里是个大家族。爷爷、叔伯爷爷都住在一起。我离开这个家的时候还在母亲怀里,十来岁时回乡去看,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
那里是一处大庄园,并不和村里人集聚而住,距离村子大约还有一里半路。庄园的院子很大,有很深的院池,里面是一片片石榴、月季、玫瑰、刺梅、木槿。陕西以及甘肃那边有养玫瑰花的传统,可能是气候很适宜这些花的生长。特别是沐浴了春风、雨露,花儿们纷纷睁开了眼睛,能从春天开到秋天。花池中有排雨水的小渠道,花池四面是很高的台子,台子上,在房檐下,醒目地立着一排很粗的木柱子,柱子后面就是房子了,那的人称房子为厦子。院池三面是屋,记得当时的房屋满眼望去都是砖雕和木雕,那些雕着松菊竹梅、喜鹊登枝一类的镂空门窗与房屋融为一体,透着一种雍容和精致的生活气韵。现在人们见到这些砖雕和木雕,恐怕要当工艺品收藏了。我奇怪,我们家镂空的门和南方的那种窄条型门很像,到了夏天,为了通风,一对一对地并在一起开着,过堂风穿过,院内屋里又连成了一体。所不同的是,冬天为了暖和,那些镂空的门窗都糊上了高丽纸,这样一来,那些窗雕门雕更是醒目。
这大院最里面中间的一排房屋住着一家之主——我的爷爷奶奶。我爷爷这一房的儿孙辈,也就是我父亲和叔叔两家住在东厢房的一排房间;叔伯爷爷和他们的儿孙住在西厢房的一排房间。庭院后面不远处,有油房、弹花库,马厩、车库,门前有水井、水车,完全自给自足,无所不有。记忆中水井边是“水车嚯嚯,马蹄嘚嘚,井水湍流在铺满陈年青苔的木槽”。上小学时,我回过几次老家。院子的大门很厚,镶有大铁钉,我们几个小孩子一块儿推,才能推动,大门发出“吱——吱——吱”的声响,很好听。每当我回忆乡村那种特有的宁静天籁时,耳边老响起那座大门像唱歌一样的声音,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安静、祥和,老让我想到生活中的一种永恒。后来我到了延安,延安整风后,联政主任肖向荣对我说:“根据陕西省委对你们家的调查,你爷爷是个举人。农村人大多不识字,出了个举人,还不得记载下来。”
现在想来,那时的老家是处在较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我还没记事时,这个家已开始败落。我爷爷奶奶一过世,叔伯爷爷们赌博,分了家,输了牲口房产,大家庭就解体了。
我外婆家离我家有三四里路,也是种地的农民。有识字的人,但上的学都不多。小时候去外婆家,门很高,两边还有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外婆家的人肤色白,鼻梁高,眼睛也不很黑。我外祖父告诉我,我的曾外祖父那辈人是从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究竟是什么地方,他没有说。母亲曾对我说,她的曾祖父长得多么排场:脸特别白,黄胡子,蓝眼睛。印象中,我的舅舅们也都是高鼻子、深眼窝。还记得,那个村子里曾有个礼拜寺,在很高很高的台上,小时候我还时常去礼拜寺废墟玩耍。
我母亲说的话,很多词汇我不会说,但听多了也能听懂。比如,她说:“客立玛察!”就是让我快点。她说话时的用词,和我祖父家的人很不一样。
母亲好说自己荣耀的过去,她一生的荣耀就是出嫁时的风光。她说她出嫁时送嫁的队伍排得很长,抬着陪嫁的嫁妆、吹吹打打的人流,前面的都到夫家了,后面的还没有出村呢。她说:“到了你们赵家,每换一套衣服,就吹吹打打一阵;一会儿,当吹吹打打又起来时,又要换一套衣服。”早晨,她起来推开门,看到两只大鹅在门口把守,真是有意思!家人告诉她:“那是看家的鹅,生人来了它们要用嘴啄人呢!”那天早晨,撩开门帘,一阵香气扑面而来。呵!人家这院子里全是花儿,房前房后都是花儿!看到这些花儿,心情好愉快,但跟着就紧张起来,因为全家人都要来看她这新来的媳妇怎么扫院子,怎么端盆子,怎么做早饭,怎么着装。一招一式都不能出差错,否则一辈子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来。刚过门媳妇的一举一动,做活、待人接物、一切习惯都需经受婆家人的检验,得忍受各种品评,日子很不好过。母亲说,她出嫁算晚的了,过去的女孩儿十六七岁就出嫁了,她出嫁时已经十八岁。母亲说:“当我做饭时,要用荤油,有僮子端来;用素油,有僮子端来。从哪儿端来,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家里有油房,自家做花生油、芝麻油、大豆油吃,做棉籽油点灯用。”
母亲不识字,但会唱小曲。母亲从六七岁起,就要学绣红。绣衣服、绣鞋袜、绣枕头、绣帐子、绣被面,所有的绣品,一直攒到出嫁。到结婚时,在新房里布置起来展示,有点像现在的个展,让村里人观赏新娘的绣红水平。说着往事,母亲一副很自负的腔调,因为婆家村里人都认为她花儿绣得好,针线活也好。她把衣裳挂在院子里时,妯娌们经常偷偷拿去照着裁样子,然后再挂回来。我长大以后,看到过母亲过去的衣服,简直太好看了,上面绣满了花鸟。那袖边、披肩、帽子、袖筒、百褶裙等都绣满了花,局部或整个《西厢记》、 《蝴蝶杯》、《白蛇传》、《玉堂春》等都绣在了衣服上,细致、贵气极了。扣子是用铜丝做的,中间还有一个珐琅做的美人头。后来我们家在西安时,父亲一个同学的太太是日本人,和我们住一个院子,她看到母亲的绣品,都惊呆了,说太美丽了。
现在谈这个,不光是说我们家的过去,也是想说乡村那种自然生长的文明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人类为自己、为世界创造了多么精致、多么美、多么考究的文气、贵气啊,我们为什么要破坏它、贬低它、羞辱它、毁灭它,却以愚昧、愚蠢、野蛮、暴戾而自夸呢?
在我还不记事时,爷爷就过世了。我的爷爷有两个儿子:我父亲和我叔叔。我父亲从小读书,当了教书先生。我的两个叔伯爷爷嫌我父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心说,不能我们种地让他们家人吃,在一块过,太吃亏,就要求分家。分家后,最初我母亲凑合着自己种地,一个女人操持着家里的一大摊子。后来,我的叔叔也让村里的人挑唆要分家。父亲就把附近的乡绅、家族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找来,他说:“父母刚过世,弟弟还小,我不能把弟弟分出去,我不愿意分家。”父亲还当着大伙哭了,就像小说《家》里的大哥觉新一样,觉得自己有当兄长的责任。但是叔叔坚决要分。乡里的人就组成了帮助分家的“临时机构”,裁定什么给我叔叔家,什么给我们家。因为父亲不会种地,家里的牲畜、农具基本上都给了叔叔。我们家就留下了老房。尔后,父亲把我们全家接到了西安,老家的房子空了好长时间。
我们家的祖坟很大,好大一片地,约几十座坟,不知道有多少代人了。坟地里有好大一片柏树,风一刮,慢慢地摇,老柏树枝叶浓密,大风气流也很难摆动,似乎在告诉人们,它们自身太古太重了……正如我在诗歌《野土——“乡村墓地”》中写的:“我记忆的荧屏永远是松柏掩映,幽影悄寂,藤萝绕枝,木香悬空。……如魔似迷,幽玄冷森,叫人心跳却又亲近。”还有许多石兽,后来军阀混战,都毁了,我只记得有一只石羊还完整。父亲逝世后,就埋在这片祖坟。
老家的房子,后来被烧掉了。是一个叔伯亲戚过年时敬神,烧香点蜡,失了火。那时,弟弟在家务农。房子被烧时,弟弟正在邻村看戏,不在家。烧了房子后,面对一片废墟,弟弟伤心不止,精神受了刺激,自那以后,就变得很迟钝。
我父亲是个书生,先是在临潼教书,后来到西安教书。他人很内向,不大讲话,也从没有大声对我们嚷嚷过,总是慢慢地说。我母亲不识字,人却很外向,操持着里里外外的家务。那个年代,男人如果有事业或能挣些钱,娶姨太太是常见的。父亲是读书人,很传统,从没有动过娶小老婆的念头。
我们家人都到了西安,怎么弟弟还在农村呢?抗战期间,父亲已经过世,全家为躲轰炸,回了老家。但母亲一直住在外婆家,可能是她娘家人对新寡女儿的疼爱。后来解放了,要给她分地,她就带着弟弟从外婆家回到了我们老家。
(摘自《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定价:35.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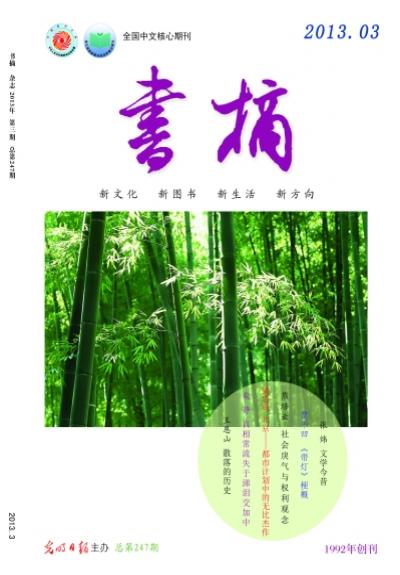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