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一,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嚷嚷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心想,各有各趣味。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
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
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
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2005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590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60%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入,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谈不下去了。
2006年,48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入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
她是15年来,这个国家第43个被暗杀的记者。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16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
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2009年4月,我去重庆调查。一块土地拍卖,三年不决,工厂因此停产,一些工人写信给我们希望报道,信上按着很多红指印,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关键人物叫陈坤志,他被指证操纵土地拍卖。
“他有枪,指着人的头让人签协议。”有人说。这人自称被他拘禁过,人证物证都有。领导知道采访有危险,让我们把手机都换掉,用一次性的卡,说:“不采访他,节目能成立么?”
“基本的证据够了。”编导剑锋说。
“那不采也成,安全第一。”领导说。
其他采访结束,够用了,行李装上了车,飞机过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几个在宾馆坐着,面面相觑,都知道对方心里的话:“采不采陈坤志?”
不采节目也能成立,但是个新闻人,都放不下。
“那就电话采访吧,采完走。”剑锋说。
我打了他电话,结果他说“来吧”。
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那么多这样的人居然会接受电视采访,“60分钟”的记者华莱士说过一句话:“因为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采访时,他几乎是得意洋洋地承认了所有的事实,包括操纵拍卖,收了一千七百多万中介费用,但“操纵拍卖”在他看来是一次正当劳动,他甚至自觉有道德感,因为做到了“对出钱的人负责”。至于那些被他拘禁要挟的人,他认为都是想从中多捞一把的脓包,而他拯救了整件事,所有想搞掉他的人只像“苍蝇一样嗡
嗡嗡”,都得不了逞。
我们坐在巨大的穹形高尔夫球场边上,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英雄故事的听众,我怀疑他知不知道正在说出的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问过律师了,我做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他歪着头,脸上几分得意之色。送我出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顾忌了:“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后来的调查和审判中,他被判处死缓。
但这事没有完。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分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印证后,我才发现,拍卖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确实不是单纯的受害人,他们最初都是要从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过,在丛林法则下,大鱼吃小鱼,最后被吃掉了。
那些向我们举报的人领头闹事,把一个厂长赶下台,焊上铁门不让厂子生产,私卖设备分了一部分钱,不久又把另外一个厂长赶下台,又分了一部分钱。等陈坤志把拍卖控制成交后,他们以暴力相抗,拒不交地,把厂房和荒地拆成一个个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笔钱,都是这十几个人掌握了……这些人不是我出发前想象的受害工人阶级,没有群像,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穷苦人群体,只有一个一个诉求利益的人。
采访的时候,各方人士都写了遗书,认为自己将被黑帮分子所害,包括陈坤志也说“我被黑社会威胁”……我没克制住好奇,请每个人都把遗书念了一遍,每个人都声泪俱下。
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
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2012、2022,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
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查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
我把这些写在博客里,但有读者问:“记者价值中立并不等于价值冷漠,难道这个职业没有道德吗?”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应国务院新闻办的邀请,我去跟政府官员座谈。其中一位说到他为什么要封闭新闻,“因为不管我放不放开,他们(记者)都不会说我好。”底下人都点头。
到我发言,我说,说三个细节吧。一是有一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是CNN的主持人卡弗蒂用“暴徒和恶棍”描述中国人的“辱华事件”。我跟美国街头遇到的黑人谈这事,他说我们很讨厌这个人,他也侮辱黑人,但他不代表CNN,也不代表白人,他只代表他自己。我又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谈到美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有明显的挑衅与失衡处,他们灰头土脸地说,“他们对我们也这样”,但他们接受记者的职业角色,因为“这是宪法给他们的权利”。
第二个细节是,有一次雪灾刚过,我去发改委采访一位官员,当时网上批评发改委在雪灾中有应急漏洞,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答完长出口气,说:“总算有人问我这问题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一个公开解释的机会。
如果一直封闭新闻,结果就是大家都会相信传言,不会有人问你想回答的问题。
第三个细节是我在广东采访违法征地,刚坐下问第一个问题。这位市长就火了:“你居然敢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你们为什么要违法批地呢?”
他站起来指着摄像机爆粗口。
我提醒他:“市长,正录着呢。”
“你给我关了!”他就要扑到机器上来了。
他怒气冲冲:“我没见过敢像你这样提问的记者。”
“我也从来没见过你这样连问题都不敢回答的市长。”我当时也有点急了,第一次直接跟我的采访对象语言冲突。
我们第二天一早的飞机走,准备睡了,晚上十一点,他大概是酒醒了,脸如土色地在门口等着:“再采访我一次吧。”同事们对视一眼,说“别理他了”。
上午的采访都已经录下来了,他是漫画式的形象,快意恩仇,而且充满戏剧性,观众爱看。但我们要的不是他的失态,而是信息。陈威老王架机器,我洗了把脸,说“坐吧”。采访了四十分钟,他说违法征地的决策程序和地方财税的压力。采访完出门时我对他说:“我可以不采访您,这您知道。但我采访了,是因为我尊重我的职业,也请您以后尊重记者。”
说完这三个细节,我说:“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我采访一个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45分钟,很坦率。
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
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
“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
他说:“准确。”
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
Ann说:“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摘自《看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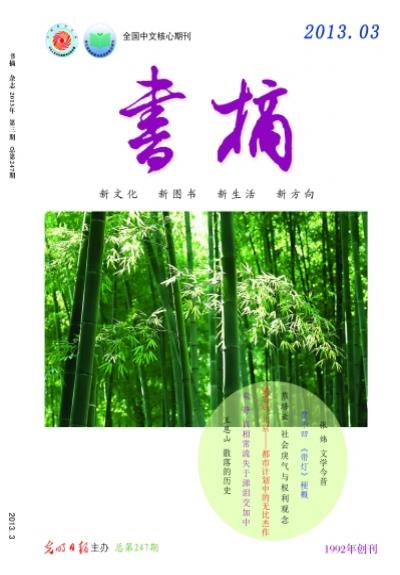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