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从石景山钢铁厂监督劳动中被解放出来,进入文化部核心小组,后来成立“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勇批极左。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胡耀邦通知黄镇部长说:这回文化部的班子是得人心的。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时,同贺敬之一起,早就看中他。
贺敬之和密友冯牧领导的“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集中了一群骁勇的理论家,他们为拨乱反正勇敢地出击,发表了不少犀利的文章,后改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我们《文艺报》复刊,正好坐落在马路对过,两家吃饭在一起,不吃饭时互相串门,指天画地,像沙龙,一家人似的,家长是冯牧。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冯牧、贺敬之就在我们的身边。
贺敬之16岁投奔延安,被“抢救”了一年,故而积极为受迫害被禁锢的作家落实政策;周扬认为他一贯偏右,其实是周扬自己从来偏“左”;在为胡风两次平反、支持丁玲二次平反以及恢复冯雪峰名誉的过程中,果然遇到阻力,他的工作很难做。阿垅鲜血淋淋的申诉直言不讳: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全然是捏造的”,“我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贺敬之亲见之后泪流满面。为丁玲彻底恢复名誉,贺敬之态度坚决,当面纠正周扬说:冯达叛变丁玲并不知道,延安时期已经有结论,陈云经手的,可以作证;他为天安门诗歌叫好,奋力推倒“教育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组织文艺界开展石破天惊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举办“理论工作务虚会”,筹办全国文代会等,以对党忠诚负责的精神参与其中,呐喊,解冻,开路,工作繁重,任劳任怨,口碑甚佳。贺敬之在万人大会上宣布平反名单,认为“右派”中绝大多数不是右派。
贺敬之遭人诟病是在调任中宣部副部长、特别是邓小平严厉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这时,文艺界啧声时起:“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甚至骂“贺敬之是‘左王’!”他感到十分委屈。
不管人们私下怎么议论,贺敬之不但忠实执行党的文艺政策,而且参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党的总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但要准确、完整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人心思变,政策不能不起变化,连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都坦率地承认他自己并不清楚,至于什么是“朦胧诗”,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现代派”,什么是“异化”、“人道主义”,都不是用简单的姓“社”还是姓“资”那种“兴无灭资”的框框生搬硬套就能定性的。太需要争论了,而那时(不得已)采用的策略是“不争论”,甚至从中宣部传出这样一种理论:“经济上反‘左’,意识形态上反右。”更何况,尽人皆知,当时的上层,已经出现起码两种声音,一种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声音,一种是四次“万言书”的声音,而两种声音,似乎对于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意见却完全一致,但在两届总书记那里又出现分歧。到底怎么科学地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聚讼纷纭,尽管贺敬之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会出现‘四人帮’无情打击那种极左的错误”,但接着又说“也不会出现过去搞运动中的右的倾向”。这种政出多门、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让贺敬之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将上上下下统一起来又常常统一不起来的时候,便陷于两难选择的痛苦之中,陷于坚决贯彻却受到抵制和误解的烦恼之中。尽管,这位延安的老革命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始终同情最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愿意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然而,处在“多变、变多”的形势下,要把是非摆平,难乎其难。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在中央党校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胡乔木坚持说周扬不听招呼擅自发表,周扬坚持说他从来没有听说不让发表,两人相持不下时,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只好骑墙打圆场。事涉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和文艺界的重要头面人物,贺敬之的辩证法不够用了,伤透了脑筋。贺敬之和他的老上级周扬失了和气,和作协党组的张光年、唐达成搞得很僵,和冯牧(他延安以来的至交)完全闹翻(我们苦苦相劝双方都无动于衷),结了仇,到死不相往来,扬言一方死了,另一方绝不参加追悼!但冯牧病后柯岩四处求医,冯牧病危,柯岩代表贺敬之趋前探视,紧紧握住冯牧的手,冯牧泪流满面。
1983年,冯牧、刘锡诚和我三个人计划编辑出版一套包括二十多位老中青评论家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我提议为贺敬之自选一本,冯牧、锡诚均表赞同。我找贺敬之,他没答应,而且很不屑,说:要出就在红旗出版社出,你们出我宁肯不出。我知道他是冲着冯牧来的。我们创办《评论选刊》,老一辈知名的评论家都应约题了贺词,约他时却碰了钉子。他没有答应我的请求,解释说他很为难,并说他会给我写信的。不几天,他竟把题词送来,态度鲜明地提出“面向现代化,开拓新领域,探求新方法”,表明他十分明智的价值取向。其后,他果然给我写了封长信,手写的,三张,龙飞凤舞,书法艺术,很耐看。信中陈述战友间的分歧,申明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同时表明自己上任以来对于文艺界的保护和支持,甚至甘冒风险。从这封信既看出贺敬之的诚恳,也看出他的苦衷,读来叫人伤感。
1982年周扬决意制定新的《文艺十条》,这一工作后来转由贺敬之接手负责,我被召参加讨论,共十人,一人负责起草一个条目。我负责起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语涉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复杂矛盾,完稿上交,未获通过。一个雨天,贺敬之参加讨论,着重强调“二为”、“双百”方针,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革命传统,反复提醒作家首先要做一个革命者。当我们提及巴金的“讲真话”和他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问题时,贺敬之极其肯定地说:“巴金只能算是党的同路人……”贺敬之亲口对我说:“在中央没有明令撤销之前,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继续执行小平同志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有的指示和讲话;中央明明发文严厉批评作协的四代会,作协不传达,不按中央的方针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所不容的;可是,要是按中央的方针办事,就会遭到不少人的指责和谩骂,工作难做!”还说:“我不同意禁演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不赞成以右批‘左’,不批准把美学范畴的(王蒙等概括的)‘文学三无’作为自由化来批,不同意开除刘宾雁的党籍再把他从中国作协的副主席里除名,我做了多少耐心的说服工作,难道我体谅作家、保护作家的用心还不明显吗?难道无原则的迎合、吹捧、赶时髦就该听之任之?”他不解地说:“真不明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解放文艺思想的大原则下,我同他们到底有多么严重的分歧!”
可是,没想到,思想界、文艺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
1982年高行健的新潮话剧《车站》在内部演出后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时,他持反对态度,说话很难听,次年,《车站》被禁演。可是,当年内部放映《太阳与人》时大剧作家曹禺说:“我愤怒!我真想跑上去一头把银幕撞个窟窿!……”贺敬之很不以为然。
贺敬之被人敬重的同时遭人怨怼,但他不存心整人,不搞阴谋诡计,所以受到极大伤害的同时受到极大的尊敬。他说过:我是一个诗人,多次挨斗,“文革”老账新账一起算,揪来揪去来回斗,在周总理关怀下返回《人民日报》,又被江青明令下放首钢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我贺敬之才得以解放,我为什么要整人呀!他叫苦说:“人言可畏,人言可畏!”一次聚餐会上,我与贺敬之同桌吃饭,我向他极力宣传“口条”之如何好吃,他很不高兴的样子。又一次,枣庄画家画展,我又与他比肩就餐,我说这里的酱鸭舌可是一道名菜,贺敬之大为不悦,气狠狠地说:“巧舌如簧,我最恨!”众愕然。
贺敬之冥思苦想,把党的方针路线编成像《二十四节气歌》那样的24字诀以求推广,(即“三四精神,一二路线。解求拨反,持展强善。两线两大,始终一贯。小草远志,力微心健”。)把三中全会、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善党的领导等等全包括进去,可惜,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而他概括文艺方针路线的“二为、二百、小二为”倒是传过一阵。在他的治下,《中国文化报》于1992年发生“6·24”语录事件。那天的《中国文化报》以特大字号《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指示》为通栏大题刊登了两大版“中央有关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决议”的文摘和语录,同期发表由该社社长撰写的大字标题的社论《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异乎寻常,当即被中央发现和制止,派工作组进驻报社调查处理,贺敬之一时懵了。
从诗人和《白毛女》的主要词作者,到“胡风分子”,到“右倾”、受处分,到监督劳动,到部级官员、“左王”,再到是非缠身,贺敬之颇具代表性,说到底,是个悲剧人物。贺敬之接管文艺以来,众声喧哗,歧见丛生,有人说他极左,有人说他老右;有的说他是官僚,有的说他仍然是个激情诗人,不过书生气;有的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强调“三中全会路线”,圈内的人称做“‘说三道四’之争”。贺敬之一直被“说三道四”所困惑,忠诚、坚守,却痛苦。
(摘自《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三联书店2012年6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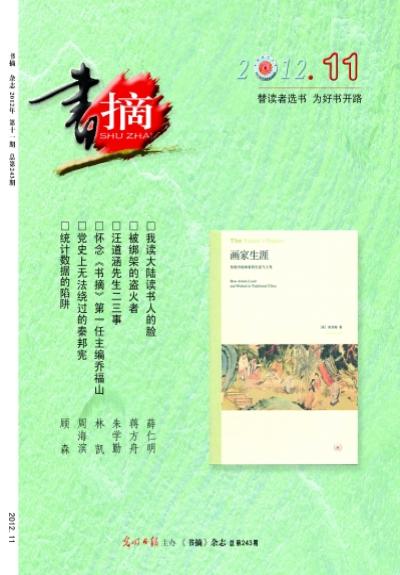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