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网这种沟通方式的全球化,导致“疆界”概念陷入危机。疆界的概念和人类历史同等古老,甚至和所有动物一样由来已久。动物生态学告诉我们,每种动物都会捍卫自己的地盘,尊重其他同类的领地,这个认知根植本性之中,当它在自己的地盘内时才会觉得安全自在,而且如果谁胆敢闯入,它就将对方视为死敌,非得斗个你死我活不可。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国家政体”这个原本相当清晰的概念也进入危急状态。因特网这种新发明不仅让我们可以跨国越洲成立多语聊天室。所以今天,位于波美拉尼亚(Poméranie)的城市可以轻松和西班牙内陆的艾斯特雷玛都拉(Estrémadure)的另一个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只要人家能在网站上找到两城具有的几个共同点即可。此外,穿越国界的高速公路亦是令疆界消弭于无形的一大原因。今天,在已经几乎无法控制的移民潮中,罗马的某个伊斯兰团体要和柏林的某个伊斯兰团体搭上线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疆界的消灭却引发两个彼此对立的现象,一方面,如今已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够阻止国民知道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就算独裁政权也找不出可令人民与外界讯息隔绝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往昔国家机器对于公民所进行活动的严格监控这项权力也已由其他权力中心接管。这些权力中心以高科技为基础,就算手段不是百分之百合法,它们也要知道我们写信给谁,我们买了什么,我们曾到哪里旅行,我们对百科全书哪些领域的知识很有兴趣,甚至连我们的性倾向也被弄得一清二楚。
还有那些可怜的恋童癖患者,以前他们大可躲在自己的小村落中,尽可能掩藏自己变态而强烈的欲望,可是今天他们受到鼓舞,大可在网络上大胆暴露自己难以启齿的秘密,但得冒着性倾向为人窥知的危险。
珍视自己个人隐私的公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倒不是抵御黑客入侵,因为后者和横行在大道上专门抢夺商人财物的土匪相比,其实人数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危险;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反而是抗拒神奇科技,那些用于搜集我们每一位资料的设备。
最近有个电视节目正在说服全世界民众,说“老大哥”这种情境有可能发生,前提是当有些个体(经由一种虽叫人遗憾却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决定被一大群人窥探监视。然而,这并不是奥威尔小说中的“老大哥”。
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是数量有限的特权者窥伺人群中每一个人的杰作,而且是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进行。《1984》里的“老大哥”并不是电视机,也就是数以百万计窥视者观看唯一的暴露狂。那是边沁笔下的“敞视设备”,里面有许多守卫不断监视一名罪犯,而且不被人看到,也不可能被人看到。可是,在奥威尔的作品中,如果所谓的“老大哥”是斯大林式“小爸爸”的寓言,今天观察监视我们的那个“老大哥”既没有特定长相也不是哪个个体,那是全球经济的总体。和福柯的“权力”概念相同,那不是个可兹辨认的独立体,而是一系列中心的总和。这些中心接受游戏规则,彼此扶助到了如下地步:一个替权力中心监视其他上超市购物同侪的人,自己在旅馆用信用卡付款时也会遭受监视。当权力没有脸庞长相时,它就变得不可征服。或者,至少变得很难操控。
让我们回到“隐私”此一概念的源头。在我出生长大的城市中,每年都要表演所谓的“杰林多”(Gelindo),那是伯利恒的牧羊人在救世主出生时表演的滑稽宗教剧,却同时又像是发生在我土生土长的地方,仿佛就发生在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农村的故事一样。事实上,这个剧种是以方言土语演出,而且发挥了极大的喜剧效果,因为剧中人物说如果要去伯利恒,就得绕道塔那罗(Tanaro),那显然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或者演员也会借古讽今,把当时政府法令规定的疏漏之处都算在暴君希律王头上。至于角色,喜剧以从头坚持到尾的极度活泼,表现了北意大利皮埃蒙(Piémont)地区人民的特色。根据一般传统看法,那里的人一向封闭,非常重视自己的隐私和感受。
这出戏演到一半时自然会出现三王来朝的情节:三王遇见其中一位名叫玛菲欧的牧羊人,并向他打听前往伯利恒的道路。那个牧羊人耄耋昏聩,只回答不知道,但要他们去问自己的主人杰林多,说他再过一下就回来了。后来杰林多真的回来,在途中遇见三王,因此三王之一便问对方是否便是杰林多。
现在让我们觉得趣味盎然的倒不是杰林多和三王间的对话,而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杰林多问那些牧羊人,那个人是如何知道自己的名字,而玛菲欧也承认是他告诉对方的。杰林多闻言勃然大怒,并威胁要赏他一顿毒打,因为根据杰林多的看法,一个人的姓名是不能和铜钱一样四处流通的。
姓名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旦将它公之于世,那么拥有这姓名的人就仿佛丧失了一部分完整的自我。杰林多不可能使用诸如“隐私”或“私生活”这类词汇,但他实质上捍卫的,的的确确就是那种价值。假设杰林多能掌握更细腻复杂的语言,他应该会说自己偏好“不招摇的方式”,讲求“含蓄”;换句话说,就是他要捍卫自己的“隐私权”。
我想提醒各位读者,捍卫自己的姓名并不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做法。1968年学运进行到如火如荼时,那些挺身而出的学生报上姓名时不是叫保罗就是马尔切罗或伊瓦诺,他们根本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这种习惯其实合情合理,因为他们害怕警方会按图索骥,将他们以教唆暴动的罪名逮捕。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是种时髦潮流,那是游击队在丛林里打仗时留下的习惯。他们彼此互称诨名,唯恐真实姓名一旦泄漏出去会对远方的家人不利。
就算现在,在电视或电台的叩应节目中,打电话进去的人也经常下意识地流露出想藏起真实姓名的欲望,然而,他们其实只想表达一些并不违法的意见或甚至参与游戏而已。也许那是种出于本能的胆怯,所以要在主持人的敦促和鼓励下,才勉强说出像是从帕维亚打来的玛儿切拉,从罗马打来的阿加塔,或戴尔莫里打来的史匹里狄欧尼这类依旧含糊不清的叫法。
有时,保护自己姓名的举动已几近懦弱行为,表示没有能力担待自己行为应负的责任,以至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羡慕那些民众经常连名带姓公开介绍自己的国家。可是,如果捍卫人名所包含之自我这一习惯,看来怪异甚至有时理由并不充分,那么捍卫自己的隐私就绝对不值得大惊小怪。从远古以来,例如“在家洗脏被单”、“家丑不可外扬”等不也是大多数人的金科玉律,甚至今天连洗“干净被单”可能还是要在家里进行,所秉持的名义无非是保卫自己隐私的坚决态度。除非法律明文规定,否则人们不会轻易说出自己的年纪、疾病或收入等高度私密的讯息。
那么,这种含蓄保守的疑虑态度是从何而来呢?当然是从那些想要保持商业交易机密的人而来,从那些不想被他人偷看自己私函的人而来,从那些暂时不想将自己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的人而来。
而这一切,我们都是中肯且确切能理解的,甚至国家还制度化地保护公民拥有隐私的权利。可是真正会诉诸这项法律的人有多少呢?我个人似乎觉得传媒、报章、电视和因特网等诸多悲剧中的一项便是大家对隐私权的放弃。
放弃这项权利最极致的表现,从病理学角度观察,是暴露狂。然而,我觉得很矛盾的一点是,在一个暴露成性的人充斥的社会中,我们却又要孜孜不倦,为捍卫个人的隐私权而奋斗。
我们当今这个年代的诸多不幸之一便是:将这种宣泄的需求(大部分是有益的)转化为八卦新闻,转变为飞短流长。
典型的飞短流长是流行于乡下街坊邻居间的东家长西家短,也可能是城市里大楼管理员或是酒吧咖啡馆里的闲言闲语,但这些毕竟都是社会凝聚力的展现。不过,人家说长道短时绝对不会说张三李四身体硬朗、财源广进或幸福快乐的话;要说就要挑别人的毛病,某甲某乙干了什么蠢事,或者他们家里遭逢什么变故等等。
说人闲话的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受害者的不幸,因为东家长西家短倒不见得总是从蔑视角度出发,它甚至有引发悲悯的功用。有时这种流言蜚语发生时,受害者未必在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以至于他们能够没听见那些语言而保住面子。
当受害者听到关于自己的闲言闲语,因而没办法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时,冲突就发生了(“你这蛇蝎心肠的东西,我知你暗中说我……”)。口角一旦发生,原本口耳相传的秘密就变成尽人皆知的消息。受害者于是变成人家的笑柄或舆论谴责的目标,而那些加害者也没有进一步的话好说了。而且,为了让闲言闲语这具有社会排气活门的功能维持完整无损的状态,所有人,包括受害者和加害人都要尽可能克制持重,共同保有一个神秘地带。
现代八卦首度出现得归因于报刊。以前虽然也有这种现象,但那些是专门的刊物,专门报道一些因工作性质而出名(像是男女明星、男女歌手、被流放的国王、花花公子)之人士的传闻,可是那些人是出于自愿让人拍照或吐露心声。但后面这类型的杂志其游戏功能如此明显,以至于读者也很清楚,假如某位知名作家和某位女子被人拍到在餐厅一起用餐的照片,这并不意味他们两者之间萌发出“带有爱意的友谊”,而极可能是这类刊物一手导演安排的场景罢了。这类出版物的读者如果要求的不是真理,那么他企盼的便是娱乐。就是这么单纯。
报刊一方面要抵抗电视的竞争,另一方面又要保留相当可观的页面给广告,以便广告利润可以维持公司生存。甚至那些在读者心目中被归类为“严肃正经”的刊物,或包括日报在内,也不得不越来越关切社会事件,连花边新闻、流言蜚语都登上页面。叫人尤其惊讶的是,如果硬是挤不出新闻,那么还有自己杜撰新闻的下策。
杜撰新闻并不代表向大家宣布一件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而是将原本不该归类为新闻的东西提升到新闻的地位,比方哪个政治人物在度假期间不经意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或表演艺术圈子里发生的点点滴滴。于是闲言闲语一跃而成为具新闻性的事件,而且大摇大摆侵入那原本不受社交界好奇的领域,把例如现任国王、政治或宗教领袖、共和国总统甚至于科学家都一网打尽。
在蜕变的第一阶段中,以前要咬耳朵窃窃私语的事现在可以高声喊叫出来,结果加害者、受害者,还有对这些事完全不感兴趣的部分民众全知道了。长此以往,八卦便丧失了往昔作为秘密的那份魅力与力量。然而,受害者却也出现了新形象:他不再是被同情可怜的对象,因为他就是出了名才变成受害者。成为公众八卦的对象,逐渐俨然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表征。
接着便是八卦现象转型的第二阶段。这时电视创造了一种新形态节目,播出的不是进一步抖出内幕的加害者,而是他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甚至高高兴兴叙述自己身为受害者的感受,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可获得等同于明星或高官权贵的社会地位。在电视节目里说的流言从来不会针对不在现场人士而发:通常是受害者谈论自己,向大众吐露自己的私密经历。
所有流言的主角通常是第一个获知那项流言的,而大家也都知道他已听闻此事。他不再是什么暗中传播耳语的受害者。因为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什么是秘密了。人家再也无法对受害者如鲨鱼见血般地猛烈攻击,因为他们既然赤裸裸地和盘托出自己的秘密,那就是勇敢到自己做自己的刽子手。社会大众甚至连要同情他都不知该从何处着力,因为他已从自己的告白或忏悔中,得到声名大噪这令人羡慕无比的好处。于是,蜚语流言至此便丧失了作为社会价值的本质,并演化成毫无用处的表白。
我们不必等到“大哥”这类节目的出现才能见证流言现象的大幅转变。“大哥”这类型的节目将那些透过出于自愿而加入心理医生病人行列的人摊在举国上下的偷窥心态前。好几年来,有许多不被同侪视为心理状态失衡的人也纷纷出现在荧光幕上,和自己的配偶开诚布公讨论彼此各搞外遇的不忠行为,和自己的婆婆吵上一架,或以绝望的心情追忆那狠心抛弃他或她的无情女或负心汉,甚至有人在现场互掴耳光,甚至毫不留情面地指责对方该为离婚负起全责,谁叫他阳痿不举呢!
如果说,在以前私生活是如此隐秘,以至于秘密中的秘密从定义上来讲,就是听取告解之神父的秘密,可是今天,“告解”这个观念早已荡然无存。
可是,更糟的事还在后头,因为在披露自己可耻的隐私后,平凡的男男女女一方面娱乐了大众,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曝光的需求。然而往日所谓“村里的白痴”这种小人物,今天也被拉去摊在众人面前。只不过今天或许受到《圣经》救世主的微言大义影响或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们将其改称为“村里那个头脑简单的人”。
所谓的“村里那个头脑简单的人”在往昔的典型形象是:因为不受造物者眷顾而在肢体或精神上有所残缺;他们经常光顾村里的酒吧,而且总有铁石心肠的村人故意买酒让他喝醉,然后令他做出有失体统或令人作呕之事。我们注意到,在那些村里,这种“头脑简单的人”大概也能模模糊糊感受到别人当他是“傻瓜”,不过他也乐于配合,因为这样可以免费喝醉,而他的“头脑简单”,从某个角度看来也是种暴露狂。
时至今日,被电视报道出的“村里那个头脑简单的人”已不是你我般的普通人,也不像上电视指责妻子红杏出墙的人。他的处境是在一般人之下。他被邀请上脱口秀节目,参加益智节目(正因为大家要看他头脑简单到什么程度)。获邀上电视节目的“头脑简单”人物智能未必低下。那可能是个心智怪异的人,比方宣称自己发现“失落约柜”的人;或者发明新式移动方式、年复一年去敲报社大门要求报道或前往专利局要求注册登记却不受理会的人,然而突然哪天他走运了,大家开始认真注意他的发明;那也可能是位只在假日才提笔写作的业余作家,在作品一再遭退稿后终于明白,若想出名,其实不必择善固执非得写出什么旷世巨著不可,其实只要上电视节目时扯下外裤,在文化性节目中口吐粗言便可一夕间名闻天下;或者也可以是首都以外其他县份的才女,一上节目就专门卖弄些古文废字并声称自己具有第六感,可以感受别人感受不到之事。
以前,当酒馆中的伙伴对村里头脑简单的人做出逾越分寸的事,强迫他做出叫人难堪不忍的动作时,总会有人出面干涉制止,这个人也许是村长,是药房老板或是受害者家族的一位朋友。他们会拉着那可怜人的手将他护送回家。反过来看,在电视上被公开观看的“头脑简单的人”一旦录像结束时,是没有人会保护他、送他回家的。结果,他的身份就像古代竞技场里的角斗士或死囚,功能只在满足观众的好奇心而已。社会工作者将心力投注在防止有自杀意图的人将心一横酿成悲剧,或协助毒瘾者避开堕落人生重返正常生活,但他们可曾帮助这些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弱势者和边缘人?这社会充其量只会如往昔鼓励侏儒或长胡须的女人到游乐园供人观赏那样,用赚取生活费的方式鼓励上述边缘人去做同样的事。
这很显然是罪过,不过我这文章的主题倒不是要鼓吹大家保护那些弱势族群(虽然有关当局应该拿出魄力照顾他们,因为那是剥削弱者的行为),我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这种“头脑简单的人”因出现在荧光幕上而有了荣耀名气后,成了普遍的模范。如果他做得到,那谁做不到?暴露弱势的人会让大众死心塌地相信,没有任何事物,即便是最可悲的不幸,有维护隐私的权利,而畸形弱智本身是可以得到报酬的。
视听媒介的力量果然不容小觑:只要那种不幸人士一出现在电视上,那么他就立刻变成有名的弱智者或畸形人,而这份名声又和广告的炒作机制同流合污,将这些人推到学术研讨会上,推到庆典活动舞台上,甚至令其沦为性欲的玩物。从定义上而言,是“畸形”这个概念变得畸形了,从此一切都是美的,连畸形也不例外,而且还差点被高捧到荣耀的地位。你们可记得《圣经》里的话?(那个心智不正常的人心想:神不存在)而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头脑简单之人可以高傲地向四方宣告:我存在。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因特网上。检视许多网站的首页可以发现,某些网站设立的目的只在展示极无趣味的正常现象,如要有趣,所呈现的只能是不正常之事。前些日子我找到某人的个人网站。他在首页上放了(或许直到现在尚未移除)自己结肠的影像供人点阅。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来,大家可以直接前往诊所要求医师用直肠镜检查直肠。这种先进仪器前端安装了一个袖珍摄影机,而且病人可以亲眼在彩色小屏幕上,看着那支带摄影机的侦测仪器深入自己体内最隐蔽的地方,以及那地方所藏有的秘密。通常检查后几天内,医生会用最谨慎的态度将一份附有彩色结肠照片的检验报告交给病人。
问题在于,除了肠癌末期的患者外,所有人的结肠看起来都一样。而且,就算真的有谁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对自己结肠的彩色照片产生兴趣,他对别人的结肠相片照理说应该不会有同样的兴趣才是。可是,我提到的那位先生却不怕麻烦地,在自己网站的首页上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结肠的照片。很显然,这是个生命不曾赋予他什么东西的人,没有后代可以继承他的姓氏,没有爱侣对他的脸孔产生兴趣,也没有朋友和他一起分享度假时拍的照片,基于这个理由,他才绝望地出此下策,凑合着把结肠照片送上网以求那最少的一点点能见度。在这种例子中,就像其他甘心放弃自己隐私的例子,其实包藏的是一个个绝望的深渊,不至于引发我们关怀注意的空洞。可是那些暴露自己隐私的人(而这就是他的悲情所在)不允许我们忽略他的耻辱。
我还可以长篇大论继续分析那些兴高采烈放弃自己生活私密面的人。平时我们在街上、在餐厅或火车车厢中总会听见别人用手机讲自己最私密的事情,或者干脆透过卫星公开自己爱情悲剧的过程。这些人并不是出于紧急状况向人讲述事情,否则,珍视自己秘密的人应该会尽量压低声音说话。但他们只是急着要让在场每一个人知道,他们对自己的那家冰箱公司下达了重要指令,或是买卖了哪只股票,或者正在主办什么研讨会,或者他们被情人甩了。他们付钱买来电话并交月租费,这是他们向世人展示自己私密生活的有效工具。我花这些时间分析讨论上述大大小小各种心理和道德伦理的畸形现象,并不是为了自娱。我的想法是,监督我们私生活之当局的义务,不仅在保护那些愿意被保护的人,同时也得捍卫那些再也不知如何捍卫自己的人。
我甚至想表达,经由那些暴露展示狂的行为,我们知道对于私生活的侵犯不仅是种罪过,而且还真是社会的恶性肿瘤。而应该最先受到正确观念教育的就是儿童,以便我们将他们从父母辈那些堕落的坏榜样中拯救出来。
可是如今正在形成的循环是恶性的。对于私生活的侵犯已令社会大众习于它被剥夺的事实。我们当中已有不少人养成一个观念:保有一件秘密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它公之于世。正因如此,连带产生了一种现象:有人会在电子邮件或电话中公开说出自己要说的,因为他们确定,凡是不闪烁其词、不遮掩的陈述是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的。
渐渐地,许多人都养成好暴露的习惯,因为他们认清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全闭锁在私领域中,而当保密已不可能,那么就没有任何行为会成为丑闻了。可是逐渐地,那些侵犯我们隐私的人便会说服自己,说反正受害者自己不也默许这种窥伺,于是接下来他们的行为就更肆无忌惮了。
(摘自《倒退的年代》,漓江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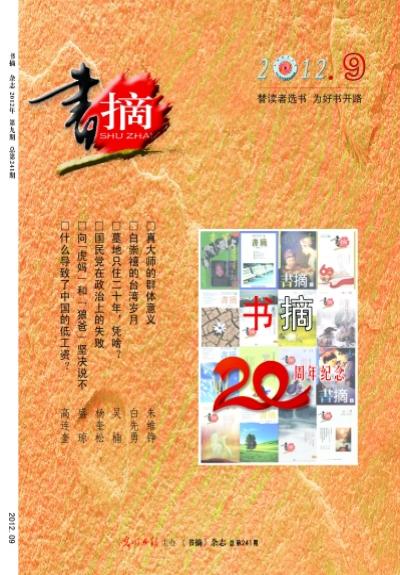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