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 我叫阿城,姓钟。1984年开始写东西,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
我出生于1949年的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十多年。1979年退回北京,娶妻。生子。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上世纪80年代末赴美,至今写过多种剧本、小说、传记类文字。
登琨艳 1951年生于台湾高雄。1971年屏东农专农艺科毕业,1975年赴东海大学建筑系旁听,师从著名建筑文化学者宝德先生。1985年成立个人设计工作室,从事室内、环境景观、公共艺术等设计工作。陆续创立、经营影响台湾年轻人都市生活文化的“旧情绵绵咖啡馆”与“现代启示录啤酒馆”,1988年自我放逐流浪欧美一年,想要好好看看世界,却从世界看到迷失的自己,决定减少工作,寻找自己。1990年开始台北工作上海隐居的两岸往来十年,并在报章杂志撰写都市人文文化艺术专栏与散文,并集结出书《流浪的眼睛》、《台北心上海情》 。1998年正式定居上海,成立上海环境设计工作室。
台北来的建筑师登琨艳先生的工作室租用了苏州河边解放前原来上海大亨杜月笙的粮仓,二楼及三楼两层,面积两千多平方米。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惊人的工作室,才创造了两个老朋友见面的机会。登琨艳与阿城认识好多年了,他们在洛杉矶、纽约、台北都同时间住过。阿城也去过登琨艳在台北的工作室,但他没来过这个上海的工作室,在这样一个地方谈论我们杂志要求的建筑与人文的话题,真是非常的契合。也因办这个工作室,位于苏州河边的黄金位置,在上海目前飞速发展的城市拆建中,可能不会有让登琨艳先生长久住下去的希望。是耶非耶,一时难以说清。(当然,本篇发表后,一切都改观了。本篇发表于2000年1月。)
登:我选择上海作我的设计事业的新起点,是因为个人喜欢这城市的活力与机会。我所谓的机会,不仅仅是说我要去发展的机会,而是包括城市本身的机会与潜力。这城市到底会变成什么样?还很难说。这城市斗志昂扬地想要成为国际都市,但国际都市不是你盖出许多新的高层建筑来就是了。仅就建筑来说,最近七八年来,上海是全世界发展史上同时间进行的最庞大的工地。但很遗憾的是还没有盖出一栋可以拿到国际上去说是代表上海这个时代的建筑。这么多的机会,只要抓住一个就可以把她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就好像西班牙的毕尔巴鄂(BILBAO),一个很小的城市,从来名不见经传,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得到,可是因为新盖了一个美国古根汉姆美术馆的分馆,一夜之间,毕尔巴鄂闻名全球。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盖出这么多的文教公共建筑,更不要说民间建筑了。我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城市,在国外像日本盖一个东京新市政厅花了二十几年。
阿:体制不一样。议会体制下,怎么花纳税人的钱,要讨论来讨论去。我们这里是权力集中,结果是可遇不可求。
登:什么东西好不好看,不能仅仅看眼前的,拿现在与20世纪90年代前对比,就会觉得城市漂亮了。我们要走出去,要去见识世界。在社会主义权力财力集中使用的优越性条件下,这个城市太有机会可以做出国际性的东西,是可以在国际领先的,绝对不是国外什么样子我们就跟着学做什么样子。拿金茂大厦来说,它跟纽约的高层建筑长得实在没有什么差别,几乎是纽约的翻版;大剧院,风格也跟法国的很像。
阿:土和洋,已经是种意识形态了。说起来,什么是土?土就是惟恐别人认为自己不洋。北京、上海,几乎全国都有这种恐惧症,不过上海是掩饰得好的,但骨子里还是土。我有一次和朋友做一个试验,就是在淮海路上凑近看有女人大腿的广告,结果身后路过的上海人屡说“乡下人”,屡试不爽。
登:我拿苏州河边上海人不要的老仓库来改成工作室,这在国外一点都不稀奇,纽约的苏荷就是这样一个旧仓库区。原来是纽约人不要的区域,三十几年前贫穷的艺术家进驻,然后画廊、时髦商店进入,成为纽约甚至美国现代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它已经代表了纽约,代表了美国开放艺术的象征。在国外许多都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过这样将老旧区域建筑拆迁的过程。但很多先进国家绝大部分都还保留相当的区域,从纽约到伦敦,从阿姆斯特丹到西雅图、旧金山,都保存很多这样的仓库厂房。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了这些都市或国家创新文化的领袖区域。可是这样的区域,上海比别的地方还要多,范围还要广,因为它过去有太多的工商产业。不止是苏州河沿岸,杨浦区还有更多更庞大的工厂区域。我在那里看到一座仓库,里头一座电梯大到可以把一辆大卡车开进去,那是一座一百多年历史的老电梯,每个细部都漂亮得像艺术品,现在还能用,如果把它搬到美术馆、博物馆去都可以吓人的。听说德国公司愿意拿一百万元买回去,再帮忙装一部新的给他们。可是这些地方现在正在快速地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全新使用功能,来保留这些旧的产业建筑,让它变成一种机会。可是如果你认为它是落后的,它占着这河边最好的位置,上海地图上最好的中心位置,要盖高级饭店、高级住宅,你就会把它拆掉,如果换一种想法呢,你也许可以创造一个上海的苏荷。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这些产业建筑的命运决定苏州河的命运。
就看主事者的文化良知良解了,一念之间而已。
建筑可以荣耀一个城市。也可以变成一个城市的耻辱。一个城市的建筑的决策者也很需要相当程度的美学素养,这样他就会想到未来,不敢乱做决定。譬如这条苏州河,你可以让它变成上海未来前卫文化的发源地,像纽约的苏荷一样,艺术家在这里给老建筑注入全新的生命,让老旧文化建筑开出新的花朵。上海是有很多这种机会的,只可惜愈来愈少了,台北犯的错,上海能不能少犯一些?
文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是不是都经历这样的过程:拆毁、建设、再发现?
阿:日本没有这个过程。英国没有,意大利也没有。上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一个砸烂旧世界的革命,它影响了本世纪的两个国家的大革命,一个俄国,一个中国。我不喜欢巴黎,巴黎是一个水泥公寓的世界,我怀疑发明水泥的原因就是为了资产阶级造公寓。巴黎的公寓特有一种伪古典的样式,很像北京扩建的平安大道,沿街排满了伪古典的水泥店铺。在巴黎转不了多久,你就能同情当年老巴尔扎克为什么总是在挖苦暴发户,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品位。巴黎的文明和文化是资产阶级的,埃菲尔铁塔到蓬皮杜中心,再到凡尔赛宫前的透明金字塔,一脉相承。特吕弗的《四百下》,影片开始是一个长尺度的活街移动空镜头,从不断闪过的公寓楼顶上,始终是那个埃菲尔铁塔。我看了也很感动,这是一种很标准的工业乡愁。巴黎的迷人不在建筑,而在艺术家。我曾经住过一个公寓,楼上就是玛格里特·杜拉。我躺在床上,看满是裂纹的天花板,想老太太真是精力旺盛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曾经请法国建筑师去改造一下佛罗伦萨,料不到法国就是一个拆,拆到佛罗伦萨人惊心动魄,赶快将法国人请走。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意大利人说起来是痛心疾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罗伦萨,只有市中心是原来的,其他的都被当年请来的法国人认为是封建旧世界而拆掉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潮流,如果没有很强的人文素质,很难抵挡。
意大利人还上过英国人一个当。诗人拜伦在罗马大道上咏叹过一堵残破的墙,大致相当于我们“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意思,于是意大利人就将一路上的道边建筑做了旧,人工致残。我也是看时有疑惑,才问出了这个掌故。
登:大部分工业革命前如果已经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它们的城市大部分不会因为这种现代化的过程而被拆毁。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要新的东西,不断拆毁老城区,老的建筑。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了发展,不经太多考虑,就把一堆老区域糊里糊涂给拆掉,然后盖了一堆很难看的新建筑。我这栋房子后面这个区域的人,也许会在一个月内就被动迁,整个搬到南汇野生动物园旁边,这种变化,是整个居民生态的变化,一夜之间,每天下棋的老朋友你就看不到了。我是很喜欢到后面的那片老房子逛的,胡乱逛,看看老先生们围着藏青色围裙,在屋外弄堂里坐在太阳下看报纸,我说,人生能这样子多幸福,一个大男人,穿着一个大围裙,洗洗刷刷做家事。在我们台湾哪有男人穿围裙,根本不可能,那是个大男人主义的地方。可是从另外的角度看,我觉得他们是生活得多么地自在,房子那么小,所有的社文活动就只好搬到弄堂里头。大男人大庭广众下挑菜洗菜,没有几个国家的男人尤其是老男人是自在的。在台北住了三十几年,可是我的父母亲就是不肯搬来跟我一起住,他们宁可住在高雄的老家里,搬来台北和我一起住,他们会失去朋友,年纪大了,很难再交新朋友的。所以里弄的朋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大夏天光着膀子乘凉,下下棋,多自在。住进新房子,会让你很愉快,可是当你搬进去不要太久,很快就会让你觉得无趣,想逃的。
阿:很多上海人对美国的概念就是纽约。
旧上海的确有很多地方与纽约相似,例如高楼、厂房、仓库、港口,所以上海人到纽约,会比较适应。我是死不改悔的平房派,所以在洛杉矶苟且着。我不喜欢纽约的另外原因是它太落后了。它发展满了,工业时代时发展得太迅速了,如果要建一个新的建筑,一定要炸掉一个旧的。前些年纽约要换掉石棉防火夹层,因为发现石棉纤维致癌,施工非常困难。凡是检修、增进新管线,只能将马路挖开,这种影响市民生活的不断施工,几乎使一任市长辞职。计算机网络时代来临,光缆的铺设在旧楼里简直是灾难,眼看着纽约在21世纪陷入困境,市政府很头痛。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追求文明的进步,结果很可能不久就是落后的。许多的新电视塔,明摆着就要没用了,因为卫星传送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们怎么避免这些判断错误,而在城市结构中预留空间?这时恰恰是人文的知识、经验能使我们眼界开阔,对技术的发展有一个批判。
登:最近台湾有人找我做设计,他迷恋台湾老的传统三合院,想在城里建一个理想的三合院,都市里那么小的土地怎么做老的三合院?所以我就把上海的“石库门”往台湾搬。上海的“石库门”就是七八十年前老式三合院的现代版,占地很小,二层楼叠起来,那个空间很有趣。这样的房子如果是一家人住,那一定是很舒适风雅的,那里头秘密空间做得实在太好,绕来绕去,在屋里院子里随便穿着怎样干什么都不会有人看见。这是七八十年前很好的都市住宅设计,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居住。
上海市政府如果做得到,应该把这些“石库门”房子尽可能保留下来。一个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建那么多的高楼,高架路,只会涌来更多的人、更多的车子,进来更多的商业的,很麻烦的。台湾如此,东京如此,汉城、曼谷也是如此,不会因为道路变宽,房子盖高,交通人流变好的,没有例外的例子。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很难解决的。
阿:最后只好放弃中心。例如纽约一样,很多人住到新泽西去,到纽约上班。每天跨州到纽约上班。
登: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巴黎,他们政府只允许在老的城区外面发展,规划出十几个新的城区。在巴黎你可以看到过去的老建筑,也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新的前卫建筑,如果上海有关部门能注意到这样的问题,那些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面貌是绝对可以保存得很好。
阿: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他们做过一个南京和北京的规划,就是将行政部门移出老城,建立新城,也就保留了老城。日本京都就是因为梁思成的意见,美军不轰炸而保留下来。我小时候的幼儿园,就在傅作义时期的“新北京”,城墙以西到西山一带,真的是新的,就是王朔写的《看上去很美》的那个地区,我们可以看出他写的那个幼儿园很大,也很新。
我在的那个幼儿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储物柜,细条木板地,操场有两个足球场大,欧美式的,与梁思成他们的留学区域有关。当年北京、南京的规划图,据说还在,倒不妨印出来供市政参考。如果按这条路子走下来,50年来我们可以不动老城。我们这些年拆的,在日本叫“文化财富”。为什么要拆?就是没有新眼光。
登:建筑是很可怕的,它绝对反映社会时代政治人文与主事者的决策能力和良知,也许今天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过了十年八年你就知道,这个是蒋介石主事时候盖的,这是毛泽东时代盖的。一点也变不了样,绝对反映出主事者的态度。建筑就可怕在这里,可是当事人在做决策的当时似乎都不觉得的。
阿:罗马、米兰有大量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时期的建筑,墨索里尼搞的是新古典主义,做的建筑又非常之大。例如米兰火车站,提着行李到月台,要走很长的一段台阶,我这么好的体力都差点累死。罗马的议会大厦,罗马人戏称为“打字机”,外观确实像老式打字机,巨大无比。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说法西斯的建筑应该拆掉,这几年大家想通了,不要拆掉,历史上有过一次法西斯,保留这些建筑就是保留经历过的状态。
登:今天我一个台湾来的人跑到上海来租用杜月笙留下的粮仓,就有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将来万一我有什么成就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诗经》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国,住在开发得很好的农牧区,在它们旁边有一个以打猎为主的国家,要侵犯它,他们打不过,就跑,另外选一个地方叫周原,重新开发,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一段,很像我今天当下的心情。
(摘自《文化不会老:名家对谈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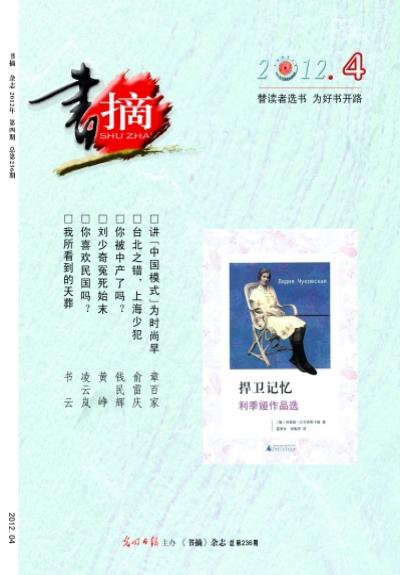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