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他们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群。
目前,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差不多有1亿。保守估计,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之间,这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面对着繁华的城市,他们只能在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不能在城市考学,没有足够的零用钱……迄今为止,人们很难把这些孩子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字联系起来。
4年前,北京社科院学者韩嘉玲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韩嘉玲说:“我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个选择,即:不知道。”但收上来的问卷中,有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韩嘉玲心酸。“他们从小在城市生活读书,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是制度把他们排挤到城市的边缘。确切地说应该称呼他们为‘城市新市民’。”
20岁的万龙:现在的日子令他不满,未来的日子他很茫然
万龙以卖鱼送货为生。和鱼腥味一起飘来的,是他压抑不住的烦躁。他每天6点30分起床,骑车进货。中午1个小时,骑车给餐厅送鱼。下午4点半到7点,继续骑车给餐厅送货。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我的生活除了市场就是马路,再有是饭店,没有别的了。”
10年前,万龙的父母瞅着家里的3亩田地年收入还不足1000元,便两手空空地从安徽无为县来北京打拼。开始时卖菜,后来扫大街,有了鱼摊才逐步稳定下来。4年前,万龙没有考上县城高中,便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起初,他特别兴奋。“每天6点钟就起床。总是第一个来到市场,中午也不休息,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后来,他就懒了下来,心也随之烦躁不安。没事的时候,别说在鱼摊坐3个小时,1个小时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什么人都没有,就你拿把椅子坐着,受得了吗?我最长只能坐1个小时,超过就心烦。”
万龙转过的地方很少。“北京那些好玩的地方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我倒更愿意和朋友在一起。”其实万龙没什么朋友,他交往的人不外乎和鱼摊有关,还有网友。他每次上网都要事先跟对方声明:“我是外地人,你愿意跟我聊吗?”记者与他初次见面后,手机上便出现了“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的短信。以至后面几次交谈中,这句话都像誓言一般,被拿出来问,万龙要得到肯定的答案。
说起北京人,万龙心情复杂。11岁放暑假那年,万龙第一次来北京。谈及对北京的最初印象,他脱口而出:“北京人太霸道,看不起外地人。”这样的印象,以后不断得到印证:“坐公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事儿,要是碰到北京人就没那么简单了。上次我不留神踩了北京人一脚,老说对不起,还是不行。”
3个星期前,父母帮他开创事业,给他新租了一个小鱼摊。但万龙已经开始厌倦卖鱼了。可他还能做什么?到北京的第三年,经朋友介绍,他站在大街上发送电脑学习班的广告,结果只做了3天就拂袖而去。“那太没有意思了,简直是浪费时间。”今年年初,他又学了点电脑维修组装的基本常识,却从来没修过电脑。
现在万龙希望自己这个小鱼摊能挣点钱,这样年底他就买一台组装的电脑。“如果这鱼摊挣不到钱,明年我就出去打工,打天下。”究竟何为“天下”,他却“说不清楚”。万龙又说他想换个城市,“这个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连鱼摊都是父母的。在北京我就像一个捡破烂的。”现在鱼摊每个月净赚两千多元。父母没有过高期望,只希望他能留在身边踏实地卖鱼,赚钱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小两口再出来打工。然而,他对未来是茫然的。
万龙对爷爷奶奶有着深厚的感情,偶尔打个电话问问身体情况,但很少会想到家乡,除非心烦的时候,他脑海里才会掠过曾经和小伙伴一起烤白薯,抓野兔子,到河沟里游泳的快乐时光。“我肯定不会回去,有能力就在好的地方生活,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儿,他说。
8岁的曼曼:太多的艰辛,会在她心上留下些什么呢
曼曼的家住在距南京市区15公里的燕子矶笆斗山,离长江几十米远。她的父亲来南京打工20年了,以在长江边上挖野菜卖为生,一天挣十几元钱。
曼曼曾有一个4岁的弟弟猫猫和一个6岁的妹妹燕燕。
2004年3月的一天,燕燕死于上吊自杀。她当时站在院子里的洗衣机上,拿起一块大的湿毛巾,挂在洗衣机上方的铁丝网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把头伸了进去。那个中午,父母不在家,3个孩子躲在家里玩。“爸爸走的时候交代我,一定要看好弟弟妹妹。”曼曼说。曼曼和弟妹们几乎没有去邻居家玩过。“妈妈说,他们会嫌我们脏的。”曼曼眨着大眼睛,“爸爸说不要让弟弟出去,因为他出去看到别人的小孩的玩具会抢过来玩。”
干完活后曼曼练习写字,燕燕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她爬上洗衣机,眺望对面的幼儿园。燕燕喜欢上学,几天前,燕燕就和父母闹着要上幼儿园。母亲说:“我们家穷,上不起幼儿园。”
“她突然叫了我一声,‘姐,王林也在幼儿园里面呢,他在做游戏’。王林是和爸爸一起来南京打工的老乡的儿子。”曼曼回忆,燕燕好像使劲地对着幼儿园的窗户叫了几声,但是对面的窗户是紧闭着的,他听不见。“后来她走过来对我说她不想活了,她想死。我没在意。”曼曼说。
一会儿,弟弟在院子里看见燕燕站在院子里的洗衣机上,湿毛巾打了个结挂在洗衣机上方的铁丝网上,脖子缠在里面,鼻子流血了,舌头也伸了出来。他连忙把燕燕的脚朝洗衣机上搬,并哭着喊大姐出来。曼曼从屋子里跑出来,“我想去解开湿毛巾,可怎么也解不开。”两个孩子折腾了一会儿,越来越害怕,就跑出去找邻居帮忙。邻居们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8岁的曼曼把手放在妹妹的鼻孔下,感觉没气了,吓得跪下拼命磕头:“快救救妹妹啊!”
出事后曼曼变了,妈妈说她老是一声不吭地瞪着眼睛看人。半年多过去了,父母几乎没怎么见她笑,她的脸上有了和大人一样的表情。猫猫也变了,变成了一个狂野的孩子,一刻都不想呆在屋子里,就想在房屋外面飞跑,拿着个棍子上窜下跳。猫猫老是跑去弄坏别人家种的东西,邻居就有闲话了,说他是个坏孩子。曼曼听到了,抓住弟弟就打,毫不留情。以前弟弟出去了,她去哄回来,现在拖住就打,那打的架势让母亲也呆住了。“我真害怕弟弟再出什么事。弟弟不乖,我就打,打了就不会出事了!”曼曼说。
9月底的一天,在离家附近的十字路口,母亲推着一辆大自行车,猫猫就在车前站着。一辆1.5吨重的小油罐车从他们身边转弯,大车子上的铁架子刮到了自行车,母亲想把孩子护住,自己跌倒了,自行车倒在她的背上,油罐车的车轮子从自行车身上碾过。随后赶来的曼曼吓坏了,对着路人就跪,大声喊:“救救我妈!”
父亲去交警大队和司机协商处理赔偿事宜。除了两万多元住院费,生活残疾补助费、误工费等一共协商赔了两万多块钱。谈到生活残疾补助费,交警问他:“你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父亲回答:“农村户口。”交警说:“那按照生活残疾补助规定,农村和城里消费水平不一样,农村的要少几乎一半。”父亲说:“可是我们住在城里啊,消费水平是一样的啊。”
父亲咨询过律师如果打官司可以赔更多的钱,可他花不起打官司的钱,也不一定打官司就真的能多多少钱,“人家是城里人,路子多啊。你看,医院开的证明说是断了两根骨头,法医残疾鉴定的时候说,片子上明明是4根骨头断了啊。”
8岁的曼曼现在在附近的公立燕子矶小学上学,学校给免了1000元赞助费,曼曼的两个眼圈总是黑黑的。她每天晚上做作业最早要做到9点钟,最晚要熬到12点。因为父母都只读过一年级,基本不怎么认字。没人教她,她一个人蹲在那儿琢磨半天。“作业做不完,老师要凶的。”有两回,曼曼都是湿着裤子回家,“作业做不出紧张得尿身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班上最笨的孩子。第一次考试只考了4分。”曼曼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父母教呢?”
12岁的娇娇:在城市的中心向往城市
娇娇出生第二年就跟随打工的父母进入北京,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离开家乡10年,娇娇总共才回去过3次。她不愿意回老家。“我,算城市人吧。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了。回老家,人家都说,从北京回来的。”娇娇不无骄傲地说。
娇娇现在的家在北京西城区甘家口,是城里高楼间的“盆地”——类似城乡接合部那种大片逼仄的平房里。她的父母在菜市场卖鱼。娇娇是在菜市场玩大的。娇娇原来在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丰台区总校,今年9月1日学校被勒令拆掉了。由此,她进了离家比较近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
菜市场对面就有一所小学,几年前,爸爸有意让她转到这里。行知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还要穿越铁路。两年前北京公办学校取消赞助费的时候,爸爸曾带她去那小学咨询。校长先问娇娇:你爸爸做什么的?回答:卖鱼。然后校长告诉旁边的爸爸:“明天就带孩子来报名吧。顺便带上40条草鱼,40只胖头鱼,都要两三斤重的那种。”娇娇的爸爸粗算了这些鱼差不多有一千多元,“怎么比赞助费还多。”他当场和校长大吵了一架,转学之事告吹。娇娇只好进入现在的学校,这学校只要入学考试成绩合格就录取。
一个星期前,娇娇在新学校参加了首次期中考试。数学97分,位列第一。她挺开心,觉得这样同学们就不会小看她了。
娇娇不仅要适应新的环境,还要平复不时冒出来的“对立”。以前在打工子弟学校,一到下课时间,娇娇就和一帮同学疯打疯闹。这边,下课后几个女生跳皮筋,从不让娇娇参加,娇娇要么识趣地留在教室里写作业,要么一个人去玩体育器材。
在班上,对于父母的职业,娇娇一直小心地掩盖着,但同学们还是知道了。有一天,轮到她做值日。一个女生被老师留下来改错。娇娇打扫到她脚下,让她挪开地方。女生反骂道:“你家是臭卖鱼的,管得着我吗?我爸是总经理!”“臭卖鱼的怎么啦?”自尊的娇娇一脚踢到对方桌角。对方也毫不示弱,两个女孩扭打起来。平时有心事,娇娇都装在肚子里不跟父母提,那天回家却忍不住哭了。父亲气愤地劝说着女儿:“没有我们卖鱼,北京人吃得上吗?”娇娇有时脱口而出的话显得宿命而成熟,比如,“我和班上的同学不一样。因为我们身份不一样。他们是北京人,我是外地人。”尽管新学校教学条件比原先好得多,娇娇还是很想念行知学校。“那边老师像我妈似的,下雨天会把自己的伞借给我。”
娇娇对记者说出了这样的理想:“爸爸妈妈很辛苦,每天三四点就起床。妈妈卖鱼,一到夏天手就烂。我希望他们也能有一份在单位的那种工作。”“希望将来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在有办公室的地方上班,受人爱戴。反正就是和其他北京人过着一样的生活。”
农民孩子的矛盾
王春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用另一个阳光的词语来指代这群孩子:“城市新生代”。他强调,新生代的孩子依然在延续父辈的孤岛化生活。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家乡。“要知道,这个人群肯定不走了,回不去了。可又不像城市人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们不知道明天,无法、也不敢规划未来。”《新京报》的一份调查反映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77.5%表示想留在北京。他们普遍对农业、父母这代人持否定的看法。他们在农村的社会交往圈变得越来越小,对农业活动缺乏感情和兴趣,甚至会批评农村人“太土,不卫生”。
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平台。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向上提升自己将越来越难。他们或许只能在彷徨中生活。
这些孩子,一方面庆幸自己来到北京读书,使得比家乡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的见识和生活经历,另一方面,他们对城市又敌视而隔膜。他们不愿意重复父母的生活,也不认可周围城市人的状态,羡慕崇拜城市人,又觉得那些都不属于自己。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王春光曾在深圳采访过几个农村孩子,对方明确表示:干不好就去抢。
“学校是最自然的融入过程。虽然这些孩子在公办学校有诸多不适应,但是让他们越早进入公办学校越好,这样他们更容易进入城市主流生活,在城市拥有更多的朋友。”韩嘉玲强调。
但是,某些已经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一个女孩8岁时离开公立学校的情形:“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来了。”
两个月前,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开展了一次活动,通过报纸征集,让10个农民工的孩子与10个北京孩子“同在北京手拉手”,报纸上事先登出了参加活动的农民工孩子的愿望。
侯丹丽 看看故宫
侯战强 能去课本上写的景山看看
闫磊磊 想有属于自己的《奥特曼》故事书
丁亚文 吃一次生日蛋糕
陶 帅 住一次楼房
孙赢赢 去动物园看老虎
陈 欣 想要一个新书包
李贝贝 得到一本英汉词典
李蓉蓉 去一次动物园
张 军 希望能去香山爬山
而他们想教给城里小孩的是:
劈柴、叠炕(叠被子)、拖地
做清炒土豆丝,特别好吃
炸油饼油条、包包子
炒饼丝、擦盘子、倒立……
10个北京家庭满足了10个农民工孩子一天的心愿。这些孩子的心愿竟是如此朴素简单。
(摘自《中国草根原生态》,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35.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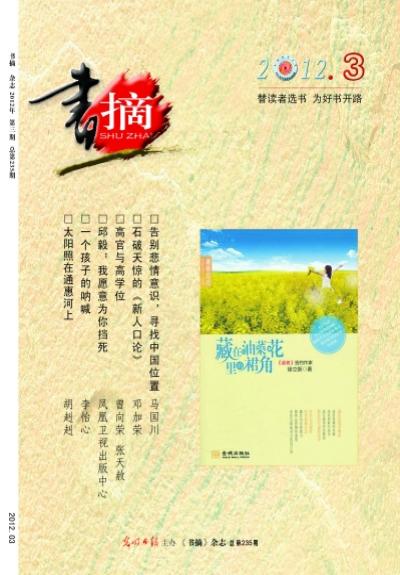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