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饭店隔街相望的“长安俱乐部”受到建筑师和作家同声的批评,建筑师用语更加尖刻:“在这样的城市中,在这个文明古都,这样重要的地段,又有资金保证,却诞生这么个玩意儿,就不由人不佩服拍板者的勇气和教养。”城市比此更让人难受的建筑多的是,建筑与业主,谁该受到更多的批评?
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功德圆满。我在电视上看到本届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吴良镛先生接受记者采访,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建筑师实际上有三个业主,一个是有地皮使用权和出钱的业主,一个是规划部门,一个则是广大的民众。因为他是临场口头表达,我是作为电视观众临时遭逢这一表述,不及录像,所以上面关于他观点的转述只是一个大概,恐怕未必准确。但建筑师与业主的关系,早在我琢磨之中,吴先生的电视亮相,促使我进一步梳理思绪,来写这篇文章。
我很荣幸,能以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机构,在1998年出版了我的一本建筑评论和随笔集《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并能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开会前第二次印刷;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在1999年第二期《建筑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卢桦先生的批评文章,他对拙著中的外行话直率地予以指正。如我说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外表保持水泥原色”,他指出“外墙材料是石材,不是水泥。真用水泥建造,难度会更高,作为金融机构不可能有那样的勇气,会嫌寒碜。尽管事实全看如何设计。大概没解决好石材是湿铺还是干挂的问题,致使水迹斑斑老在返潮,仿佛外墙都是水房和厕所,而不是办公室”。他对我的《通读长安街》基本上是逐条进行“反弹”,行文颇俏,举一反三,实在是我抛出的砖头所殷殷期待的一块美玉。他也偶有与我所见略同时,如对与北京饭店隔街相望的所谓“长安俱乐部”的批评,不过他用语更加尖刻:“天下比这更让人难受的房子多得是。不过,在这样的城市中,在这个文明古都,这样重要的地段,又有资金保证,却诞生这么个玩意儿,就不由人不佩服拍板者的勇气和教养。”
卢桦先生是建筑师。他在批评我的建筑评论时,有时批评到同行,有时批评到业主。上面所举两例,都涉及到对业主的批评。“作为金融机构不可能有那样的勇气,会嫌(直接使用水泥处理外墙)寒碜”,是比较温和的批评。我是建筑业的外行,更不知世界上是否有勇于用水泥外墙的金融机构,但我在美国参观过位于科罗拉多山麓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那一组由贝聿铭设计的建筑就用了水泥墙面(其中掺入了就地取材的山石粉碎成的“石米”),立面效果与周遭的山野十分和谐。恐怕有勇气容纳建筑师这种粗犷风格的科研机构也不会多。卢桦先生对“长安俱乐部”业主的批评则非常严厉,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两个业主:一个是具体占有地皮使用权的出钱的业主,一个则是对北京城市整体风貌负有重责的规划部门,即第二业主。在我们当前的局面下,第二业主的拍板权是大于高于第一业主的,“不由人不佩服拍板者的勇气和教养”,这讽刺性的批评太刺耳了么?但卢桦先生此时是在以一个普通的市民身份说话,正如吴良镛先生所指出的,广大的市民对那些与他们日常视野息息相关的,想躲开不看,“眼不见为净”,却又无法逭逃,只好被动地,“不看也得看”的大房子,如长安街上的这栋“长安俱乐部”,作出反应,表示反感,乃至问一声“谁让盖的”,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应予法律保护——这是第三业主的声音。因为城市是属于全体市民的,只要其形体包括轮廓线为市民所共享,哪怕其内部并不为一般人开放,作为一个市民便拥有发言权,也不仅是评论,必要时,还可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比如,我们报上也登过,国外曾有市民控告某些建筑物的业主,指控他们所盖出的建筑形成了非正常的气流,因而导致了自己身体受损,要求赔偿。这样的事件,如果在我们这里也发生,应该说是一种进步,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崇洋媚外一类的问题。“三个业主论”,应划入人类共享文明的范畴。
不过,话说回来,第一业主,也就是提供资金的主儿,毕竟是最重要的业主。没有这样的业主接纳,任何建筑师都不可能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筑师当然也可以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业主和建筑师的身份合而为一,不过,那充其量也就是为自己设计个私宅罢了,哪个建筑师甘愿只是小打小闹设计点小房子小院子呢?但大的项目,就得有财大气粗的业主来投资,人家既然是出钱的,当然就要对建筑师提出要求,并拥有最后的拍板权。于是,作为建筑师,就有个维系跟业主关系的问题,有个把自己的美学追求,与业主的功能性要求和审美趣味磨合的问题。现在许多大型的城市建筑项目,业主对设计都是采取招标的办法,你过分挑剔业主的“勇气和教养”,也许那业主的“勇气和教养”确实不敢恭维,但业主完全可以率先将你的设计方案淘汰出局,你的方案不管如何高妙,盖不成实体,总不能算数。我认识一位青年建筑师,他有许多令我看来耳目一新的创意图,也曾参与过几次不算太小的项目的招标活动,绘制出很具个性的效果图,甚至有两回还出了沙盘模型,但终于还是都被淘汰,或者说被埋没。这就比弄文学的狼狈,比如现在想公开发表小说,当然也需要与出版机构,与“一渠道”或“二渠道”的发行网磨合(最好“一二兼容”),但即使暂时不能出版,小说总还是小说,况且“东方不亮西方亮”,换几个地方试试,总不难找到出路,就是放一放,过些年再面世,也往往仍不失为一部佳作。搞建筑设计,你最后变不成实物,那就很难说是有了作品,也很难把为这个业主淘汰的设计,原样拿给别的业主去使用,而搁置多年的设计是否还会在以后“枯木逢春”呢?即使举出几个那样的例子,能以彼为激励吗?
于是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优秀的建筑师,其素质之一,就是能对付最刁钻的业主,在业主所设定的框架里,使自己的审美追求和技术才能得到最大发挥,使自己的设计终于化为大地上具体的景观;最后业主很可能被历史的尘埃淹没,被后人遗忘,而建筑师所设计的佳构,成为一方名胜古迹,令一代又一代的地球生命所欣赏,所赞叹,建筑师也就因而百世流芳。中国过去比较轻视建筑师,许多非常优秀的古代建筑,都没能留下具体的建筑师的名字,但普通老百姓给这些优秀建筑师,赋予了一个“共名”——鲁班。有关鲁班的传说故事,往往采取了这样的结构方式:业主对建筑项目提出了哑谜般的奇诡要求,如在指定时限内满足不了那要求,则或是鲁班本人,或是求救于鲁班的匠人(设计者),便会遭受重罚乃至有性命之虞,但每次鲁班总是以超常的想象力与巧妙的技术处理,不仅达到了业主的要求,还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器物或建筑物。鲁班的故事里所贯穿的征服业主的勇气,与在忍耐中孕育出巧思奇技的教养。是不是完全过时了呢?
历史上有许多糟糕的、恶劣的业主:暴戾的皇帝,颟顸的贵族,大小军阀,恶霸乡绅,市井流氓,暴发户,黑社会老大,贪婪的资本家,伪善的传道者等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业主,利用他们的权利和金钱,雇佣设计者、营造者所建成的宫室殿堂、宅院园林,留存到今天的,我们多半还是认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或文物价值,可见即使在这样一些业主的雇佣下,建筑师仍有可能创造出璀璨的作品。中外古今,例子太多。大的古的如埃及金字塔,小的近的如中国山西的乔家大院。这一事实是令人深思的。或许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束缚下的建筑设计,是不可能焕发出充沛的想象力,构建出具有永久性审美魅力的建筑的。这种见解经不起推敲。现在我们所一致赞叹与竭力保护的,明成祖所建成,在清代基本上没有大动的北京城“古都风貌”,无论是整个内外城的规模形状,中轴线的处理,紫禁城的布局,以及天、地、日、月等神坛的设计,完全是在“天人合一”、“皇权天授”等意识形态理念束缚下完成的,面对这些大体仍活现于我们面前的建筑物及其园林、环境配置,我们不能不佩服当年那些设计者在限定的框架里发挥其创造力的睿智与机敏。
我在《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里,还没有表述过这样的思绪。把这样的思绪讲出来是否会令现在的中国建筑师们不快?我在书里也抨击过“长官意志”,“长官意志”在我们的第一业主和第二业主身上都存在,比如把“中国民族形式”简单地理解为“亭子顶”,把“现代化”或“国际气派”简单地理解为“玻璃幕墙”与“摩天式”,尤其令建筑师们不知所措的是,要问建筑设计是姓“社”还是姓“资”。这样的框架实在应该打破,为建筑师们解除掉这些束缚,也是第三业主——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明成祖时建成的北京城固然是个杰出的艺术品,却不可能在设计、建造时听取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如我置身其中的当代市民群体,应该站出来为建筑师们请命的。但我还是要继续表达我的困惑:为什么北京城近二十年来令人气闷的大体量建筑是那么多,而令人欣喜的地标性建筑是那么少?难道问题都出在业主一方吗?
在卢桦先生批评我的《通读长安街》的文章中,他击中了我的要害,就是未能把整个长安街当作一个整体背景来思考。在他的文字里,他对第二业主——城市规划部门,以及位置还在规划部门之上的机构和官员,其实不仅是并不排斥他们的干预,还往往责怪他们在城市整体面貌的把握上,缺乏良性的干预,只满足于在几个环路内外以不同的尺度限高,或要求新建筑预让出今后必将拓宽的街面、人行道,以为那就是尽职,结果是听任“城市淹没在自我为中心的单体建筑的浮躁喧哗之中,破坏了城市空间的连续和完整”。比如建国门内大街很短的一段马路两厢,便呈现出粗壮厚重的建筑与纤巧柔靡的建筑紧相连属,令人见之扼腕,却又起码几十年里难以修改的怪相。
该干预的没能起到良性干预的作用,不该干预的却又去恶性干预,这是我们现在一些业主的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毛病确实需要治一治。现在我们都为北京有颐和园而自豪,它确实是一座世界罕见的夏宫。但它的业主是很恶劣的——慈禧太后为了一己的享乐,竟然挪用海军军费来修造这座园林。不知还能不能找到有关修造颐和园的档案,作为业主的慈禧本人有什么懿旨,作为业主代理人的官员又对设计者有什么具体指示,具体的设计方案,“烫样”,是怎么拍板的?慈禧究竟过问到什么程度?对设计者的构思、图样、审美追求干预到什么深度?……似乎是,不仅她并未很深入地介入具体的设计过程,就是业主代理人,也未必在功能性和总体美学要求之外,去对设计者的设计进行繁琐的“论证”。当然,倘若建成后慈禧太后不满意,她可以杀设计者的头,但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没能找到有关设计修造颐和园的资料,但偶翻清末民初何刚德所撰的《春明梦录》,此人在光绪年间曾奉命主持天坛祈年殿的重建,他记载此事说:“余所办工程,以祈年殿为最钜,工费将及百万。祈年殿者,即上幸祈毂坛也。坛为雷火所击,全体毁焉……殿柱本用楠木,近时无此材料,以洋楠木代之。横卧于地,对面不能见人,其圆径之钜可想而知。殿顶以金镀之,在库领金六百两。中可容数十人,甚矣规模之宏壮也。”他作为业主代理人似乎只是把握资金、建材、规模、总体效果而已。这次重建在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他对这座殿堂原是上圆下方,后来改为三层圆檐各为蓝、黄、绿色的攒尖顶,以及乾隆时改设计为三层檐全为蓝色等设计师美学上的推敲了无记载。可见那时候业主在政治上可能很没落腐朽,但在与建筑师的关系上,倒还给予了建筑师相当大的艺术想象与创新出奇的施展空间。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在内忧外患那么深重的情况下,作为京剧这一艺术品种的最大享用者(也可以说是业主)的慈禧,能让京剧这朵艺术奇葩灿烂开放,以至给我们后人(也可以说为全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根由吧。我当然不是要为慈禧太后评功摆好,不过,她的对建筑师、艺术家不作过多的专业性干预,甚至往往并不去进入其专业性的操作,只是“坐享其成”,这一点,恐怕还是值得我们多少想一想的吧。
第二十届国际建筑师大会,通过了吴良镛先生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文件,提出了在21世纪,要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强调综合的广义的建筑学,其原则包括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的融合;建立人居环境循环体系;面向全社会;重温建筑的综合性;创造和而不同的建筑文化等等。但站得再高,看得再远,建筑师和业主的关系,仍是关键性的一环。这一环磨合不好,所有的美好向往都可能泡汤。勇气和教养,对现代建筑师和第一、第二、第三业主来说,都是重要的;或许应该各有侧重;各方该把勇气与教养侧重于哪些方面呢?自问自答,你问我答,都必要。
(摘自《听刘心武说房子的事儿》,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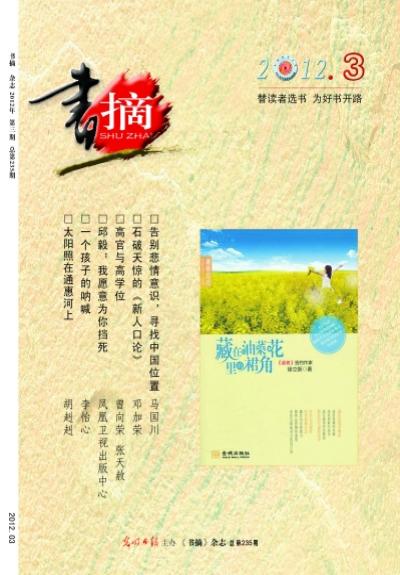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