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说:“妈妈就是政府!” 事后我想了很久,孩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家中根本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痕迹,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纪律严明的。
自从当上了教授,年资日益增长,连我自己也感到无端地受到分外的尊重。在学校里随便走到什么公共场合,都有学生,上过我的课的和没有上过课的,对我让路。到外面开会,常常有人把我从角落里拉到中座,像婚礼中的新郎一样安排在最醒目的地方。其实这几年,我和过去作为小字号的充当放大炮的角色的时候,水平没有多大变化。除了顶部头发越来越沙漠化,不得不调动四周的植被来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地方支持中央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提高。但是我仍然乐于享受着我们礼仪之邦特别丰厚的对于我的资格的尊重和微笑,还有对于我怪脾气的迁就。
但是一回到家里,事情就颠倒过来。
首先,对我不买账的就是我的女儿,在她面前,我几乎没有什么本钱可以骄傲的。身为文学教授把一辈子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文学,可是,从她小学高年级升到高中,我对她的语文考卷、练习不但不能辅导,而且不断造成误导,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不止一次的打击。说实在的,当前中学语文考题,主要的那些刁钻古怪的选择题放在我的面前,我是非常可怜的。我对于那些隐蔽着的陷阱的警惕性比她差远了。在几次失败以后,她对我由不相信发展到嗤之以鼻。我呢,除了暗暗诅咒那些出题的家伙阴险毒辣之外,别无他法。有时想到这些出题者之中,有一些就是我的学生,心中就未免恨恨不已,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在考试时刁难过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刁难报复我呢?
由这里开始,我在女儿面前,威信日益低落。在学校的权威感和在家庭里的自卑感形成对照。我的话,女儿越来越不当一回事。有时简直弄到叫她上东、她偏要上西,要打狗,她偏要骂鸡的程度。
我多少有点不甘心。有一天,我随便提起的样子,问她:你爸爸是不是很民主?她头也不抬地回答:凑合。我又问,民主是不是多了一点?她还是漫不经心地回答:凑合。我有点火了,说:我看我们家有一点无政府主义。
她十分惊讶地抬起头来说:“什么无政府!妈妈就是政府!”
我以为她是和我开玩笑,但是她却没有笑,表情是非常严肃的。
事后我想了很久,孩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家中根本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痕迹,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纪律严明的。
就说吃饭吧,孩子妈妈一回来,就展开了短促的突击战,紧张的削、切、剁、剥,如进军的小铜鼓,烹、炒、煮、炸,如凯旋的鞭炮。煤气在左,电炉在右,原料居先,佐料后续,穆桂英高坐中军之帐,学诸葛用兵布阵:东方属青,甲乙木之属,有葱、菜、芜青之色,西方属金,丙丁火之质,有酱醋蛋肉之香,调和鼎鼐之妙,在方寸之内,驱遣闽粤之味,全在顾盼之间。胸中自有百味翻新,手下不劳运筹帷幄。须臾之间,菜香满室,一声令下:开饭!此时,不管女儿之数学作业才做及半,本人为文之灵感隐隐若现,全都得在30秒之内就座,否则就有遭受埋怨,乃至声讨之虞。原因是拖拖拉拉,不利于饭后迅速彻底、全面地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一齐洗擦干净。
有时女儿恳求:题目正做及半,稍待即来。随遭严词拒绝。女儿提出承担饭后洗碗擦桌之任务,即被驳斥:此乃吾之权利,不得侵犯!然后是第二次警告:上桌!军令如山,岂容商品社会讨价还价之风污染!
我问女儿:此等政府有如军管会,是否过分,几近希特勒之独裁?女儿摇头曰:否!妈妈实行的是民主专制。以绝对公仆的姿态,执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而且非常注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头一天晚上反复调查研究:明天早上吃什么?
我想起来,这种民主最可怕。不但我的想象力不行,就是女儿也无法在到达市场之前,凭空想象出可供选择的菜谱。稀饭、馒头早说吃腻了,牛奶、面包更是吃怕了。好容易想象出煮麦片加光饼这样土洋结合的新花样,没想没有几天,一看到就没有胃口了。对于妈妈的问题,孩子的天才早已使用殆尽,每当她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把这样的歌德巴赫猜想推到我头上。但是在食谱方面,我的创造力,是绝对贫困的。
吃饭本来是为了自己,现在变成为了别人的一种牺牲,对于这样的爱的专制,女儿显然是比我有更加聪慧的理解力。但是有时也不免牢骚满腹,有一次,她感慨万分地对我说,她有一个理想。我问是什么样的理想,她说,什么时候能不为妈妈的情绪吃饭就好了。我说,这恐怕很难,人总是免不了要为别人活着的。女儿万分无奈长叹一声,我不胜同情地短叹一声。
没想到女儿理想的日子居然在没有几天以后,不期而至。孩子的妈妈去医院照料岳父大人去了,吃什么,完全由我们这两个向往自由的臣民自己决定,日子竟然长达一天。令人开怀的,绝对自由终于来到了。
女儿欢呼不已。
第二天一早,孩子提上买菜的篮子拉上我的手,直往市场奔。自由的风在我们两个人的耳边歌唱,终于可以不用动脑筋,不用挖空心思地去想什么劳什子的菜谱,碰到什么就买什么,两个人脚底生风、在市场转悠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好吃的早餐。好在市场上的水果很是新鲜,先是尝了尝芒果,接着又吃了一点荔枝,无花果、番石榴刚上市,端的是齿角留香。两个人尽情地在市场转了一圈又一圈,等到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菜篮子里除了水果以外不但什么菜也没有,而且连早餐的主食也忘记买了。于是,又重新奔回市场,可是除了光饼、麦片、面包、牛奶之外还有什么呢?只好随便买了一点东西胡乱吃了一通,孩子叹了一口气说:纯粹为了自己的自由的早餐比之不自由的为了他人吃的早餐要差多了,而且,中午那一顿还不知道怎么混呢!
原来绝对自由的味道竟是这样的!
专制政府才撤离几个小时,两个被统治的臣民已经在盼望着早日恢复它专制的统治了。
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念过左拉的一篇小说,叫做《猫》。写的是一只猫被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养着,吃的是牛奶、鱼类,睡的是鸭绒被,女主人关怀备至,稍有不适,便百般呵护。弄得它百无聊赖,毫无自由。以致厌倦了,终于逃亡,去享受那可贵的自由。但是,在垃圾堆和阴沟之间流浪了多天,受尽了饥寒和歧视,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女主人的家里去。我记得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是: “我说的是猫。”
当我正在为午饭而忧心忡忡的时候,忽然门一响,孩子欢呼起来:妈妈归来也!两只手里,提着沉甸甸的菜肉鱼蛋。原来是她在医院听人说,她的两个臣民,逛了半天市场只买了一点水果,不放心,赶紧买一点菜回来解救她的臣民于倒悬。我禁不住和孩子一起鼓起掌来。 这时,我忽然想到左拉的那篇小说的最后一句,应该改为:“我写的不是猫。”
(摘自《愧对书斋:孙绍振心灵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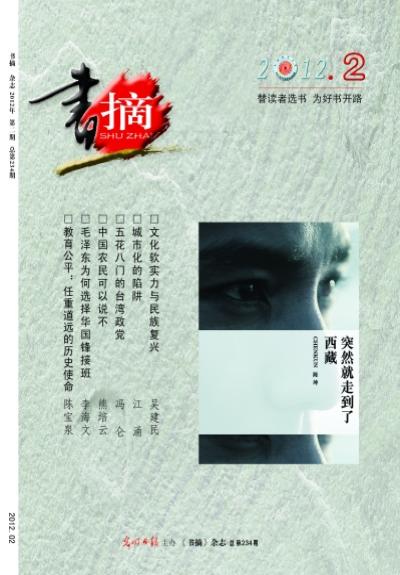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