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也还记得大概是2005年的冬天,读了梁卫星老师寄来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所受到的心灵的震撼。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所期待、所呼唤的语文老师,中学教师,民间思想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等得太久太苦,他终于出现了。我随即写了一封长信,实际是一篇长文,题目就叫《作为思想者的教师》。三年以后,我在《新教育》上读到梁老师的《凌月、樊强、郁青青》,再一次受到震撼,又写了一篇《直面中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这两篇长文都收入了我最近出版的教育随笔《做教师真难,真好》里。可以说我退休以后关于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与思考,都深受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中小学教师中的民间教育思想者的影响,而梁卫星老师就是给了我深刻启发的一位。我的民间教育思想者朋友中,有的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集杂文家的敏锐、犀利与老教师的教育智慧于一身,大气而浑厚;有的如深圳中学的马小平老师,目光远大,思想深邃,具有全球化教育视野,在中学教师中可谓独树一帜。这大概也是我对他特别关注,甚至有些偏爱的原因吧。
但我的“偏爱”,却给梁卫星老师造成了心理的压力。他似乎不愿意接受“思想者”的定位,而强调“我所知道的只是常识”。其实,我所理解的思想者,也就是回到常识,包括“人是有精神追求的思想的动物”这样的常识。因此,在我看来,所谓“有思想的教师”,就是“常识的捍卫者”,就是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我在一篇评论王栋生老师的文章里,就把他称作“合格的教师”),这本来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在当下中国教育的实际环境里,常识、思想都成了相当奢侈的东西,甚至懂常识、有思想,就显得有几分异类了:这都是中国教育的“怪现象”。
尽管梁卫星老师不接受,但在我的观察、感受、理解中,他在我所接触的中学老师里,大概是最具有思想者的品格的,他也因此而承受了教育思想者所必有的矛盾、尴尬、无奈和痛苦。
在我的理解里,思想者(包括教育思想者)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的存在”,思想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敢于直面“存在的困境”。梁卫星老师在给我的来信中强调,“我的文字无关乎教育,只关乎人生”,“教育不是工作,而是我们的存在境遇”,“我所写的是我存在的困境与我应对存在困境的挣扎和反抗”。这背后是有一个“为人生的教育”的存在论教育观的:教育的前提是对人(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和作为教育者的教师)的存在的尊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人(学生和教师)的存在寻求意义,创造“理想人生”;作为现实的,而非理想的教育,又必须正视人(学生和教师)存在的困境。这就是梁卫星老师所说的,人(学生和老师)并非生活于真空,而是存在于社会,它们“包容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所有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它们像空气一样存在于学生(或许还有老师。——钱注)从出生那一刻开始的一呼一吸之中,它们也因此占有了学生(和教师)的肉体和灵魂”,形成了一个异化了的存在(《那些夭折了的花朵》),梁卫星老师又把它叫做“非存在之境”(《教育:生命在语词中行走》)。而教育的使命就是要帮助学生和老师自己,从这样的异化的存在危机中挣脱出来,梁卫星老师说,他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和自己 都“成为自己的反动者”(《那些夭折的花朵》),他又说,教书对他而言,就是“拯救与批判”(《教育:生命在词语中行走》),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这都是显示了教育的乌托邦本质、本性所导致的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对抗性,批判性。而教育思想者正是这样的教育的乌托邦性的坚守者与捍卫者。
因此,教育思想者和现实存在有着潜在的本性上的对抗性,而且他还必须面对,现实存在的逻辑任何时候都远比教育的逻辑强大的事实。这就是梁卫星老师终于醒悟到的:“没有什么人的教育可以抵抗来自社会、家庭、日常生活的教育合力”,“即使你的教育能够抢过学生的灵魂,但你永远也抢夺不过学生的肉体,那将使学生陷入灵肉二分的深刻痛楚之中。我的教育因此注定无力抵抗这些无所不在的大教育”。 这样的“无力抵抗”的失败,在教育思想者这里引发的是巨大的精神痛苦。首先是自我存在的荒谬感。这就是梁卫星老师所说的: “我是不能投降的,我生来就是他们的敌人,这使我更深地陷入了人生的荒谬处境——我的反抗,成为这种社会家庭与日常渗透的教育的强大抟捏力的见证;我的反抗,成为西西弗斯不断推石上山的苦役。”
而失败的教育的后果更让梁卫星这样的教育思想者陷入无休止的自责与自我怀疑:“如果没有我,(学生)会活得虽然混沌,但却没有存在意义上的痛苦;而现在,他们活得清醒,却永远失去了快乐。他们总是让我对自己的教育充满了矛盾和游移。如果教育的影响只能是人生的痛苦,这样的教育还是人道的吗?我自然知道,如果我随波逐流,我的教育依旧是非人道的。我无论怎样做,都是错的吗?十多年来,这个疑问一直折磨着我,让我黯然销魂。我知道,它还会折磨我的,直到我教育人生的终结”(《那些夭折的花朵》)。这几乎是一切从事启蒙教育的思想者的宿命;鲁迅当年不是也在自责自己是“做醉虾的帮手”, “也帮助着排筵宴”吗?(《答有恒先生》)
在我看来,思想者还存在着超越社会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的困境。我进而提出“还思想予思想者”的主张:在我看来,思想者所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怎样”,他对人和社会存在,包括教育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用彼岸世界理想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
在我看来,同样是对教育的关注,是可以也应该有两种方式的,思想者与实践者之间是应该有区别,有分工,而且是存在着不同的逻辑的:“思想者着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并从自己的教育理念出发,对现行教育的弊端作出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思想、舆论的压力,以促进改革,并为其呼唤的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彻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考虑现实的操作。而实践者面临的是教育的现状,不仅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要考虑在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下,改革的可能性和有限性,因而奉行‘逐步推行’的改良策略,这其中也包括必要的妥协,而不可能像思想者那样彻底。这样,改革才有可能稳步而有效地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很明显,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想者和实践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既互补,又相互制约。如果没有思想者所提供的大视野与新理念,及其锐利批判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改革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或者只能在既有框架下打转,变成换汤不换药的表演。反之,如果没有实践者对于思想者的理想的调整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和实践,也会因为理想与实践脱节、过于超前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参看拙作:《我与清华大学的网络评价试验》,文收《语文教育门外谈》)。
这就说到了梁卫星老师这样的教育思想者的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因为作为一个教师,他的主业是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也即进行教育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师主要是一个实践者,而教育思想者却同时要扮演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者的角色,他不仅有自己的教育理想与理念,而且如上所说,他对教育的现实存在以及自己和学生的存在,都有着尖锐的批判,并且以这样的“批判与拯救”为自己的使命。教育思想者的教师,所具有的双重性,必然为思想者与实践者的不同思维、行为逻辑所纠缠,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困境:作为思想者,他要坚守理想,批判现实;作为受到现行教育体制限制的教师,他又必须适应现实,作出各种妥协。要同时兼顾这二者,并把其中的“度”掌握、拿捏得恰到好处,做到该进就进,该退就退,而且进退自如,这是需要教育智慧的,而且还需要鲁迅所倡导的韧性精神。
我从梁卫星老师的教育笔记里看出,他是懂得妥协的,但每一次妥协都给他带来巨大的持续的痛苦,像他在《未来,我们永不放弃——最后一堂课》里所表达的在坚守与妥协之间的挣扎,是令人感动与感慨的。梁卫星老师也不缺乏教育智慧,他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就是一个证明。但他在来信中告诉我,他“对技术性的东西缺乏应有的兴趣”,“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积极进取富于教学艺术的人”。我猜想,这或许就是在他身上,教育思想者的内在矛盾格外尖锐的一个原因。而他的自我怀疑(在我看来,这也是思想者的重要品质)又格外强化了他的痛苦。因此,我觉得他有时颓废一点,“自私”一点,让自己放松、平静下来,反而是必要的。因为我坚信,从根底上,他是不会退缩的。
以上所说,都只是姑妄言之,是不必认真对待的,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
(摘自《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新华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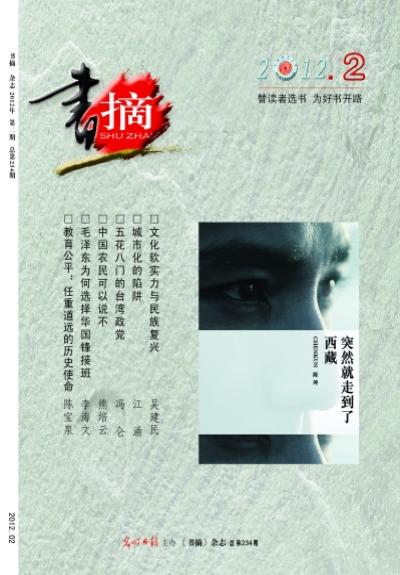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