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西方的舶来品,然而并非在法治方面我们一直落后于西方,因为法律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道德的作用不可或缺。
律师是西方法律概念,大约在南宋时期,欧洲开始出现律师。当时,欧洲的法律刚刚形成,律师就成为司法活动中的重要角色,直到今天,律师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律师收入丰厚,而且还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的大任。相反,宋朝的司法极其完备,司法文明的程度也领先于世界,但是,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排斥律师,律师在那个时代被称为讼棍。宋朝以后,讼棍始终是中国历史上被定性的角色。直到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的律师才改变了“讼棍”的形象,律师才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从战国时代就废除了世袭等级制度,最早的私人讼学也出现于战国时期,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私人讼学的一大特征,即:不是为等级制度服务。这一特点在宋朝更为清晰。宋朝的“律师”们寻找可打官司的缝隙,教人诉讼技巧,寻找法律漏洞。由于宋朝没有世袭的等级阶层,也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为上层等级服务的法律制度,因此,宋朝的“律师”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在广大老百姓身上寻觅机会,挑唆别人把纠纷放大,动不动就去打官司。如果说等级制度下的昂贵律师属于“轻易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的话,那么,在宋朝这样的平民社会,“律师”则属于广种薄收。他们尤其喜欢挑动人们打财产官司,以便从中获得“提成”。
这种现象与中国人一贯主张的“和为贵”是有抵触的,同时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在等级制度下,律师的地位并不比贵族高,因此律师往往要听命于贵族,主动兴讼的事情反而不多。而在平民社会里,律师的专业知识使得他们相对于平民来说更具有权威性,出于赚钱的目的,他们常常在百姓中间挑拨离间。反过来看,中国古代的官员如果犯了法,一般都不会去找律师,因为官员本身都要学法律,甚至可以说,官员自身都在从事法律工作,他们的法律知识比民间的“律师”要强,自然不需要民间律师。而在欧洲中世纪,官员或贵族是靠等级制度决定的,不需要具备知识,因此,一旦遇到纠纷,他们就需要找民间律师帮忙。对于百姓来说,欧洲中世纪时,低等级的百姓很少能有打官司的机会,从财力上他们也难以雇请律师。相反,在宋朝,社会上层不需要律师,律师的生存空间只好向社会基层转移,“滥讼”便很容易出现。
当今世界的法律状況出现了两个逆转。一是,西方国家由于平民社会已逐步发展壮大,“滥讼”经常出现。例如英国有一个案子,诉讼双方因为“偷了一只香蕉”,诉讼费用达12万英镑。美国有一个案子,某女演员在超市偷东西,官司打了几年,最终判决该演员到社区做十几个小时的义工。类似的案例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多,除了律师得好处,这样的案子还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中国南宋时已经出现的问题,如今在西方社会也开始出现。
另一个逆转是,由于西方的法律依然残留着很多等级制度的特征,因此,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有将西方的那套等级制度也学了过来的势头,致使现在不少弱势群体打不起官司。
南宋时期,针对“滥讼”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对诉讼的时效性开始有了规定,这一点也被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所接受。例如,“诸理诉田宅而契约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应交易田宅,过三年而论有利债负准则,官司不得受理”;“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等等。古人说“官司不得受理”,其中的“官司”是指官府司法机构,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法院不得受理”。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行政权与司法权合而为一的状态,才使得“上法院”与“打官司”有了同等的含义,到后来,“官司”也有了“案子”的含义。
从宋朝对“滥讼”的限制內容可以看出,这类受限的民事诉讼大多都是财产纠纷。而这类案件正是宋代的民间“律师”最愿意看到的契机,他们努力寻找这样的由头,挑唆人们打官司,这在宋朝被称为“教讼”或“兴讼”,这种人也被人们称为“讼棍”。史书记载,南宋时一个“讼棍”居然代一位12岁的儿童写诉状打官司。前文提到英国的“偷香蕉”案子,与之颇为类似,即当事人被律师裹挟。寻事打官司。
宋朝的法庭像现在一样,允许诉讼双方各说各的理由,是真是假让对方或法庭去辨析,法庭经常会做出“不予采纳”之类的结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多原因就是当事人或律师夸大或狡辩,甚至枉顾事实地胡说。宋朝面对此类“滥讼”也有规定。宋朝的百姓并非个个都识字,写诉状也是一项专业,而且官府还定有诉状的格式,很多人只能找“律师”代写诉状。宋朝规定,诉状必须只写事实,“不得称疑及虚立证见”,旁人不得“论诉不干己事”。我们今天的“起诉人”或原告,在宋朝被称为“状头”,所谓“不干己事”,就是案件与“状头”本人无关。此外,宋朝还规定,老人或智力不健全者也不可做“状头”,目的是防止他人利用原告的糊涂滥打官司。这类人如果要打官司,必须由其心智健全的亲属代为行事。
而且,宋朝还规定,诉状上要明确写上“若有不实之处,甘坐其罪”之类的文字。这类文字至今在民间告状信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是中国传统的延续。但是,今天的法院,诉讼双方的“不实之处”却屡见不鲜。例如美国有这样案子:一家企业排污,对居民造成了伤害,企业狡辩说自己没有排污。对方就必须花很多钱找到企业排污的证据,一旦证据成立,企业的“不实之词”被推翻,法院的判罚也就是原告提出的赔偿要求,而不会针对企业的“不实之词”增加惩罚。但在宋朝则不会这样,在法庭上撒谎是要判罪的。今天西方的法院也有向《圣经》起誓不撒谎的环节,但真的撒谎了,“伪证罪”的应用也有限。
宋朝在排斥“讼棍”的同时,还发展出一些司法习惯,即“调解”。宋朝的调解有多种方式,既有法庭上官员的亲自调解,也有鼓励亲戚邻居劝和,还有令当事人双方“自行和对”,再有就是在司法判决中“调判互用”。例如,即便当事人双方接受了调解,法官也会告诫“如若再犯,定当严判”之类。或者在调解之后,附带其他的判决。例如,南宋一位法官在处理一起父子财产纠纷时,调解完成后,判令儿子读《孝经》一个月。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说,法律条文中没有这样的条款。但是,从“判例法”的角度,这样的判决却可以成为后世法官的判例。
调解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与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相比,调解也只有在中国出现,至今依然在我国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提倡调解与排斥“讼棍”正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律师以打官司为生,无论如何,这个行业都不能创造真实的财富。如果任由律师为了多赚钱而打官司,一些不必要的官司会闹上法庭,一些简单的官司会拖得很长。宋朝的法官们明确地说,这会造成“本业荒废”,徒然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一认识对当今社会也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比方说,当今西方社会律师业发达的国家,都是富裕的国家,否则,社会财富无法供养大批律师。从更深入的视角看,所谓法治发达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大量的财富基础上,法律是一种奢侈消费,穷国根本消费不起。
这样看待法律并非是说社会不需要健全的法律,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过于繁琐的法律对社会也会造成伤害。尤其是当律师只在繁琐的法律条文中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的时候,法治便违反了初衷,成为少数人保护自己、维护自己权益的工具。我认为,当今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正义超出了实质正义,得利者只是那些设计制度和有能力操纵程序的人。中国古代法律中出现的“调解”,与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管理的 “调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致的。因为差异总是存在,只要差异没有太过分,没有绝对化,比较公平合理地形成差异,社会才和谐,这就需要调和。
虽然今天法院等机构的调解与古代已经不太一样,但我们还是应该理解一下古人推行“调解”的真正意义。我认为,它的意义就在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政治以人人安居乐业、天下太平为目标。但这种太平并非是不合理制度下的强制性约束,而是一种在社会公平合理基础上的自觉,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有所养、幼有所爱”等等,就是这种体现。为了这样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古代政治家还要关心鳏寡独居的人,以减少他们的孤独。
中国古代政治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的首要手段是道德,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为了让道德原则能够体现,对于每个人来说,首要遵循的是“礼”。 “礼”作为一种习俗,成为贯彻道德原则的外在工具。它既具有强制性,也具有随意性。违背“礼”不见得要受到惩罚,更多的时候,违背“礼”只是一个教育问题。通过教育和榜样的力量,道德原则和“礼”是一种自觉,由此而形成的规范,使得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只要内心遵从道德,行为遵守礼仪,就不至于出太大的差错。
法律具有强制性、暴力性,法律是在道德失效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与法家并不一致。儒家主张先教化,后法律;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面对人性中所有可能的缺陷。宋朝关于儒家和法家的争执也很突出,其典型就是对待王安石的评价。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王安石父子都配享孔庙,被视为儒家的圣人。但是,很多人都指出,王安石实际上是一个法家,直到现代依然有很多人持这个观点。事实上,宋朝恰恰体现了儒家和法家的一个折中。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说,宋朝的法治体系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不亚于当今社会。但是,宋朝的刑罚又是相对较轻的,也许可以称之为“重法轻刑”,它体现了教化和鼓励人们自觉的社会价值观。
在这种价值观下,法律是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最后才采取的手段。当社会还有其他温和的手段可以用的时候,就不必抬出法律的手段。具有暴力性的法律是社会和谐的最后防线,而不是冲在最前沿的威吓。这样一种治理社会的价值观能否实现,取决于公共道德的普遍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是否能够实现。
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欧洲的世袭等级社会正好与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倒过来:首先用法律来维护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此后才通过道德表达一下对下等人的关心。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对于教会道德的虚伪性有很强烈的批判,但也矫枉过正,反道德、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先进和文明的标志。正是由于虚伪的道德钳制了欧洲一千年,因而使得文艺复兴之后的反弹更为强烈,至今都处于矫枉过正的状态,没有摆正道德与法律的合理关系。
简化一点说,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提出的问题是:道德与法律,我们需要哪一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智者试图借助中国的方式解决宗教退出后的社会道德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这个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道德与法律“二选一”的状态。西方社会至今依然强烈的制度崇拜,正是这种“二选一”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这种“二选一”的状态,而是相互结合地使用。只不过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结合的方式不太一样,有时候偏重多用道德,有时候偏重多用法律。
以宋朝来说。从北宋开始的一系列变法活动,都是主张多用法律的体现。而在南宋时期开始成为正统的理学,则是要求多用道德。后人评价说,“有穷之律,终不能治无穷之情”,这里的“情”是指私心。也就是说,法律并不能穷尽一切可能性。而道德作为一种原则,可以使人们在面对各种可能性和变化时,自己做出抉择,而不必事事寻求法律。南宋以后,宋明理学长期成为正统,只说明中国古人主张治理社会应该道德为先,而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人只要道德,不要法律。本来,这种歧见在中国的环境中也不至于发生,但是,由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有着强大历史“进步”意义。因而,在欧洲中心论的主导下,很多用来解释欧洲历史的观点,都被搬来解释中国历史,从而造成了很多谬误。
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与欧洲不同,根本原因还在于等级社会与平民社会的不同。如今,欧洲渐渐进入真正的平民社会,渐渐开始发现中国传统的真正价值。而我们已经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给了传统太多荒谬的结论,抛弃了太多传统的精髓。
(摘自《超越利益集团:对宋朝史无前例的狠毒解剖》,中国书店2011年9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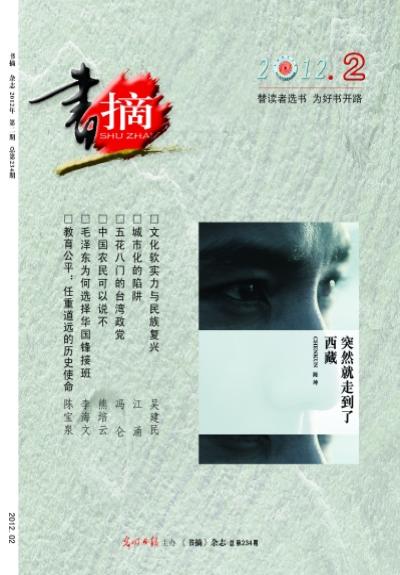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