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方圆几十里,可以说父亲是一个苦命而又终生勤劳的善良人。父亲很小的时候被他的养父母收养,那时养父母不生育,也就比较疼爱收养的儿子。后来没几年,养父母却生了一个儿子,自从有了亲生儿子后,我父亲就越来越感觉到养父母对待他和弟弟的差别。
我父亲说他这一生中上学最艰辛。上小学时,养父母供他读书。到了小学毕业时,养父母觉得在农村里,能认得自己名字就可以了,上那么多学没有多少用,打算让我父亲给家里挣工分,就不想让我父亲再继续上初中。可是倔强的父亲一心想读书,就说自己找学费上学。在解放初期那些年里,要想找几毛钱,其难度可想而知。父亲就利用星期天去附近山上拣柴,回来再去卖掉,换回几毛钱,日积月累,攒够自己的学费。父亲说最苦莫过于在上元观读书那几年。学校距离家很远,就得住校。这样每天就得在学校食堂吃饭,吃饭的伙食费每天都开销。这比学费多多了。学费一个学期再贵也就一次,可是吃饭钱,每顿都不贵,可缺了那顿都要忍饥挨饿。父亲也想到了上山砍柴卖了交伙食费,可是学校离家太远,星期六放学回家后天已经黑了,星期天下午还得早些返校。这样一来,每周末也就多半天时间。如果上山砍柴挑回家,就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卖柴了。父亲就找学校老师,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说学校食堂每天做饭都得烧柴,自己每周都给学校挑一担柴,折合成伙食费。好在那个老师很开恩,给学校食堂管事人说好后,同意了父亲的请求。父亲就这样,每周星期天一早吃饭后去很远的山上砍一担柴,挑回家就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了,吃过午饭,又得挑着上一周放在家里晾晒干的柴往学校挑。就这样自己用柔弱稚嫩的肩膀,铺就了自己求学的路。我没有问过父亲,当时在学校像他这样自己用肩膀供自己上学的是否还有第二人?我每次欲张口,总怕勾起父亲伤心的回忆,因而这几十年里,我也就始终没有问过父亲这个问题。
父亲总想找个机会,离开贫苦的农村,在外找一个工作,养活自己,所以他上学期间读书也就特别用功。到了毕业前夕,父亲的一个同学得知县公安局要招收几个公安人员,那个同学悄悄问我父亲是否愿意当警察,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多久,那个同学就给了父亲一张表格,让父亲填写。有一天那个同学又叫父亲一起去体检,体检也很顺利。之后,就是等公安局通知去上班。在等待期间,毕业也就临近了,学校推荐保送父亲上师范学校。由于父亲一心想当警察,就没有答应保送上师范学校。因而保送上师范学校的推荐表就给了其他同学,当时的班主任傅老师对此很不理解。有一天那个同学急忙给我父亲说,本来县公安局已经决定录取咱们几个当警察,就准备马上发通知了,可是地区征兵办公室通知县公安局,最近有几个退伍军人,要求县公安局接收为警察,这样咱们几个当警察都泡汤了!父亲听到这话,欲哭无泪,心中的万分希望,顿时成了肥皂泡。更为悲痛的是,自己被推荐保送上师范学校的机会已经成了别人的快乐!
很快就毕业了,父亲带着满心的伤痛又回到了村里,随同村民们起早摸黑地从事农业劳动。在村里劳动几年后,父亲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我的母亲。他们结婚后,在老屋住了没多久,就因分家被迫搬出去租房居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村里,农民租房居住,恐怕也难以找到第二个人。就这样,父母开始了独立生活。在那个年代,各地工矿企业等单位,也都陆续从农村招收一少部分文化水平高、办事能力强的人,直接成为国家正式职工。我父亲回村劳动的那些年里,确实有几次很好的机会瞬间光顾过我父亲,但是由于家庭清贫送不起礼给村里管事的人,加之父亲耿直不愿多求人,况且这种招工招干的好事,你不求人,有的是人抢着给管事人送礼。最有希望改变父亲命运的一次是连体检都进行了,就因为没有给村支书送礼,支书不发话文书就不给在政审表上加盖公章,导致最终换人。这一次,让父亲彻底伤心了。此后不久,父亲带上简单的行李,就去青海找工作了。后来我听父亲说,他在门源县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工资太低,又吃不饱,干了几个月后,实在难以忍受饥饿,就辞工回家了。此后,父亲也就不再抱希望外出,只一心想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读书,尽量满足我们上学读书的愿望。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曾跟我们几个说,只要你们能考上大学,我就是拆了房子卖房梁,也要供你们把学上完。
在农村,修房是一个家庭的最大事。父亲在村里一边劳动,一边供我们几个孩子每年的学杂费,同时还得节衣缩食攒一些钱为修房做准备。父亲曾多次跟我说,在农村,尤其在我的故乡,一个家庭四五十年里,能修一次房就很不容易了,在我老家,有些人一生都没有能力翻修一次房屋,而我父亲没有借亲戚朋友的钱,也没有去农村信用社贷款,曾四次修房。我家房屋的那些大小梁和椽子,几乎全是靠父亲的双肩从巴山深山里一根一根扛回家的。那个年代,白天整天在生产队干农活,每年都没有一个假期,因而扛木头的活,全部都是事先私下打听到什么地方、谁家有存放的可以用来修房用的木头,然后夜里吃饭后摸黑走山路,到了卖木头的地方,把人家叫起来,商量好价钱后,再赶紧往回扛。路上连歇气都不敢,必须赶在天亮之前到家,然后生产队开工时,还得跟大家一起再干农活。劳累和困乏就不用说,还得坚持干一天活,说不定夜里还得加班干。父亲就是这样,隔一阵去一趟深山里,一根一根扛回了两间房屋需要的大小木头,料备齐后,就是找地基,然后再去山区里拣石头砌根基用。父亲第一次修了两间草房,房屋修好后,就从租的屋里搬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父亲第二次修房,是在自己的草房里住了几年之后,父亲觉得草房有些旧,也落后了,该换成瓦房了。于是,父亲又开始一点一点再次准备木料。这次,父亲心中的房子是四大间瓦房。在准备了一多半的木料后。父亲就开始自己动手,租赁制砖瓦的工具,自己做砖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把砖和瓦都做好晾晒干后,又自己在我家房后坡边挖窑烧砖瓦。而烧砖瓦的所有柴,也都是父亲一趟一趟用肩头挑几十里山路担回家的。父亲烧窑时,请了附近的烧窑把式,请人家指导掌握火候,以及烧制的时间、填埋窑口的技术要领等。但人家只是指导,其实活都得自己干。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窑口那灼热的火浪还依稀记得。父亲为了修房,哪顾及到自己身体被高温的窑火炽烤,一心想的就是烧制成功。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就更加信心足了,在干好农活多打粮食多余钱之外,利用一切农闲时间干手工活攒钱。第三次修房时,是在正房西北边一次修了四间砖瓦厢房。这次,由于家里已经有了一些积累,四间厢房除了木料是原来修四间正房时剩余的木料添补少量不足外,所用的砖、瓦和地基石头以及沙子等材料,也都全部购买了。父亲修了三次房屋后,单从住来说,已经完全够了,可是父亲还总觉得农村柴草多,堆积的地方少了点。特别是每年的两个农忙季节,晾晒粮食时遇到下雨抢收堆积地方紧张,加之各家后来陆续都修起来两层楼房,所以父亲心头一直有个结,想再把四间正房换成两层楼房。这次,准备时间不多,就是决心一下,就开始动手请施工队,买楼板、钢筋、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一两个月工夫,楼房就修好了。
在我们家乡,修房造屋是农村家庭最大的开支,也是许多农村居民终生的期盼和梦想。但是,绝大多数人家,几十年里,也就修一次房屋,最多一个人一生修两次房。然而,父亲自从跟养父母分开过日子租同村人房子开始,可能就在父亲心中萌生了修房的梦想,而且修不次于其他人家的房屋。所以,父亲一次又一次修房。在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同时,向村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不借款修房,而且修的房屋不比其他人家的差。后来,我们三个孩子都陆续离开村庄。到其他地方读书,进而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工作。遇到逢年过节时,我们三个孩子才能回家看望父母。这些年里大多数时间,都是父母和小妹一起在老家村子里居住生活。再后来,小妹结婚后也随同父母生活在故乡的老屋里。母亲在五年前离开我们全家西去后,就是小妹妹一家三人陪同父亲在老屋里居住。自去年以来,小妹又经常离开村庄,去城里陪同她的女儿读书。如今,经常是老父亲一人在空旷的院子里转悠。我想,即使父亲再孤单,只要看着自己一生四次修造的这些房屋,也会欣慰吧。
父亲在体力好时,不单自己没黑没白地承担了全家的繁重体力活,还经常帮助村里其他家庭干活,小到忙季的抢收抢种,大到修房造屋时的抬楼板、扛水泥袋、拉砖瓦,甚至也帮助别人家从山区拉石头,到深山区摸黑走夜路扛木头等。全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或多或少得到过父亲的体力活帮助。因而,在故乡村庄里,提起父亲的为人,那绝对没有争议。
勤劳朴实的父亲,终生话语很少,但他用自己粗糟的双手,红肿的肩膀,满是伤痕的双腿,支撑起了我们六个人的家。每每想起这些,我们都为因这样或那样原因不能在节假日赶回家多陪同孤单的老父亲感到愧疚。
沉默寡言的老父亲,如同故乡老屋南边那无言挺拔的巴山,将永远矗立在我心头。 (摘自《故乡背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24.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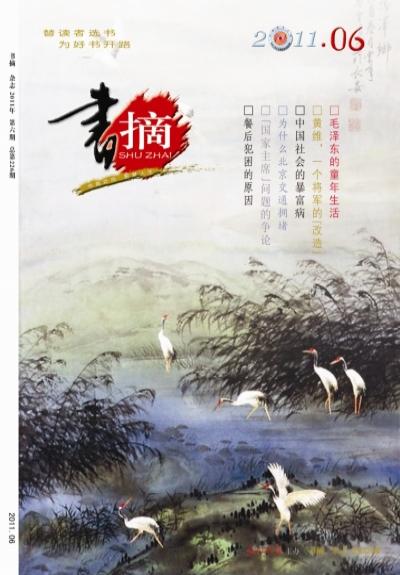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