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以“傲”著称,被认为“向来不爱接受媒体采访”。在《唐山大地震》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冯小刚说:“这些年陈道明变得特别随和了。”陈道明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不是的,其实我一直挺随和的。”近年来,对电影或者电视剧完成后,制片方的宣传需求,陈道明逐渐理解了,也参加了不少集体性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原则是只回答有含金量的提问。”陈道明说。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
张 英:媒体上描述的陈道明是难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你是温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个陈道明更接近真实?
陈道明:如果把这两者视做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就是20世纪90年代那一阵子。好在我这种状态持续时间比较短,没过两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过,可能有时说话不大注意,是不是会伤到别人?这次拍《手机》,别人问我王志文好合作吗?我说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个规规矩矩做事的演员,我反问“干吗非得叫他哈着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后就有人说我和志文不合。
张 英:这些年对娱乐界的大环境有怎样的观感?
陈道明: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戏好,老百姓喜欢,才有长远的名利。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唯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纵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张 英: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现在许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后基本上都变成了江湖班子,说白了,耍玩艺谁耍得能吸引人,谁就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唯一的标准。
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总盯着收视率,放三级片收视率最高了。电视台有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不能眼里就是钱。
一个甚至一批不好的电视台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人想、没人问、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收视率高就放什么,怎么能这么纵容它们呢?
而且现在主宰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都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调查标准也没有。谁是标准?这些假收视率影响着广告投放,影响着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影响着几亿老百姓,但它的基点是假的。靠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说谎,一个社会结构在讲假话,但是没有人处理它们。
我们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
张 英:你最早是从电影《今夜有暴风雪》走进影视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太认同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银幕,就看低电视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演员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当时进这行,就是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有一个正经的城里饭碗,这个饭碗跟文化沾边。那时候都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则根本没有。
起步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现在的演员不同,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竞争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多功利性。
随着年龄的变化,我的人生观有一定的转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成功人士是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张 英:相比电视剧,是电影不给您机会吗?
陈道明:不是。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赶上我不想拍戏,后来凯歌就找了孙红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签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个信息,说算了,我还是不拍了。后来周润发接了孔子。
张 英: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是,有的剧本很好。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真没有好电影。
张 英:你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陈道明:好电影应该是讲一个完美的故事,有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性,要有完美的表达,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着观众往前走,有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电影画面,看不见任何刻意的造势。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张 英:你这个标准包括哪些电影?
陈道明:这样的电影太多了,比如《目击者》、《轿夫》,包括《毕业生》这种轻松的电影,也包括法国电影《蝴蝶》、美国老片《魂断蓝桥》。
张 英:中国电影里哪些电影是你认为能得85分的?
陈道明:我不想说,得罪人。我觉得中国导演的好年代还没有到,我们都是拉纤的纤夫。不光是电影,文学、美术、音乐也一样,我们只有艺术家,没有大师。我们拍电影的受各方面的制约,那些编剧和导演也是很痛苦的。目前电影的繁荣和热闹就是一些票房数字,它真正的成熟和健全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个时代还没有来,我相信有一天它会来的。
张 英:我们差在哪里呢?
陈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那时候我们拍《围城》,10集的电视剧,按现在的节奏,满打满算就一个月,但是我们整整拍了100天,那时还有创作可言,现在哪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不适应现在这种两天一集、三天一集的模式,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已经不符合基本规律了,制片人不管导演怎么拍,但你一天必须得消灭多少页剧本!所以现在出现了一大堆烂玩意。
过去的老电影比如《芙蓉镇》、《老井》,可能有破绽,电影叙述得比较笨,叙述得不那么智慧,但憨厚也是美,电影里的那种力量、劲道非常扎实。
过去是“占一个便宜”就行了,现在是什么便宜都要占,华丽、假贵族,憨厚是狡猾的憨厚,属于城乡接合部的憨厚,不尊重人。你蹲下身段了,以为观众也和你一起蹲了下来。现在的电影人不纯粹了,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电影的认真氛围了。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
张 英:你有点恨铁不成钢。中国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一个很好的势头时,突然就一头往下了。
陈道明:让钱给冲没了。中国的文人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我说的这些人里头也涵盖我——既然你风骨了半天,怎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的,我也拧不过。没错,我也为五斗米折腰。但我觉得可怕的是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我以及一批在虚荣上跳舞的人,还念及一份美好;现在更多的人是连这个美好都没想过,我是不是比他们好一点?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知道反省的人。中国电影进步的基础不在于炫耀,而在于反省,可是中国有多少人有反省精神?
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年轻的演员没有自我,整天勾心斗角千方百计想着炒作自己,为出名挣钱不择手段;什么叫“为老不尊”?根本跟你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要跳出来大骂。
我也虚荣过、轻狂过,现在让我放下这份虚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尽管我不断在教化自己。
张 英: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把它称为“纯真年代”,你怎么看那个时期的电影?
陈道明:我不喜欢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有属于它的电影形式和表达方法,不是好和坏的问题,就像我们看过去的《地雷战》,不代表它作为电影有多么好,电影也是随时代进展的。要说怀念的话,我怀念那时候的文艺思想,是积极的,是上进的,还有一种刻苦劲。
现在是糖和味精都进来了。其实,我始终梦想的电影是不着急不着慌的、慢慢的、一点一点、讲讲究究地拍,不要这么仓促、匆忙,从容一点对待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惊世之作对我来讲不重要,但这个过程会很舒服。
张 英: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过渡时期?
陈道明:电影院线改革,电影就走市场、走商业片的道路了。那个时候电影厂纷纷倒闭,西影、长影、上影这些老牌厂,后来纷纷变成租赁单位,演员队伍、导演队伍也没了,电影好像就完了。谁之罪?不知道。跟总体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吧。直到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中国电影都没有喘过气来。
张 英:很多人往往把没有好作品归结于审查制度,但在更加严酷的环境里,为什么伊朗导演能拍出好电影?
陈道明:“意识形态”可能成为托词。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不能说没影响,但美国的主流电影有多少感人的小故事?像《当幸福来敲门》有意识形态吗?《诺丁山》有意识形态吗?无能就是无能,就像中国足球,开始时说因为伙食不好,后来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你自己没有演好。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都在商业这棵树上下功夫了。
张 英:电影局现在就抓两手:第一,主旋律拍好;第二,商业片导向把好,不出事,高票房。
陈道明:治标不治本。
“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张 英:按照你的地位和名声,你完全可以找个投资商,找好导演和好编剧,找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陈道明:当然不是问题,而且做到这一点很轻松。很多老板都要给我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我做导演,我不做。
一是我觉得累,我从疲劳变成更疲劳,我要管人不自由,要别人管我更不自由;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的,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我只能努力适应这个商业、消费时代,在可以适应的范畴之内寻找自己的舞台。这个过程很艰难,可选择的余地很小,在这当中尽量寻找我能完成的作品,文艺和商业都可以并存的作品。纯商业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如果两者选其一,我当然还是选文艺。所以说,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我们现在动不动让外国人来演戏,我觉得是对中国演员的一种侮辱,那些角色完全可以用中国演员来演,因为是中国戏。我们没有合适的演员吗?非要找国外的演员来演?我不信,别找借口。这不是国际接轨,文化上,永远国际接轨不了。
张 英:你是中国价格最高的演员?
陈道明:应该说是标价最高,因为我不想接太多戏。我入这行这么多年,直到近几年,就一个摄制组给到790万这么多钱。
我上戏的原则是这样的:制片人来跟我谈上戏,我首先看你剧本怎么样,如果剧本不错,我再和制片人见面谈合作,问他戏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是一般的戏,成本又不高,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为什么呢?你给我这么高的价码,其他演员你请什么人呢?阿猫阿狗吗?你靠着我耍大刀去?所以我不会上的。
很多电视剧,剧本不错,但投资有限,花在演员片酬上的预算很紧张,像《中国式离婚》找我,制片人朱志斌跟我反复谈片酬,我特别随性,按标码我是15万一集,我打折一半,7万一集接这个戏,因为我爷爷、我父亲都是医生,我一直想演个医生,就接了《中国式离婚》。拍《手机》的时候,制片人说请演员没钱,我说你拿出我的一部分片酬,用这部分钱去请另外两个我喜欢的演员来和我演对手戏,于是,我的片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这可能是我潜意识的文艺思想在起作用,我想做的戏,不拿片酬也演。就像这次《唐山大地震》,小刚问我要多少钱?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也上,因为我有地震的情结,也因为我对军人有敬仰,我想完成这个心愿。我说你不要跟我谈片酬,给我合同,我给你签上字就完了,我连看都不看。
张 英:挺有意思的。价格现在成了一个演员的价值和标准。
陈道明:我不认为我最好,我也不认为我最贵,我永远是看片论酬,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不上就是不上。
张 英:你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陈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来,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
更悲哀的是,我们看到了,却改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远离人群,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现在让自己边缘化,就是这个原因。
(摘自《中国文化现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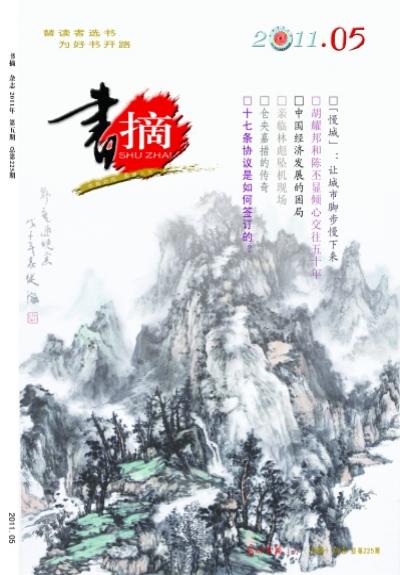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