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曾作为大使尤金的中文翻译多次参加与中国领导人的外交会晤。那时候,苏中两国两党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双方互通对国际共运和两国重大政策的情况与观点。尽管也会出现意见分歧,但双方都还能通过友好协商、交流以达到基本一致。应该说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任苏共总书记初期,对中共毛泽东主席还是比较尊重的,苏共一些重大决定都会及时向中共领导通报。苏联人对中国这一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兄弟国家曾寄予最大的希望。中国人也对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怀着真诚的感激。但至50年代后期,两国两党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候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1958年在中国兴起的“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曾使我们的苏联领导人大惑不解。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几个新的政治名词是在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按双方互通消息的惯例,由中国领导人通过外交会晤正式传达给苏联方面。这次是由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传达的消息。
我记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在座的还有为刘少奇主席担任翻译的赵宗远先生。当刘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时,我在脑子里就开始琢磨如何正确翻译他所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在俄文里还不曾出现的新政治术语。根据其中文原义,我起初想的是将“大跃进”译成俄文为“快速的运动”将“人民公社”译为“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当我听了刘少奇主席进一步阐明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具体涵义之后,我立即否定了我起初意欲翻译的这两个俄文词汇。于是,我用更能贴近中文涵义的俄文直译为““大的飞跃”一词,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应用“人民公社”这一新词。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译刘少奇主席的谈话之前,我特地先征求了在座的中国资深俄文翻译家赵宗远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说明,思索片刻,当即表示赞同。他认为,如此翻译已非常准确达意。他尤其欣赏我用公社,说这个词翻译得恰到好处,比之俄语中的同义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能达致其意。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主席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当我们离开刘少奇主席办公室时,我再次同赵宗远先生交谈了我对翻译这两个重要政治名词的观点。随后,我将整理的翻译记录交给了尤金大使。
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 “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他说他看见我同中国翻译赵宗远谈话,他认为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译法。当我再次肯定并确认翻译无误时,他仍表示怀疑,对我说道: “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解,难道尤金大使会认为,是我错误翻译了刘少奇主席的原话?
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那么,中国人发明的这两个政治术语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这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他仍然认为,刘少奇曾经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不可能提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如果这两个政治术语的俄文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可以说,尤金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苏联理论界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能否为我们苏联领导人所接受?我却不得而知。在我看来,我们苏联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就是以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农工体系代替了合作社经营体制。实际上,中国农村也经过土地改革,成立了互助组和合作社,然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农村人民公社。此外,中国也有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农林垦殖场。我认为,这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中国和苏联都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将中国的农业体系和农村管理机构命名为“人民公社”,以加速工业建设的“大跃进”来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或许毛泽东是借鉴“巴黎公社”的名称来命名“人民公社”的。这确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问题是中国这次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在很多方面仿效苏联的经验。我个人认为,这也许是令尤金大使感到不可理解的原因。
为此,尤金大使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研究讨论我对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
我立即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我对刘少奇主席的谈话翻译得正确与否将关系到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这场政治运动的看法。但我作为苏联使馆的外交官和首席中文翻译,我的工作职责只能忠实于翻译本身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我必须正确理解和准确翻译这两个关系重大的政治术语,尽管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典中不曾出现的新名词。
于是,我在这次使馆内部会议上再次将中国领导人召见我大使的重要谈话做了详尽的译述,并向与会同志解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俄文新词的来由。
在那次使馆内部会议上,尤金大使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因为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可能会使苏联人对中国人的观点不易接受,很可能会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关系出现裂痕,而势必影响两国两党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他提出为验证我的俄文翻译的准确性,可否用另外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的同义词来翻译这两个政治名词。但我仍坚持己见并力陈我如此翻译原义的理由。出乎意料的是,使馆大多数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译。之后,尤金大使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中央。
然而,据我所知,苏联方面对中国广泛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沉默。
不久,北京新华社《俄文电讯》刊载的《中共中央决定》最终确定了我对这两个词的俄文翻译。这以后我了解到,在那次刘少奇主席会见尤金大使之后,赵宗远先生即将我翻译的这两个俄文新词报请刘少奇主席批准,在新华社《俄文电讯》中首次采用此俄文译词。
这以后不久,在中国对苏发行的刊物中,在中国对苏俄语广播节目里,以至在中国出版的俄语教科书和词典中,都出现了这两个新的俄语词汇。然而,在苏联出版的《汉俄词典》中却未收录这两个词汇。也许苏联人认为,这两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政治词汇,其实却是我这个苏联人翻译的俄文词汇。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译首先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确认。这是我未曾想到的结果。
这一年,中国开始在全国各地兴起声势浩大的“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亲笔题词: “人民公社好”。他甚至提出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这使中国人为此感到奋发抖擞,然而却令我们苏联人感到不可理解。这期间,苏联依然没有对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攻击和抵制,苏中关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在推崇“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国分别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向共产主义迈进。
这以后不久,苏共和中共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最大的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导致苏中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至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公开论战并愈演愈烈。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苏联从此终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至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后,苏中关系恶化依然加剧。
毛泽东曾经在他的一首诗词中这样写道: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曾因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定罪的中国杰出军事家彭德怀蒙冤致死,曾经作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坚定支持者的刘少奇也屈死狱中。他们都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直至毛泽东去世后他们才得以平反昭雪。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抚今忆昔,感慨万端。屈指算来,我记忆的这段往事已历经半个世纪。这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令人欣慰的是,1989年的春天,苏联终于结束了同中国冷冻了30年的历史。两国人民重新友好,携手走完了上个世纪的冬天,又并肩走进了新世纪的春天。
这是我们希望的春天。我们唯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摘自《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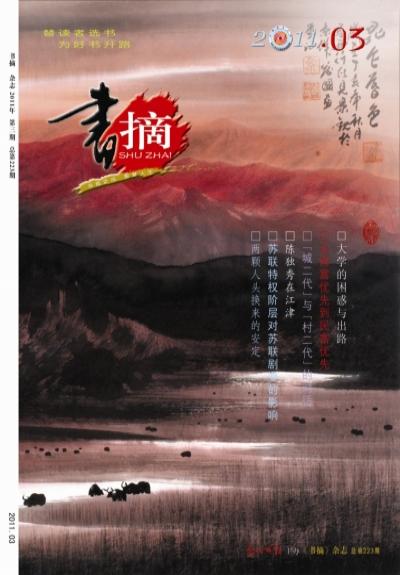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