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是美国公民,却自称为“流亡移民”。他是教授和文学评论家,却自称为“局外”知识分子。他是新教圣公会教徒,娶了个贵格会教徒妻子,却又维护伊斯兰教文明,说自己是个“由穆斯林文化包裹起来的基督徒”。他在西方做学问,却以“东方学”研究成果著称。有人说,他既是学者,又是斗士。有人崇敬他,也有人憎恨他,但没有人可以否定他对当代世界文化和思想的重大影响。
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典型代表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阿拉伯家庭。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国,耶路撒冷属于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他父亲经商,在埃及有生意,所以他是在开罗长大,上过当地的美国学校,后又入维多利亚学院,同班同学中有未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1950年代初,他父母把他送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在那里他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64年修得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任教,直至2003年因白血病去世。哥大师生始终因有这样一个出色的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典型代表而感到骄傲。
他的身世曾使他感受到认同危机。他曾写道:“有‘萨义德’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阿拉伯姓氏,还带上一个未必要有的英国名字(我母亲在我出生的那年很崇拜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我在早年一直是个不大自在的特异学生:一个巴勒斯坦人在埃及上学,有一个英文名字,一张美国护照,却根本没有肯定的身份。”
他又说,他是一个“过着两种不同生活的人”。一种生活是当美国大学教授,另一种生活是当美国和以色列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强烈支持者。自1977年至1991年,他是巴勒斯坦国家委员会——一个流亡议会的成员,曾协助起草巴勒斯坦新宪法。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将他视为“激进派”,而巴勒斯坦人又把他看作“温和派”,因为他曾劝说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从而突破中东问题的僵局。
他常说,他从未感到自己完全隶属于哪个国家;他既受阿拉伯文化,又受美国文化影响,是一个并不专属于哪种文化的“外人”。由于他经常在书面声明、讲演和采访谈话中公开为巴勒斯坦辩护,指称巴勒斯坦是以色列野蛮政策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出于无奈而采取某些暴力和恐怖行为也可以理解。某些犹太组织便攻击他,说他“纵容恐怖主义”,说他是“纳粹”,甚至派人到他办公室放火。《评论》杂志有篇文章把他称为“恐怖教授”,结果引起很大反响,为他辩护的人中包括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政治学教授写道:“把萨义德描绘为一个恐怖主义政策的狂热信徒,这是对他作为学者和斗士的一生工作的严重歪曲。”萨义德自己声明说:“我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不仅是巴勒斯坦的恐怖行为,我也反对以色列轰炸难民营的恐怖行径。”
出于对萨义德的憎恶,有个以色列学者居然花好多年时间去调查他的早年生活,在他生平上大做文章,指责他编造了“巴勒斯坦童年”的“感人故事”,说他的童年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开罗度过的。为此,萨义德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他小时候在耶路撒冷和开罗两个地方都生活过,从未否认自己在开罗度过童年。他说:“不管怎样,我不认为那有什么重要。我从未把我自己的事情当作问题提出来。我提出来的是我的民族的事情,那是有很大不同的。”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观
2000年7月,因一幅广为刊登的照片,萨义德被卷入了一桩意外的“国际事件”。在那幅照片中,萨义德正站在黎巴嫩边界,手举一块石头,似乎要朝以色列警卫队房子的方向扔去。当时萨义德一家正在黎巴嫩旅行,听说了以色列终止侵占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好消息,他“因高兴而有此象征性举措”,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一片抗议声浪随之而来。有些人强烈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谴责萨义德的这种行为。数月后,哥大校方发表声明说,萨义德的行为得到学术自由原则的保护,不必对他采取任何行动。教务长科尔在给学生会的公开信中写道:“据我所知,那块石头没有瞄准什么,没有违反什么法律,没有引起谁来告状,所以就没有必要对萨义德教授提出刑事或民事诉讼。”教务长要给学生会写信,这是因为哥大学生中有很多是来自犹太家庭,他们对萨义德教授的“义愤”不能等闲视之。
或许有人会想,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博学的教授,萨义德又何必去卷入中东地区难解难分的争端,去承受舆论界那么多攻击,也招来某些学生的不恭?他既然已经是美国公民,又何必反复强调自己是“逃亡者”、“边缘人”、“离散的巴勒斯坦人”?他既然可以长年享受曼哈顿晨边高地校园和书斋生活的宁静,又何必去当得罪人的“斗士”?他既然已经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学与社会》等力作问世,尤其是《东方学》 (1978)一书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大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之确立了在世界学术界的显赫地位,又何必去为巴勒斯坦人起草宪法?他既然早在1991年就发现自己罹患白血病,又何必不颐养天年,而仍然念念不忘于他的“业余”事业?
这是些很容易提出的问题,或许也是容易解答的问题。如果我们读一下他的另一本力作——《知识分子论》[一译《知识分子的表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或许就能明白,作为一个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他为何要这样做;就能明白他始终铭记着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并且特立独行,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奋然前进。
萨义德阐述了他自己的知识分子观。
他说,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中有特殊公共作用的个人,不能降为一个无个性的专业人员,不能降为一个只能干其本行工作的称职人员。他所发表的信息、观点和见解应代表公共大众。他应意识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能公开提出质疑,对抗正统观念和教条主义,不易被政府或大公司征用,其立场代表常被遗忘的人们或被掩盖的问题。
他说:“在我思想中,毫无问题,知识分子同属于弱势的和无人为之代言的人的一边。归根到底,知识分子,在我的话语感觉中,既不是橡皮奶头式的抚慰者,也不是一致意见的达成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整个存在是在施加一种批判力,这种批判力不乐意接受现成的公式或陈词滥调,对权势者或守旧者不得不说的话和做的事,也不轻易地加以肯定。不仅是消极地不乐意,而且要在公众中乐意积极地说出来。”
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现状搅乱者。”他说,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作用是“向权势说真话”。 “不要只说一些趋附时尚的话,而要说出官场内说不出来的真实的思想和评价”。他发挥葛兰西的观点说,知识分子应该维护广泛的公正权益,尤其要为社会上被不公正地剥夺了权利、被压迫的人说话。他告诫说,独立知识分子要拒绝权力、金钱和特殊化的诱惑,也永远不要因为怕人说“不爱国”而胆怯畏缩,放弃批判的武器。
他认为,思想家可以“局外人”的身份在我们社会里发挥批评作用。处于主流地位之外,“局外”知识分子更便于批评所谓“爱国的”民族主义、公司观念、阶级意识以及种族或性别歧视。
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性”,赞赏“业余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所谓“业余知识分子”是与“职业知识分子”对照而言。他看到当代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们——编辑、记者、学术或政治顾问,等等,均由独立地位转向与有权有势的大公司、政府或学术机构结缘。一个职业知识分子,或为“发给工资的大学”工作,或为“要求忠于党的路线的政党”工作,或为“答应给予自由做研究的智囊团”工作,到头来难免会“微妙地损及其判断,克制其批评之声”。而一个业余知识分子,他不从属于任何上述机构,故能作为正直和勇敢之音来维护知识分子的传统作用,发出为职业知识分子所放弃的对那些有权有势的社会结构的批评之声。
世界知识分子的良心
萨义德自己从未为智囊团或政府部门工作。他认为,在那些地方,知识屈从于权势利益。他努力保持知识领域的自主权利,而不受政治霸权控制的干扰。他和他的多年朋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强烈抨击者。
晚年的萨义德,身体因病而越来越衰弱,不能再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便有较多时间听音乐、弹钢琴。他是音乐行家,曾多年为《国家》杂志撰写音乐评论专栏,自己也弹得一手好钢琴。病中,他重又想起了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可以成为和平的桥梁,可以把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感情和想象带往崭新的天地。
1999年,他在伦敦与钢琴家、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相见,叙谈甚欢。巴伦博伊姆生于阿根廷一个俄国犹太人家庭,后在以色列长大,在政治观点上与萨义德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业余”知识分子精英们所具有的宽阔胸怀以及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使他们成了亲密朋友。
他们俩一致认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将来有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可能,并决定一起组织音乐活动来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不久,巴伦博伊姆便在巴勒斯坦举行了钢琴独奏会。同年,他和萨义德在德国魏玛共同创办“东西方会合工作室”。这是一所学校,也是一个管弦乐团,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些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集合在一起学习和演出。柏林、芝加哥等交响乐团派去导师,马友友等名家去讲课,萨义德和巴伦博伊姆亲自主持了文化研讨会。这些来自中东不同地域的年轻人朝夕相处,从最初的彼此陌生、隔阂变得越来越和睦、亲近。
萨义德逝世一年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巴伦博伊姆在追思会上弹奏了舒伯特的一首即兴曲,并发表悼词说,萨义德自己就是个音乐家,他通过音乐来理解世界,人们常用音乐来逃避世界,但他知道,在音乐中一切都互相联系,不能像在其他领域中那样切割分化,而我们的世界也应该像音乐那样融洽和谐。
(摘自《美国知识分子: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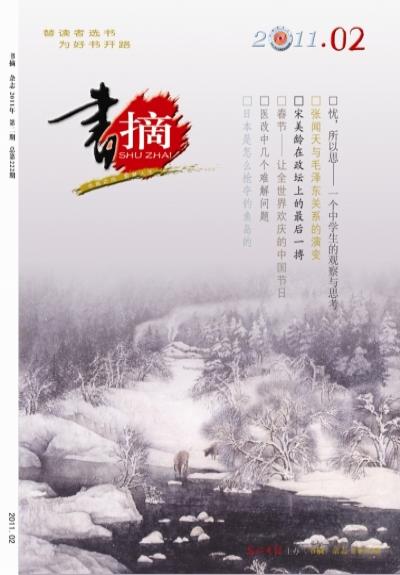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