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走进电影
我在江西农村插队,已经开始第九个年头,周围的知青几乎都走完了,最幸福的当数进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然后是病退回上海,最后是在当地招工进厂的。只有我,还留在村里;还在那里插秧种地。我穿着短短的蓝色平脚裤,大热天也不戴草帽,田间休息的时候,两腿的泥巴都懒得洗去,坐在装着秧苗的扁担上,和老乡用报纸卷着烟卷,在那里使劲地吸着。蹩脚的烟丝,怎么吸也吸不出个烟味。那时候,与其说是要在那里干革命、接受再教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如说我是带着浑身的怨气,要在那里发泄,一头一脑的愤青架势。
后来母亲来信说,父亲原先的老战友江渭清又出山了,就在我们江西当省委书记。于是拿着她写给江书记的信,书包里还装着一本书——那时候最时髦的内部刊物白皮书《白轮船》,搭乘着长途汽车去省城了。一脸的酷劲,谁都不搭理,但是心里的喜悦还是上下跳动着,我对自己说,见到江书记,就是我理想的“白轮船”起航了。
江书记在家,但是他没有出来见我;江夫人对我说,你在农村多好啊,空气新鲜,我们现在都怀念那时候下放的日子。七搭八搭地聊了一会儿,然后她又说,家里要开饭了,没有准备我的饭。她把母亲写的信留下,让我走了。我赶到长途车站时,当日最后一班回去的长途车开走了,蜷缩在车站的角落,我大哭一场。我和母亲的自作多情,让我尴尬地在车站里熬过了一夜。
年底的时候,“文革”后的第一场高考开始了。15岁就下乡,没上过什么学,数理化对我是天方夜谈;可是不考取大学,就再没有其他办法离开村子。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那时候艺术院校,只考作文、政治和专业。对电影,我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懂得多一些,因为母亲是俄语片的翻译,小时候在那里看着他们对口型配音,看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剪接;休息室里,似懂非懂地听大人在争论着电影的好坏;还有,在放映间捡回那些废胶片,我已经会学着那些老师傅,只要用舌头舔一舔,就能判断出胶片的正反面了。后来,我离开了农村,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电影,在我的生活里,成了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走进去以后,就不愿意随便和别人谈论他了。因为这似乎变得像是一个恋人,有了那么多感情以后,就想保住自己的隐私,因为有太多的微妙和细节影响了我的感觉、生活态度和对人的认识。
带着《上海伦巴》去看黄宗英
梧桐树抽嫩芽了,粉绿色的叶瓣涂抹在天际,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莫奈的油画,这时候真觉得上海有点巴黎的味道了。我带着《上海伦巴》去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阿姨,关于她和赵丹叔叔的爱情是这部电影里讲的故事。我知道宗英阿姨一定会说我的片子拍得很好,她是那种非常宽容的人,不论我们拍了什么,她总是先说好。而我真正希望的是,我的电影能给她带去快乐!
故事是在1996年,我无意中看到了《文汇电影时报》上写的关于她的文章,这让我激动了整整一夜。从小在她家里玩着长大,却不知道她的经历竟然是那么戏剧化。我飞到北京去看望她。我说,我能拍你和阿丹叔叔的电影吗?她说,可以啊。但是,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说话很累。于是在北京小西天她和冯亦代老先生的小屋里,我每天只能和她聊上两小时。我们东拉西扯,整整讲了一个星期,然后捧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回上海了。那时候,我跟宗英阿姨说,我还要她出现在我的影片里。她笑了,“让年轻的女演员去演吧,我老了……”说话之间,她还是那么漂亮,那么迷人。一头银发展现出她的风韵,特別奇怪的是,至今她脸上都没有什么皱纹。可是,没有想到,这一说就是8年过去了,手上写的本子就这么转来转去,到处找投资。一直赶上电影百年,我们才有机会完成了《上海伦巴》,但是宗英阿姨已经81岁了,她病了,真的不能出演影片了。
我买了正版DVD,慢慢地放给她看,她穿着病服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晚饭送来的时候,片子才放到一半,宗英阿姨对护工说,你把饭吃了,给我去买两个白馒头就可以了。说话的时候,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机,似乎怕漏掉了什么。我问宗英阿姨:“我们在摄影棚里搭的景,拍得像你们当初拍《乌鸦与麻雀》状态吗?”
她轻轻地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像!”
过了一会儿,她几乎是在自语地说着:“像,片场挺感动的,让我想起很多事情……”
她说得那么轻,可是那么深情,我几乎想哭。
阿劲,我大学同学,她的小儿子,努力把气氛挑得高兴一点,大声地说:“黄宗英同志,你觉得袁泉演得像你吗?”宗英阿姨真的笑了,“像,像!侧面最像……就是我那时候,自行车骑得快极了,还是28寸的男式大平车……”
阿劲又说:“黄宗英同志说像,那一定是像了。我们掌声鼓励!”
总之,我们想表达出自己全部的快乐,这之中包含着我们对老一代人全部的爱和敬仰!片子结束的时候,宗英阿姨问我:片子有多长?怎么就完了?
“107分钟。好看吗?”
“好看,恋爱谈得挺好的。有人写我和赵丹谈恋爱,两个人在那里对看着,然后,我们就开始念诗。啊呀,哪里有这样谈恋爱的。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吵吵闹闹,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啊,也和你们一样的……那时候,赵丹一接到一个角色,就穿起戏服,神经兮兮地生活在人物里。但是他不演戏的时候,出门总是穿得很讲究,很注重各种礼仪。”她暗示着我,不像我电影里表现出的阿丹穿得太随意了。
我知道,这就是老一代人的教养,他们特別酷,因为那是骨子里、是血里面的东西。那份气质,那份灵气、智慧和优雅,是我们永远会在那里追随和仰慕的……
最难忘的一部电影
第一次看《人与兽》这部苏联电影,是在我上小学一两年级的时候,学校放暑假了,母亲把我带到她工作的地方“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天是他们和陈叙一导演为影片的配音对口形,于是一小段片子就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停地放映。每一段几乎要放上十几遍才罢休。我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赶紧跑到后面的放映间,只看见是一小节片子挂在放映机上,就那么循环地放着,没有人向我解释。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故事,那里面的人就是在说着同样一句话,实在看不出个名堂,最后干脆倒在放映间脏兮兮的地板上睡着了。
一直到1978年我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才有机会完整地看了这部电影。在放电影之前,我激动地跟同学说,那是我母亲翻译的片子,小时候睡在放映间地板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呢!于是,早早地拿着小马扎,在学院食堂里面占好了位置……今天回想起来,电影里面讲了什么,已经完全记不住了。但是,我记得那份很抽象的情绪,我看得非常激动,对影片甚至充满了崇拜。但是,一直到最后译制人员的名单出来的时候,我瞪大了眼睛,也没有看见母亲的名字。这让坐在黑暗中的我,羞辱得无地自容,偏偏在这个时候,还有同学问我,“不是你妈妈翻译的片子吗?”我没有回答,不是因为生气,实在是没有脸面去发出声音,更是不知道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写信回去问母亲。
母亲很快就回信了,她说,我的记忆力一直就那么好。《人与兽》是她翻译的,因为父亲一直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她的名字是不能出现在译制人员的名单里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她说,她曾经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以及60年代中期翻译的西班牙的几部片子,大部分都没有她的署名。
母亲说这些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以后了。于是回想往事,就觉得事情并不像母亲说的那么简单,这让我想到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似乎生活变得就像《人与兽》里面的主题,人身上有着太多的兽性……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在我简单的下意识里面,我是本能地在忘却这个电影。回忆里面夹杂着太多的电影以外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起我最难忘的电影,我还是会想到《人与兽》——这部黑白片子只给我留下一个抽象的记忆,拍得非常非常漂亮;里面还有一个爱情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也记不清了;但是我坚信,那一定是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因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唉,这又是一个很抽象的情绪记忆,因为所有的这一切,依然和电影以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电影
当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伴随而来的是精神生活的丰富,可是一切都恰恰相反,人们变得浮躁起来,焦灼的情绪像一根鞭子,抽着生活不断地旋转,像陀螺似的,转到什么地方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能停顿。于是,大家在一起谈电影、做电影的时候,忙的都是电影以外的事情:找钱、包装、炒作、得奖、成名、宣传、销售等等。至于电影的品质、内容、电影语言、演员的表演、还有故事本身都留到最后被谈论,甚至不再谈论。
不论是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家都在抱怨,说是电影越来越不好看了,还是过去的老片子有意思。但是,好莱坞的电影销售手段却依然越来越被市场接受,人们一边抱怨着一边学习着,一边在最后遗忘电影本身。大家还在做电影,可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跟电影最本质的事有关系了。很少还有人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思考着电影。当朋友邀请我们去看他们完成的影片时,我们常常坐在最后一排,在工作人员的字幕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借着黑暗,偷偷地溜出电影院。因为,大家实在都害怕面对面地说真话,而那些善意的、好听的话,已经让我们说累了。电影本身早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于是真话也失去了它固有的价值。
赶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冯棱棱从美国来了,她原是录音系的同学,可是去了美国改学了电脑,现在又开始做生意。她说,带我去电影节看看电影吧!我说,那么贵的电影票,你不如回美国去看呢。
电影节,我们没有看电影,我们去看同学。霍建起来了,他得了那么多的奖,但是冯棱棱大概什么都不知道,我想,她不仅是不知道,霍建起的电影她一定都没有看过。这根本不重要,我们是去看同学的。当我敲着霍建起的房门时,冯棱棱按住我的肩膀,像孩子一样躲在我的身后说:“不要让他看见,给他一个惊讶!”果然像冯棱棱说的那样,她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叫了起来,屋里还有美术系的周欣人。现在,美术系的同学几乎都当上了导演,只有周欣人依然在干着本行,只是偶然客串一下,或者说是玩票一下,当个电视剧的导演。于是,在他干美工的时候,我们叫他“大师”,平时我们叫他“周导演”。
见面了,大家说着以往大学里的故事,同一个故事每个人都会说出不同的版本。于是,我们一起大笑着。这是我们电影学院版的《罗生门》。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找了一家没人的小店,没有什么可点的,于是一起混着吃了小馄饨、青菜炒饭、锅贴还有一碗粉丝汤,四个人凑着一张小桌子。那个感觉就像在电影学院的食堂里,我们继续说着往事,大家继续笑得稀里哗啦,我们什么都谈,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苦恼,自己的孩子和家庭,朋友的故事,但是惟独没有谈的就是电影。冯棱棱有点伤心地说:“我现在是离开电影最远的人。”
没有人接她的话,其实,我们离开电影不远吗?
当我们不再贴着电影很近的时候,这份间离让我看见了问题也看见了真诚。那份真诚是留在沉默之中的,很多时候,最渴望的东西是不喜欢大声说出来的,你会在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面壁而思。只有那个时候,一切才是最真实的,只有在那个时候,你不用再跟自己演戏,你不用再跟自己说假话。那个时候,你问自己,电影是什么?那个答案是最准确的。
(摘自《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7月版,定价:1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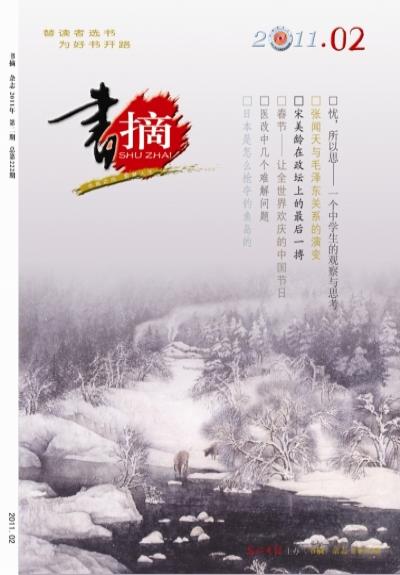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