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医改草案
2008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而与农村、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改革相比,医疗卫生落后得太多。和亿万人切身利益相关的“新医改”方案,近年来曾几度“呼之欲出”,卫生部、发改委的领导一再表态,可多数没了下文。终于,在11月初,黄叶纷纷飘落的季节,姗姗来迟的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和公众见面了,并通过网上征求意见。
医改成为全国公众热议的话题已有数年了,至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时,达到了鼎沸。国家发改委网站9天中就征集到了1688条意见和建议。肯定、迷惑、建言、批评,如潮水般涌来。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消息称,“总体上反应良好”。但许多人认为,这与民间的舆情、社会真实的反响,有相当大的差距,令人无法释怀。
几天后,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并在黄金时间播出。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说了一句话,至今使人记忆犹新,即医改方案“看不懂”,“都是中国字,连在一起却没太读懂”。
对于医改征求意见稿,白岩松可能读懂了,也可能真的没太看懂。征求意见稿几万言的长文,内容很多,看似面面俱到,而有的又如云里雾里,有“疑似埋伏”存在。作为“非专业人士”,白岩松对这些也似有所察。
针对一些公众称“看不懂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的问题,一位据说参与了方案起草的官员发表谈话,说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他称,“作为医疗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看不懂并不构成问题,随着医改方案的相关配套文件出台,老百姓可以从切身利益的变化中理解这次医疗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
与此同时,一直关注和参与医疗改革讨论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澜教授,也认同“看不懂正常”的说法。他称:因为普通老百姓缺乏专业知识,他们的意见一般只是给公共决策提供方向性的选择。他表示,这次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前期邀请相关研究机构和其他一些单位提出不同方案,现在又公开向民众征求意见,从民主化方面,在中国重大改革方案中做得已经相当好了。
乍一听,这出自官员+教授“黄金组合”的解释似乎有理,令人晕眩。但对老百姓看不懂“非常正常”说法的附和,总难免带有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轻慢。作为官员或学者,其实这是最要不得的。既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毫无疑问,原本是希望老百姓能读懂的。而且白岩松也不是一般的百姓,如果连他都“读不懂”,不该问问为什么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是博导,北大医改方案的起草者,医改方面的顶级专家。他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得出了与普通公众并无二致的看法。对于白岩松直言不讳地对方案作出“专、绕、涩、大、空”的四字评价,他表示赞同。他亦不讳言自己虽是专家,“我看得懂,但是费了点力气”。
医改关系到千万人的切身利益,本来是应该让人看明白的,诸多改革措施应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遗憾的是,为什么偏偏会让人看不懂?
医疗卫生与其他服务行业一样,从来都不是卫生清洁的净土。有读者认为,这不单是文风表述上的问题,也不单是多个方案如何有序互补的理论构建问题,而根源在于医疗卫生体制长期以来矛盾、混乱与痉挛着的“老病灶”本身。
在中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时,总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部门或团体的利益,如同巨大的引力场,使指针发生摇摆和偏差。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伦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美国资深的保险精算师,曾任美国国家总精算师,担任过美国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三位总统社会保险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金改革等方面的政策顾问。曾被评为1991年美国卫生医疗界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他也是蜚声国际的台湾地区保健制度的最初设计者。他生于北京,幼年即随家人赴美。虽然已年逾花甲,近年来多次回国探亲或讲学,往返于美国和中国西部,想“实现一个探索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改革路径的梦”。他反复强调“医德与伦理的重要性”。萧庆伦教授认为,医改的当务之急,是改变医院和医生的追求。他忧心忡忡地说,“大约二十年前,中国把公立医院改成了一个私人营利的单位,追求金钱,而且没有股东,这些钱被医院和医生分了。他们的生活好了,但他们也变成了一个强而大的利益团体。所以,这次改革很难真正动这些既得利益团体。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可是,在这个政治环境下,因为每个强大的既得利益团体都在政治上有他的力量,所以很难出台一个明确的政策。”
真是一针见血,直中要害。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今天的各项改革,已经进入相当理性与成熟的阶段,似乎只有医改例外,歧路彷徨。不绝于耳的,是病痛者呻吟号哭甚至咒骂,广大医务人员勤勤恳恳工作,也因此蒙受了许多委屈责难。
“看不懂”,这三个字有沉甸甸的分量——在模糊不辨中,就很难满怀信心地把目光引向未来。
有没有“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医改需要有一种清晰的指向,即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很好,完美无缺,则医改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像是否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其实认识就很不一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力意味着获得医疗服务的自由。比如有一位留洋归来的中科院院士,在好多地方作报告说,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医疗服务费用很低。他举例说,做一个盲肠炎手术费300元,等等。此人就是广东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曾益新院长,在新医改方案出台半年多后的2009年10月底,还在电视节目中信誓旦旦地说:“现在大家都抱怨医院黑、价格高。但是医院收费的绝对价格不高,甚至是偏低。现在医院的条件都很好,中央空调、电视、网络、电话一应俱全。两人间的病房只需72元,附近连宾馆都找不到这样的房间,100片止痛片才1.69元,生理盐水的价格比外面的饮料还便宜……所以,医院的绝对价格真的不高,大家比较一下就明白。”
他说得很坦诚,而且句句都不假,但多是一地鸡毛。
曾院士是声名远播的研究医改的专家,还是肿瘤专家,应该懂得,治疗肿瘤光用不贵的生理盐水和止痛片行吗?住院他偏偏跟住宾馆比。医院病房里的空调、电话、网络,哪一样不要外加收费的?曾院士的医院,每个病人住一次院,要预缴多少钱?平均费用是多少?1万、2万还是5万元?
一个人做学问的第一要义,是学会理解底层,学会和普通的百姓对话,了解民间大众的疾苦。人应该讲求良知和人道。
曾益新在“广东论坛”上为“医院讨公道”的同一天,报载,江苏兴化市的一个吴老汉,一年前摔断了腿骨,在医院动手术打上了钢板。2009年9月,骨头长好了,医生建议他取出钢板。吴老汉舍不得花钱,坚持回家,找到菜刀、螺丝刀、酒精,瞒着家人,试图自行取出钢板。由于没有麻醉,菜刀又不锋利,老汉忍受着剧痛,费了很大功夫,也没有能卸下螺丝,伤口处血流如注,情形极为悲惨。后幸亏被家人发现并送去抢救,才保住了生命。
网友讥讽说,这老汉真傻,怎么不看报,没有看到昨天专家又在鼓吹了,中国看病不难也不贵。这是中科院(应为中山大学)“医改”咨询项目负责人、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说的。又一位网友说,还是得去医院挨三刀:精神上一刀,肉体上一刀,金钱上一刀!
显然不是智商问题。不同阶层的人,境遇迥异,收入悬殊,享受的医疗保健待遇不同,思想与情感并不相通。如果一个行业与职业的高层普遍与社会格格不入,与道德价值指向背道而驰,其体制与机制本身就应该受到质疑。
还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群众对看病的要求高了,超前医疗消费。在地方、在小医院看病并不难。难的是都盲目跑到大城市,都要到大医院找名医看病。
貌似有理,实则大谬。据我所知,农民到县城医院看病已经不易了。既然到大城市来求医,必定在当地看不好病。否则怎么会每年几千万人,凑起钱款,甚至倾家荡产,千里迢迢,坐火车汽车,送亲人到北京、上海来求医?奇怪的是,这些论点竟一再被某些官员所引用,好像看病难,只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对过高医疗消费追求所引起的假象。
记得1985年5月,我参加南极首次考察队归来。“向阳红10号”考察船在吴淞口靠岸,我走下船桥,突然看到了欢迎人群中的父亲与妹妹,眼里满是泪水。我感到奇怪,怎么他们也来了。原来,母亲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癌症,病危。父亲的学生是上海华山医院的科主任,打了电话,他叫母亲来上海,他再诊断一下。母亲是一周前到上海住院的。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立即赶往医院。
即使有人帮助,外地人看病也不易。母亲躺在走廊临时加设的病床上,脸色苍白。不一会,主任来了。他说,今天钟老师的体温已经下来了,问题会水落石出。他初步诊断是肺炎,当地医院是误诊,按癌症用药,治了一个月,便进入了病危。
当晚,我没有随考察队回北京,和父亲挤在朋友家陋室的地铺上,没有了大海波涛的摇晃,反而怎么也睡不着了。父亲说,没有学生帮忙,你这次可能就见不到母亲了,家里连坟地都买了。当教师的母亲还有公费医疗,两个多月的折腾,身心俱伤。如果是农民,怕早没法好活了。
至此一回,对家庭来说,已是大难。有这样一次求医的经历,对一个人已经足够。
“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
与邓小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著名论点“不争论”相反,专家、不同部门负责人、不同群体,对医改方案的意见建议一直不断。在高层论坛、学习研讨会上,代表各自行业部门人群的专家教授官员纷纷登台,按照各自的体会解读新医改方案。同一个表述,可以作出N种解读,N个诠释,彼此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原以为一些混沌不清的理念和思路,会越辩越明。谁知或隔山叫阵,或顾左右而言他,对一般百姓来说,有一些本来清晰的问题,反而被理论空谈弄得云里雾里,摸不着边际。特别是一些貌似激进的后退,形似改革的权力寻租,能量颇大,不动声色地把公共卫生公益性的坚持,引向对医疗服务既得利益的固守。如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问题。本来这两者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但这种理念理论的“裂隙”,让你看到了最难解的深层矛盾与利益纠葛。
有人把各国的医改归结成为两大基本思路:一、靠政府,二、靠市场。这纯粹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中国式思路。认为“靠政府”使医疗投入缺口不断变大;“靠市场”,则使小企业员工、个体经营者、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买不起私人保险,也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保险。
总之,所有这类信息相当混乱相当矛盾,都向人们描绘了医改这个难题全世界无解,各国比中国看病还要难、还要贵的消极图景。
一篇综合报道的题目是《欧美“医改”,各家都有难念的经》:“近日,中国卫生部正式公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意味着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新医疗改革向前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事实上,不光中国和美国,无论是号称‘高福利天堂’的北欧,还是我们的近邻东京,医疗保险体系也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
发达国家尚且没有解决,我们解决不好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其实各国在医疗卫生体制和制度的设计上,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比如,全世界的医院和诊所,除急诊和住院的外,没有一个兼卖药,没有一个国家以药养医。还有在医院管理体制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医院的(朝鲜、古巴除外)。如果我们能认真观察、研究各国的不同医疗卫生体制,定会发现人家很多长处,有所启迪和获益。
本来,政府与市场没有矛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早已确定坚定不移的方向,怎么在医改中生出这么多的歧义?
有一些专家所谓的“政府主导”,模糊了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行政监管,与政府直接举办、财政对卫生医疗服务全包的区别。“政府主导”论强调公立医院(几乎所有医疗服务)“回归”公益,再给政府戴一顶主导的“高帽”,要求财政——全国纳税人的钱——包下公立医院日常运营,把农村和城市基层医疗机构“打造”成“公共品”,再承担医生的工资等全部费用,并且有“一个稳定的较高收入”,同时,与他们的服务项目、服务质量无关。这即是专家们的理论——“补供方”。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中国公立医院数量、规模、卫生资源占全国的95%以上,政府很难都养得起,都办得好。不仅现阶段如此,而且将来恐怕也很难。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公立医院一般只占50%,且多数标准并不高。
而论及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涉及卫生行业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涉及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等相关性问题,“政府主导派”则语焉不详,或刻意回避。 虽然“政府主导派”也直指——“医疗机构与药品营销的经济利益联系、医生处方与其个人收入的经济利益联系,都是导致医生开大处方和高价药、甚至收受药品回扣的重要诱因。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不仅加深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其中的利益分割还加大了医改往前推进的难度。近几年来,药品收入依然占到了卫生部门综合医院收入构成的40%以上”,但又认为一切根源,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而市场化又是“国家财政对卫生投入严重不足”造成的。
“政府主导”派在转了一圈,痛批政府之后,提出了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要么财政养医,要么放手让公立医院高收费、乱收费的现状继续下去。这种似乎理直气壮的发难,在三十年改革的巨变中,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事实上,多数公立医院,特别是县和县以上的综合性医院,都是盈利的。几乎所有三甲医院每年总收入都有数亿元,甚至十几亿元。“非营利”医院实际上多数是营利的。
赚钱的医院多数乐于维持现状:既有财政拨款,又有大量医疗服务和卖药的稳定收益。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说了大实话:扣除医院日常运营费用后,收益率可达8%~10%,如果一家医院年经营额为5亿元,净收入可达4000~5000万元。即使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往往也望尘莫及。如我国最大的药品流通企业国药集团,药品销售的利润率只有千分之几,几百亿的产值,年利润不及一家大一些的医院。这样想来,公立医院千方百计想戴的“公益性”帽子,委实有点小了。
比较麻烦的是不良的医疗卫生资产。不少公立小医院、街道乡镇医院,处境艰窘,成为卫生部门的包袱。现在,正好统统打包,组织进社区或农村医疗系统。在现行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由政府来举办,接过这个包袱,那就功德圆满了。
在主导与主办没有厘清的情况下,过分强调政府主导是危险的,极易把行政监管、服务型政府,混同成“包办型”政府,赋予某些政府行政部门极大的权力。比如医疗机构支出的审定权,运营经费的下拨权,医院管理层的任命权,医疗服务和药品的定价权,基本药物生产的定点权,药物以及耗材和设备的集中采购权、配送权以及政府直接组织的药品招标采购等商业活动。如果这样,权力寻租将不可避免,以这样为原则进行改革,很有可能毁掉一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官员。深圳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发生的腐败窝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北大医改方案的起草者刘国恩教授,其观点则倾向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公立医院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应在产品的供给上鼓励市场化的竞争,促进效率和让价格回归理性。财政补贴的方向应是补给患者,即实施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提高患者的购买力。他认为,提倡把财政卫生经费补向公立医院,只会导致低效率和腐败。“补需方其实也是间接的补供方。补到患者手中,即赋权予老百姓,患者通过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谈判,谁提供的产品好、价格低、服务好,就购买谁的,同时还拥有监督权。这些费用最终也是流回到供方手中。”与此同时,补需方的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管办分离”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卫生部门并不愿意管办分离”。
在今天的社会中,垄断和缺乏有效监管的公立、公办、国控等等看似健康的肌体,往往是最容易被“商业的手段”攻破的。在改革初期有一句常说的话“不找市长找市场”。反过来,找不到市场就去找市长。想想这些年来因腐败频频落马的市长们,还不够令人深思吗?现在,药品销售上,“药虫子”、医药代表们,同样不找市场,而专找院长找医生,依旧依旧,究竟谁肥谁瘦?
(摘自《大国医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1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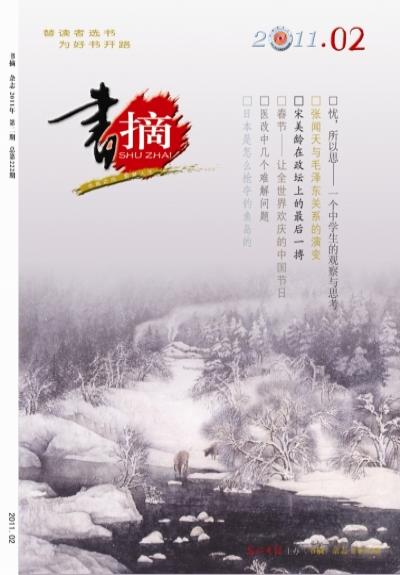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