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5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留校任助教,后于1958年3月因1957年政治问题离校,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工作,至今正好四十年。这四十年间,无论社会与个人,都有极大的变化,但我对母校的感情,却始终如一,而且是愈久弥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工作关系,与北大一些系、一些教师,接触渐多,有时每周都来,有时还住上好几天,似乎又成为北大的人。我于l95l—1952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念一年级(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编者注),深感清华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学风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与贡献。1995年为清华中文系建系七十周年,我应邀在《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上写了一篇题为《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的文章,把清华的学风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是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细小局部,能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来把握所研究的课题;二是能着眼于当前的现实,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而又能沟通古今;三是对中华的历史和文化有强烈深沉的爱,而在清理传统时总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1997年春,我为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尚君教授《唐代文学丛考》一书写序,谈到复旦的学风,说:“复旦的学风确使人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与严格的学术准则之感。”(这篇序文在《复旦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刊出)我也曾谈到过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在程千帆先生倡导下所形成的治学格局:“南京大学中文系和古典文献研究所近十年来养成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学风,就我个人的体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在文学的审美研究中加强现代科学思维训练的学术品格”(《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序》);“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与(周)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序》)。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引录这些文字,是因为我觉得上面所说的这几方面治学风尚,北大是可以兼而有之的。北大自从蔡元培任校长时倡导兼容并包以来,一直有一种大而广的气度,依我的私见,这大而广确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学风。《诗经·鲁颂·泮水》郑笺有云:“大,犹广也。”《庄子·秋水》篇云:“至大无外,谓之大一。”晋郭象注更进一步明确大的含义:“囊括无外,谓之大也。”这就是说,大,可以囊括一切,不见外,不拒异。这也就是能有气度地继承、吸取前人和现有的一切成果,形成完整的体系,即所谓“集大成”,如《孟子·万章》篇所说的:“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这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大具”。“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荀子·正论》)我这里引录的虽然都是古代言论,但这些哲人对于有关大的概念的演绎,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北大的学风,仍有参考意义。我自己觉得,我在北大上学的三年,工作的三年,得益于这种“大”的学术风尚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努力追求的治学与待人的品格。具体到上世纪50年代的中文系来说,更可使人有这样一种亲切感受。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合并,文理两科集中于北大,工科集中于清华。这对于北大中文系来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人才荟萃。当时从清华过来的教师,有吴组缃、浦江清、王瑶、朱德熙、冯钟芸、郭良夫等先生,从燕大过来的有高名凯、林庚、林焘等先生,北大中文系留下的则更多,如杨晦、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杨伯峻、川岛、吴小如等先生。不久,又从广州中山大学过来几位语言学教授,如王力、岑麟祥、袁家骅等。中文系的几门学科,如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文艺理论、写作,都有国内第一流的名家执教。就我个人所上的课来说,中国文学史,第一阶段是游国恩先生教先秦两汉,第二阶段是林庚先生教魏晋南北朝隋唐,第三阶段是浦江清先生教宋元明清,第四阶段是王瑶先生教“五四”至1949年。每一阶段为一学年,每周六节课。这样厚实的基础课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几位先生对中国文学史都能前后贯通。游先生当然是楚辞研究权威,但他对陶渊明、黄庭坚,特别是对清代戏曲家洪昇,都有很深的研究。林庚先生则对楚辞、屈原也有独到的看法,有几本专著问世。浦先生关于屈原生卒年的考证在建国之初可以说举世瞩目,他的《八仙考》、《花芯夫人宫词考》,都是脍炙人口的名文。王瑶先生关于中古文学的三部专著,可以说是继鲁迅“药与酒”一文之后研究魏晋南北朝士人与文风的最佳之作。因此,我们当时听这几位老师的课,都像进入一座座深邃的殿堂,使自己整个身心都受到德业的熏陶。很可惜,这样的一种学术气氛,在1957、1958年,受到极大的冲击。1958年初,我们几个刚处于学术上升时期的年轻助教、研究生,如乐黛云、金开诚、谭令仰、褚斌杰、裴斐、刘群和我,说是1957年4、5月间办同人刊物(实际未办成),属“反党”性质,划为“右派”集团,有的去劳动,有的贬至外单位。我与褚斌杰先后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我记得我于1958年3月离开北大前,杨晦先生特地要我到他家里坐一坐,吴组缃先生邀我到他家去吃一顿饭,算是饯别,由此也可见北大前辈学者那种不同寻常的宽宏的气度。那时我确实不期而然地涌出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的亲切之情。我于1958年秋到中华书局,到现在已将近四十年。先是做一般的古籍编辑工作,“四人帮”粉碎后,政治问题得到改正,环境逐步有所改善。70年代后期曾任编辑室主任,80年代初为副总编,l991年任中华书局总编。1992年匡亚明同志受国务院之命,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匡老因长期居住于南京大学,故要我做古籍小组秘书长,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这些年来工作的担子确实比过去重,我个人的科研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我始终把自己看成北大一名普通的学子,在中华书局将近四十年工作期间,努力为北大的文史哲科研项目,在出版方面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50年代后期,中华书局重印了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撰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接着又与教研室联系,继续编辑、出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这部稿子由我负责审稿,当时我真是日以继夜地做,一条条的注释都查原书,倒也发现不少问题,书稿边上贴满了纸条。北大中文系负责具体注释工作的主要是陈贻焮、倪其心两位,他们看了我的意见,不但不怪我挑毛病,而且一条条认真核实。这是我离开北大以后与中文系进行的第一次学术合作,彼此都很愉快,往后大家在一起,不时引为佳话。80年代以后,工作交流就更多。80年代初,由金开诚先生组织,把游国恩先生生前已着手但未完成的《楚辞注疏长编》,交中华书局出版了《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二书。后来,我们又建议把游先生有关楚辞及其他古典文学的论著集中编成一书,经过几年努力,于80年代后期出版了《游国恩学术论文集》。朱德熙先生去世后,北大中文系拟编集朱先生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论文,但顾虑在出版方面可能有困难。中华书局编辑李解民同志受裘锡圭先生之托来与我谈,我当时一口答应。后来这部书出版时,朱师母的序与裘锡圭、李家浩先生的跋都提到了我,表示感谢,我读了后心头感到一热,油然产生一种报答师辈的自我安慰心情。80年代中期起,我参加了高校古委会的重点项目——《全宋诗》的编纂,与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合作。我作为主编之一,开始时每周来一次,有时在审稿阶段,在北大一连住几天。碰上中华书局工作忙,我就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到北大来看稿。开始时条件较差,一间很小的房子,坐五六个人,进进出出都须十分小心,怕碰着别人桌子,把书稿搞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部《全宋诗》在1998年全部出版。但我还是感到惭愧,由于我本职工作忙,未能在这部大书的修纂上多付出精力。不过这些年来我与古文献所的几位老师,特别是与好几位刚毕业的年轻研究生,一起含辛茹苦地翻书查书,阅稿改稿,他(她)们那种学术上的真诚奉献精神,我是始终不能忘怀的。这里我想再说说中文系林庚、陈贻焮两位先生与我的学术交往。我在五六十年代重点研究宋代文学,70年代中期起改治唐代文学,因此与林庚先生接触较多,林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奖掖,我一直铭记在心。197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编的《唐诗选》中某些不确切的注释提出批评,此文刊于《文学评论丛刊》。后我把此书寄给林庚先生,林先生于1979年l2月2日给我一信,中说:“《文学评论丛刊》收到,奉读大作,功力甚勤,至为钦佩!北大唐诗中心,因百废待举,课堂为先,一时无力集中,系中仍不忘此事,当待一二年内,教学上基本稳定,再正式展开,届时望共襄盛举,同骋齐足,乐何如之。”1980年初,我的第一部唐代文学专著《唐代诗人丛考》出版,4月间给林先生寄去,林先生马上回信:“十多年来混乱局面,耽误了一代成就,兄能成此巨帙,足见功力之勤,承赐以先睹为快,尤感厚意也。”信中再一次提到中文系应加强古典文学研究,希望我“来此共图盛举”。80年代初,由我与几位同志发起,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一套别具一格的学术随笔,名曰《学林漫录》。林庚先生十分支持这套书,还特地推荐了他的研究生钟元凯同志《李贺诗歌的艺术美》一文,在1981年11月18日给我的信中说:“该文于艺术分析上颇有见地。元凯同志研究生已经毕业,现留北大中文系任教,治学甚勤奋,该文如可用,望早日为之刊载,是所至盼。”过几天,11月22日,又来一信,说:“21日手书敬悉为谢!该文校样请挂号即寄舍间,由我转去更为稳妥。元凯同志宿舍即在我南墙外数米,楼中却无收发处,平时信件都通过系里,不如我直截了当也。”《李贺》一文即刊于《学林漫录》第5集(1982.4)。元凯同志后离开北大,现任苏州铁道师院院长。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先生对后辈的深切关注,连文章的校样也可由他送交,可以看出我上面说过的北大学风宽容谦和的一面。陈贻焮先生,我们都称他“大师兄”。他于1953年毕业,留校做林庚先生助教,1953—1954年间与我们一起听林先生的课。他于70年代末即专心撰写《杜甫评传》。他在1980年7月给我一信,专门用毛笔写录一首长诗,首云:“近被杜诗恼不彻,悔攀高驾作遨游。少陵二十青鞋布袜适吴越,我过五十夹镜载笔陟降藏书楼。”颇有风趣。同年7月,他又写了一大张纸,有好几首诗,其中一首云:“感激言诗或起予,羡君学富五车书。帝王怎敌诗人贵,千载犹劳注起居。”诗末注云:“读《唐代诗人丛考》赠璇琮兄。”第二年,《杜甫评传》上册写就,约四十万字,他与我联系,提出两点,一是要我写序,二是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写序事我曾辞谢,我说我是学弟,资历浅,不宜为序,以请师辈作序为好。但他还是坚持要我写,我只好从命。他于1981年5月给我一信,中谓:“上午拜诵大札,承过奖,感愧兼之。拙著谬误实多,敬请郢政,苟不累清誉,渴望赐序,幸勿以浅薄见弃也。”关于出版的事,他希望早日印出,中华方面有难处,后来只好转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结果出了三大册,洋洋大观。我在序中说:“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解。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贻焮先生的治学特色正是如此,这也体现了北大那种“人能正静……乃能载大圜而履大方”(《墨子·内业》)的学术气度。我与北大老师,除中文系外,如邓广铭、宿白、侯仁之、张岱年、朱伯、田余庆、楼宇烈等先生,都有学术和文字交往,从中多受教益,限于篇幅,只好以后再谈了。
(摘自《我们的学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5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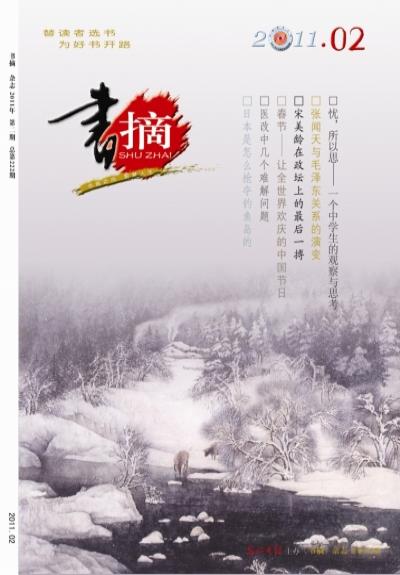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