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词在汉语里倒也古已有之。《书》曰:“革殷受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于人”。但此词在汉语中虽然古老,地位实在可怜,偏僻得近乎无用,而甲午战后却突然崛起,一跃而为声名最显赫、使用率最高的汉语词汇。这样一个“语词变迁史”,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思想变迁史和文化变迁史。更重要的是,它的古典的本意如梁启超言,仅指“王朝易姓”,不具现代的含意,现在所用的“革命”一词,是由日本人译于西方,而后被我们从日文中拿了来的,但这引入,岂止是再造了一个词汇,分明也再造了一种思维方式,而它在破坏中国传统上的威力较诸曾令国人失魂落魄的电线、铁路之类,不知强过多少倍。
梁启超的《释革》(1902年)一文这样解说“革命”的含意:“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 “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可乎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这个“革命”的意识,既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意识,也非惑于激情、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念,而是在时势的推动下中国人对自己历史和未来的“大彻大悟”——许许多多的论者,在谈论他们的这一思想转变时,用了“觉悟”“觉醒”等词,以表明有一种裂变发生在他们灵魂深处,同时他们也认为和期待着中国将踏上这条“觉悟”“觉醒”之路。
不管“革命”一词后来在不同党派口中被赋予了何种特定甚至尖锐对立的意义,其实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革命”这个词本身,对于20世纪中国乃是一个超越党派、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主题,或者说,是20世纪全中国的一种共同“宗教信仰”。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团体或不同社会领域的人们,“革命”目标可以不同,但对“革命”的主张和信仰则同样坚定坚决——国共互骂对方“反革命”,而都以“革命者”自居,革命党人斥立宪派“反动”,立宪派也绝不能赞同,梁启超鼓吹“革命”的文章岂非现成的有力凭证……
所以,20世纪中国不存在要不要“革命”的分歧,而只有怎样“革命”之争;唯“革命”马首是瞻是海内如一的,政治要“革命”、文化要“革命”、文学要“革命”,无事不在“革命”之列,整个现代中国便是吃“革命”的奶长大的。
将现代中国之历史视为一部革命史,不单单是指它的内容,尤其指它的精神。因为,20世纪中国埋葬君主制、实行共和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固然是历史巨变,但若从根子上看,引“革命”思维入文化、以“革命”思维为历史哲学基础并指导一切实践,才是对中国自身传统的彻底决裂和反叛。
一个重大的原因可能在于,中西文明的反差过于巨大,看取事物的方式几乎分处两端;而这两种文明一经碰撞,尤其是在一强一弱、一成一败的完全不平等的情形下碰撞,不单弱败一方必然不禁一击,而且很自然地会让人在这两者间产生一种非此即彼的因果的判断,比如说,将彼文化之成因解释为此文化之败因,虽然这在逻辑上的可疑明显之极,但来自眼前的现实的错觉转移了人们对其判断的逻辑性的注意。不管怎么说,20世纪初,中国人显然普遍相信中国落败或停滞不前的原因,正在于我们文化中缺乏一种革命性思维,反过来说,对它的根本改革,必须是灌注、培育和激扬革命性思维——凡事皆以革命性思维待之,“革命”乃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褒义词——这样的认识,直到当下依然指导着我们的各项实践。
久而久之,“革命”已成一种绝对理念——一切思想和行为,无论本身内容究竟如何,只要是新的和反叛的,便具有“进步”或“先进”的意义。如果从背后来看,又会看见一种泛恐惧心理的存在,即无时无地不在的对“革命”中断或停滞抱有恐惧或失落之感,为“革命”而“革命”,“革命”被当成永恒的目标,步伐必须一浪高过一浪,一旦有放缓的迹象就会引起历史认知乃至个人道德上的严重不安——解读作为现代中国一个缩影的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我们便强烈感受到“革命焦虑”的作用,他心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几乎成为永恒,以致不能想象事物发展可以采取“革命”以外的方式。
20世纪中国文学不单自身被革命思维所支配,而且它实际上也是这种思维的主要滥觞之一。每个重要的文学阶段,都有革命的意愿发生,都被革命的意志驱动。革命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润滑剂,也是这架机器的运转原理。整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分出“古典”与“现代”的疆界来,这实在要算一座分水岭。
或者说,什么是“古典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我们若从其他方面寻找依据往往还不甚明朗,但只要抓住“革命”这条线索,则分野立明。盖古典文学虽然也有讲“一代而有一代之文学”、“不蹈袭”、“勿拾前人语唾”者,却只是对差异的认可,而并不以否定、超越前代为旨归;古典文学思想体系之中既缺乏“革命”内核,其实践也从不谋求在“革命”模式中向前发展。
从孔子起两千多年的古典文学史上甚至连一次革命性事件也不曾发生,骚赋、近体诗、长短句以及戏曲小说,每个重要演进只是文体间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自然嬗替。反观现代文学,则一如冰炭——没有哪一个重要演进,不是文学家以其理念人为地以“革命”方式强加推进的结果,如新诗,如“两结合创作方法”,如先锋小说……尤为紧要的是,每一种新文学现象的登场,都以宣告旧有文学的“死去”(或者“腐朽”,或者“反动”等等)来开道,以排拒别种文学来给自己正名。
在上述被改变和易换的文学史运作模式中,以革命面目登场的“五四”新文学具有一种内在的宿命,即它注定要被新的革命所终结所替代,而这样的结局与其说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否定,毋如说是其最后被完成的仪式。其实,当上世纪2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生力量起来宣告“五四”新文学死掉时,某种意义上,这一行为是对“五四”新文学衣钵的真正继承——它为“五四”新文学的肉身送终,却在精神上传承了它的生命。
这说法看上去似乎是文学式的象喻,其实却是极为具体的现实;“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天狗》这几句直抒,呈现了郭沫若胸中“抉心自食”的冲动,而这冲动于每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知识精英是基本的、共通的,人们普遍渴望以自我一次次毁灭来脱胎换骨。
革命,革命,没有毁灭如何革命?毁灭是必要的牺牲,也是为更高历史目标应该主动追求的命运;当某种事物行将死去的时候,人们就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和曙光。所以,“无产阶级文学”等将“五四”新文学及其代表性作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送上新时代的祭台时,既没有半点犹豫,也不曾觉得失诸轻躁残忍,他们心中只被革命的豪情所鼓荡,以为这对于历史非但不是什么损失,相反倒更是一种胜利和进步。实际上岂独“无产阶级文学”之于“五四”新文学如此,先前和此后一切急忙忙出来宣布某某时代某某文学“过时”“落伍”“死掉”的人及言论,哪个不是这样?而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文学推进方式,直到20世纪结尾也还没有消失——1998年新生代作家集体策划的“《断裂》问卷”事件,我们也还记忆犹新。
察识了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内在逻辑,则“五四”新文学仅仅十年便被“废黜”一事,我们便不表吃惊了。它是不是来得太快一些呢?一点也不。其实否定“五四”新文学、对它感到不耐的情绪,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便露了端倪,待到完全形成主导性舆论已迟了四五年,可见革命的步伐并不很快。就这件事本身而言,真正值得重视的,恐怕倒不是“五四”新文学的命运问题,而是它显示的现代文学史的那种特有的张力;这种张力解释了一切,既包括“五四”新文学的命运,也包括30年代“左联”的崛起,直至延安时期超级文学的最后形成。
(摘自《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4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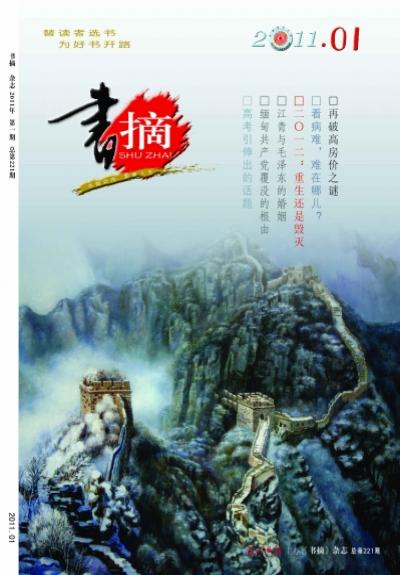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