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改革开放始于1977年。
1977年恢复高考,城市大门开始向农村青年敞开,这对所有农村学生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那年,我们村里的高中考了三个大学生,其中,我们同一个生产队的刘家荣考上了西安交大。这事被乡亲们翻来覆去说得有些神了。有的说,他在家已经研究出原子弹了,还画了草图;还有的说,他日后至少是政治局副主席。反正,学生们学习的劲头一下子被刺激起来了。
初一的时候,母亲念我岁数单薄,老受大孩子欺负,硬是让我留了一级。果然,留下的这个班学习风气浓厚,而且不搞阶级斗争。这真要感谢母亲的英明决定。留级还给我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一年后,从我们那一年的初二开始,县城重点中学一中、二中的高中部面向全县招生。当然,要在县城参加统一考试。学校组织我们村同一年级的五个人去考试,结果全部考中。这样一来,我就到了全县最好的中学,当时大概也是全省最好的中学之一,靖远一中。我被分到高一一班,重点班。
我到靖远一中是1979年。那时的一中,五湖四海,名师荟萃,集一时之盛。物理老师任家浩、谈复华夫妇是浙江人,数学老师李明田是河南人,地理老师刘毓峰是山东人,历史老师彭世荣是广东人,语文老师是天水甘谷县人张克让。当年给我们上课的这几位老师都十分优秀,他们中的多数后来都调到了省城兰州或外地,当了大学老师,有的还成了学校领导。张克让1991年调任甘肃教育学院副院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
张克让在甘肃名气很大,但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全国特级教师的缘故。那是后来的事。按照他自己自嘲式的说法,那只不过是“一顺百顺,冠上加冠”的事。其实, 1970年代末的时候,张克让在老家陇中一带就已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我的母亲不识字,住在离县城六十多里的乡下,但她知道张克让。
对一个依赖知识而度过一生的人,中学阶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学阶段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能不能受到好的教育,实在太重要了。但这完全是运气。命运对我很开恩,在我的中学阶段,我遇到了张克让。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对我的影响最大。
二
我的初中同学杨建庆比我们村考到城里的五个人都聪明,但因为他家庭条件的限制,初中毕业就上了中专。当然,他现在也很好,在老家靖远县人大做办公室主任,也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我至今仍觉得,没能上靖远一中,没能听张克让的课,他吃了大亏。记得上一中的第一节课就是张克让老师讲的,听到中间我的脑子里就蹦出八个字:如痴如醉,目瞪口呆。这是我当时彻底进入聆听状态的准确描述,也可能是我此生当学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我是一个有点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我当时想,要是杨建庆和我老家村子里上学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听到这样精彩的讲课,那该多好!
对农村青年来说,上高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通过高考完成城乡二元身份的转变。这如同鲤鱼跃龙门,是惊险的一跳。直到今天,我还会偶尔做关于高考的恶梦,梦中,不是考试迟到,就是答题时找不到笔,或者考试成绩不理想,乃至于后来又反复参加高考。惊醒之后,确认自己早已考上大学,才又安心入睡。我和许多参加过高考的人聊过此事,似乎大家都做过类似的梦。
1980年临近高考的时候我突然得了一场伤寒病,在县城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家修养。第一年高考缺7分,名落孙山。第二年补习时转文科。1981年7月,我接到兰州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是县里的文科第2名,省里大概是第24名。
靖远一中文科班最初给人的印象是理科学不好才学文科的差生的去处。1980年,从应届理科转到文科班的包强考上了北京商学院,这之后,大家的观念才有了转变。补习后,我转学文科,第一个征求意见的当然是张老师。他以头一年包强的事例激励我:学文科照样有出息,照样可以上好大学。到了文科班,虽然他不再为我上课,但我时常到他那里请教问题,有时他不在家,雒师母代为讲解。他也始终在关注着我。那时,张老师是为数不多的参加高考阅卷的中学老师之一。1981年6月,他从兰州阅卷回来告诉我,他查到了我的两门课的成绩,分别是语文和地理,都在80分以上,估计上一个好大学没问题。张老师告诉我这些情况时是在他家里,当时他的表情和眼神我至今都还记得清楚,那不是纯粹的高兴,深邃的目光中还满含着任重道远的期待。
三
有一种小孩子叫“人来疯”,张克让讲课颇有“人来疯”的风格。只要他一站到讲台上,马上就进入角色,抑扬顿挫,手舞足蹈。讲到兴奋处,他的嘴唇微微发抖,这时的学生们也个个屏住呼吸。他几乎有着掌控课堂气氛的魔法,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满教室的空气中都是噼噼啪啪的弹奏声;讲到《过秦论》,整个教室又被悲情所笼罩。他最厉害的一招是讲到难点重点时的突然停顿,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个突然停顿里面什么都有了,给你片刻的时间,你就抓紧体会、抓紧领会、牢记心中吧!
作为语文老师,张老师最大的缺陷是普通话不过关。但我爱听他朗诵古代诗文,尤其是古诗词。他带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念起唐宋诗词来别有韵味,以至于使人怀疑那些唐宋名家是否都说甘谷话。当然,有一种可能是唐宋人的口音接近于陇右腔调,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对这些著作的理解十分到位,对其中韵味的拿捏到了十二分的火候。我曾经用普通话朗诵过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文天祥《过零丁洋》等印象深刻的诗篇,但总感觉味道出不来,没他那个效果。
张老师的板书是一大绝活。现代书法的种类当中好像没有粉笔书法。其实,应该在教师队伍里提倡粉笔书法。一些短诗,一些歇后语,一些即兴编出的对联,经张老师的板书表达出来,令人赏心悦目、过目不忘。虽然张老师近年也写毛笔字,但说实话,他的毛笔书法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太硬,太标准,缺少变化。几十年的粉笔生涯,他只适合在粗砺坚硬的黑板上书写,命运似乎已经把他定格成了一名标本式的中学语文老师。
我的一篇作文曾经被张老师用粉笔抄在学校的黑板报上,那也是我平生发表在公共场合的第一篇文章。我知道,那是一桩力气活,黑板的表面全部皲裂,写起来费劲,而且每次写之前都要拿墨汁把黑板刷过。老师用辛勤的劳动和隽永的板书来肯定自己学生的作文,这对学生是何等的奖赏和激励!我现在还能写点东西而且能够表达自如,多半应该感谢张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是他把我领进了写作的大门。
四
我到靖远县城的时候刚满15岁。青春无限好。但我要与青春进行残酷的搏斗。渴慕异性而无从下手,那些惊为天人的城里姑娘,就是自己的同桌或邻桌,可就是不敢说话。几天洗一次脸,平时不理发的时候基本不洗头,头发经常结成一个硬邦邦的“锅盖”。自卑,深深的自卑。不考上大学,你休想与这些女同学们正正当当地说上一句话,你只有偷看一眼的份儿。娶一位城里姑娘,成了当时那个懵懂少年考大学的最大动力。我听说,张克让就是大学毕业后娶上了一中老教师的女儿。我与我的青春达成了妥协,先金榜题名再说。
得要感谢当年我同桌或邻桌的城里姑娘,或许她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她们成全了我的大学梦。上大学的最初一两年,我与靖远城里国营工厂的一位女生死去活来地搞起了单相思,直到最后她随父母调到了遥远的南方杳无音讯为止。
我在靖远一中完成了我初步的城镇化。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甘肃农村,随处可见那些披衣服磕瓜子懒洋洋的少年,我曾经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刚到一中,我还是保持着披衣服的习惯,冬天上课总是把一件棉外套披在肩上。如何纠正我这个毛病,班主任张老师费了一番心思。我只记得某次课堂上,他说到穿戴要整齐,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突然,他笑呵呵地对坐在前排的我说:“大家都在看你呢,怎么回事啊?”我转身一看,果然全班同学都在看我,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因为那天全教室披衣服的就我一人。这肯定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局面,估计张老师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以一种看似不经意的委婉的方式来达到他所想要的效果。我披衣服的毛病从此得到了纠正。不过,老师这种提意见、批评人的委婉的方式我一直没有学会。我现在还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总因为说话不会拐弯而得罪人。
张老师与学生始终着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在讲究师道尊严的县城中学好像有点另类。他与学生的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自然,二是亲密,三是长久。他的普通话不好,一些字的四声念不准,他就把从小会说普通话的李宁宁同学安排在前排,随时请教,随时校正。买花椒、白糖都要凭票供应,李宁宁的爸爸是国营二七九厂副厂长,他时常会通过这位同学走后门买点花椒、白糖。据说,1960年代张老师家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是靖远乡下的塬上学生接济了他,即使三年困难时期,他也没怎么挨饿。若干年后,他的学生中不乏权高位重者,但见面时都喜欢以“张克让的学生”自称。在北京工作的学生们,平时难得一见,但只要他来,总能聚到一起,年龄和辈分相隔两三代,但统统执弟子礼。那些早年毕业的学生与他年龄相仿,但短一声张老师,长一声张老师,喊得不亦乐乎。
五
张克让一辈子烟酒不沾,没什么养生秘诀,但至今七十多岁,仍很精神。他热爱生活,却甘于淡泊。上高中时,我有一次去他家请教问题,他刚从定西地区教育局开完会回到家,还没有吃饭。师母问他吃什么,他说糖开水泡馍。一碗开水加少许白砂糖,学校食堂的馒头,掰开泡到碗里,我眼看他津津有味地吃了。在靖远一中时,他家住在铁道边上,距离铁轨大约五十多米,每天都有火车定时通过。我曾经在他家亲自体验过一次火车经过时的情景:忽然间地动山摇,哗啦啦房屋作响。师母说,后来搬到兰州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两口子都因听不到火车声而无法安睡。他是一个吃过苦的人,一个从物质匮乏年代过来的人,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近乎于无。但他始终是一个精神贵族,他的内心世界似乎没有因苦难生活而留下阴影。在靖远县城的时候,只要有电影大片上映,他总会带着师母在电影院正正规规地看上一场。现在,他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在晚辈学生们的聚会上讲话,为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上课,如果有学生与他交换一幅有特色的字画,他会长时间地沉浸在兴奋之中。
张老师1957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打成了“右派”,并开除党籍,那时他刚20岁。我看过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等等书籍,我知道他们这拨人九死一生的不寻常经历。我至今不知道他当年因何而成“右派”,我对他后来的乐观性格也难以理解。我直觉之中,他的阅历和命运绝不像他本人后来所说的“倒运”、“走运”那么简单,那么轻描淡写。
对他的“右派”一案,我特意打问过与他同时代的一中老师,但回答都是语焉不详,不得要领。最近,我在高财庭同学的博客上看到一个张老师的演讲稿,讲的是他近些年出国考察的“24条观感”,也是中国与国外的“24个‘不一样’”。他的观察既高屋建瓴,又见微知著,而且每一条都对国内的现状有所针对。直到这时,我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张老师本质上就是一个“右派”,一个天真可爱会说实话的“右派”。过去的这么些年,我们被“左派”害得不轻。我觉得,这个世上还是多点张老师这样的“右派”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老师与我的母亲同庚,都已是75岁的老人。我希望他们与全中国的老人一样,都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当然,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希望张老师能为他所处的时代做一些反思性的工作,因为他有这样的阅历和能力。一个20岁的“右派”,一段20年的沉冤,亲人付出生命,自己也曾在死亡线上徘徊,那是怎样的刻骨铭心,为什么不写出来?在写这篇文章的采访中我发现,至今在一些人心目中,对当“右派”一事还是讳莫若深,甚至视为可耻。现在的年轻人对现状有些不满,但我们的国家原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并不知道。我希望张老师能在有生之年把他丰富坎坷的人生写出来,对自己、对后人、对这个时代,都是一个交代,也是一份财富。
(摘自《烛光——张克让先生风采录》,北师大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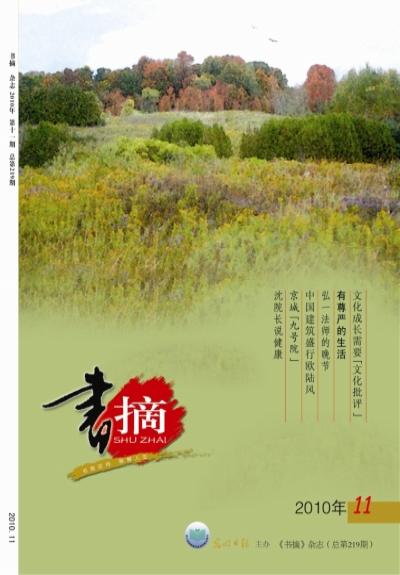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