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九号院门口经过。我情不自禁地注目而视:厚重端庄的大门依旧,“清代礼王府”的大理石门牌依旧。门侧,警卫战士荷枪而立,这些哨位不知迎送了多少次新老兵交替,但看上去仍然感到亲切熟悉。二十余年过去,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大门比较,风貌居然一如当初。但是,我知道,这个深邃神秘的院落而今物是人非。当年,这里曾经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院落内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农村改革息息相关,现在,它已经从农村研究者的视线里消失了。
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
这是一个宏大而古朴的院落,是清代的礼亲王王府。据说,明代这里也是一个王府,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师入京之初,并没有直接住进紫禁城,而是先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三天。王府内有六七个规模不等的小院落,这些小院落基本上都是四合院,有的甚至是两三进的四合院。现在,从功能分配上大院大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区主要是两个部门办公用,其中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北区主要是住户,三个大的院落里分别居住了三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当时卸任不久的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另有两个院比较小,主要用于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们办公,分别称一号院和二号院。一般工作人员都在一栋三层的办公楼里办公,通常被称为小灰楼。报到后我被分配在秘书处,办公就在小灰楼第二层中段。后来我做秘书的时候,先后在一号院和二号院办公。
这年夏天,大院这边忙乎的主要事情,是准备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此前的早春,中央刚刚发出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这个文件成为著名的“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的第一个。正在准备的这个文件后来成为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
在我的印象里,讨论第二个一号文件的会议开得很红火。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将近二十天。讨论非常热烈,但是因为“政策坚冰”基本打破,意见分歧不像讨论是否允许家庭承包那样尖锐,所以气氛并不紧张压抑。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改革初期的农村现实呼唤出来的,迫切需要解决。地是承包到户了,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大型农业机具,如拖拉机之类,问题需要回答;农民在种地之余,可不可以搞倒买倒卖的长途贩运,也需要回答;雇工已经出现,但政策是否允许,也必须回应。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则属于大政方针。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上面没有部署,政策没有松动,基层很难施展发挥。比如,私人买拖拉机问题,如果中央没有统一的政策允许购买,即便是农户要买,也没有办法买到,首先是国家的工厂就不卖给私人。九号院里的会议,九号院派出的调查人员,许多都是以此为议题。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政策问题,往往要等到当时的几位中央最高领导表态,有的是口头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农民搞长途贩运,有材料说是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当时的总书记就批示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这些最高层批示表态,是政策文件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了三个一号文件。这几个文件的突出贡献是及时地回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有效地突破了束缚农民的旧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基本架构。
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不仅限于政策研究。当时,九号院整合了全国的农村和农业研究力量,把高校和科研单位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直接为应用研究服务。那些年里,经常出入九号院的还有大量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来自北京,也有许多来自地方。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还有另外一块牌子,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这个中心的名义,有一笔数量不菲的专款用于资助社会力量的研究课题,调动了各种学术力量为政策研究服务。不仅如此,这个中心还开展了许多国际交流合作。当时,一些西方学者通过这个中心到中国来,九号院里的领导利用这些机会听取吸收外方学者的意见。通过九号院的安排,这些西方学者有的还与国务院领导会见讨论。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最末一年,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撤消。机构变动发生在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之后。以我个人的体察认识,在机构撤消之前,九号院的影响力就开始有所衰弱,大概开始在第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时候。标志约略有三,首先是80年代中期那年的粮食大减产,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一些质疑,甚至出现了激烈批评;其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那时人们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政策精神有些含糊。在第五个一号文件之后,1987年仍然发出了农村工作文件,这个文件是当年的五号文件。这个时候粮食产量还在徘徊,农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九号院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机构撤消一年后,又是夏天,近二百工作人员被陆续分配到五个相关部门,人们不无悲凉地各奔西东。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划归另外单位的部分人员还在这里办公,我和部分同事还在这个院落。但是,对于农村研究来说,九号院风光不再。1998年秋,新单位整体迁入新址办公,我们与这个院落从此作别。今天,我是作为一个路人从门前匆匆而过。
许多人知道,九号院里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智库,因为五个成功的一号文件而辉煌。现在,诸多智库仍在,各类文件更多,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当我把目光从九号院转移到广袤的中国农村,透视20年来的发展变革,依稀看到,“文件”时代已经晚景凄凉。在基层,许多领导讲话,上级怎么讲,下级怎么讲,村支部书记讲话如同《人民日报》社论,讲话完了往往烟消云散;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许多规定要求,左一个文件强调右一个文件强调,说了一年又一年,但是问题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就文件本身来说,现在的文件立意不可谓不高,思路不可谓不深,方向不可谓不清,其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当年,但问题在于往往无效。过去的文件发挥作用,很重要的是借助了大一统的体制力量,上边怎么指示,下边基本上怎么贯彻。现在,体制已经不再大一统。体制外部,民间力量多姿多彩而且蒸蒸日上,各种利益主体在千方百计表达权利主张;体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各有诉求,各有表达手段,虽然无人公开藐视体制的权威,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却是各怀心思,各展拳脚。体制的这种新变局,用美国政治学家澳森波格对中国的观察,叫做“碎片化的权威体制”。改革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较力”,也成为各种体制力量之间的“较力”。如同一个棋局,过去基本上有一种力量在指挥全盘,现在,虽然这种力量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去指挥一切的力量其实只成为多种力量的一方。于是,虽然指挥号令还在发,但是,运作逻辑已经不同,变成了一种“对局”,时髦的说法叫“博弈”。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发文件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执行,甚至从思想上就反对这个文件的精神。文件的形成可能是体现了高层的精神,但是,文件的执行则各有各的精神。我在基层调查,有乡镇党委书记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改革历程昭示,创造辉煌的真正动力是农民,因为问题由他们提出,发展由他们创造,高层所做的,往往只是顺应和追随的工作。
众“老” 云集
几乎整个1980年代,九号院是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中枢之地。西皇城根下,这个富有历史感和神秘性的院落,曾经聚集了一些高层政治人物。我初出校门便进入其中,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印象深刻的,不仅有政策过程中的诸多往事,还有一些“老”者。这是一些革命资历比较深的人,通常,我们称呼为某“老”。从这些“老”身上,或许可以捕捉中国政治的沧桑流变,品味改革年代的风云激荡,甚至还有更多领悟。
九号院里“老”很多。于我来说,第一个见到的是张老,名平化。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高级干部。第一次见面就在他的办公室。1982年盛夏,他召集了五六个新进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座谈农村情况。张老是湖南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中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后跟随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建国后,长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曾在他的麾下任湘潭地委书记。1977年7月,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据说是因为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中出了问题,1978年末离开中央宣传部,胡耀邦接了他的位置。1978年11月30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释说:“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公开表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文件,总觉得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1979年,他来到九号院,职务是国家农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初次见面的最深印象,是他的“领袖”风度。当时他75岁,讲话声如洪钟,言简意丰,非常有气势。因为第一次见这样的高级干部,我兴奋而紧张,至今不记得都向他汇报了些什么。几天后去给他送文件,有机会看到了他的居所。他住在民族宫后面的一个四合院里。这个院子是“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在位时住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的四合院,也是第一次走进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住所。走进那样的地方,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历史风云的循环往复,感慨政治人物的命运莫测。
经常见到的还有一位张老,名秀山。这位张老的经历更加跌宕起伏。他是陕北人,1929年参加中共,与刘志丹、高岗等一起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国初期,高岗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他是东北局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高饶”事件发生后,他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成员,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被撤销职务,从行政4级降为8级,安排在辽宁盘山县一个农场当副场长。1978年末,他到新组建的国家农委担任副主任,进了九号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以后,他经常到单位来。退到二线以后,他除了开会基本不到单位,花大量时间在家里写回忆录,全部是自己手写。写好后叫孙秘书拿到单位的文印室打印,我有时也帮助校对。关于“高饶事件”,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高岗在东北局的工作并没有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执行的是党中央的路线,在干部任用上执行的也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不存在宗派集团。张老最不能理解的是对他的处分。整个处分过程没有具体事实、没有组织审查、没有组织谈话,也没有听本人申述。这个处分报告只有五六句话,说他“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1978年重新安排工作时,他提出1954年的处分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先抓工作,以前的问题以后再说。”晚年,他一直在“请求组织上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得到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结论”,并说是“对党最后的、也是惟一的要求”。我是在文革中读的小学中学,关于党史的知识都是接受的标准说法。那时,张老的这些回忆讲述,给我的冲击很大,朦胧地感到党史问题复杂纷纭,党内斗争的是非曲直难以辩说。
九号院里还有一“老”,那就是华国锋。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华国锋继承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一段时间还兼任国务院总理。当时,他被称颂为“英明领袖”,他的照片是和毛主席像并排挂在教室里。刚进九号院上班,马上就有同事告诉我:“华国锋就住在这个院里。”他的家就在这里,门口另有单独的岗哨。我没有进过他的家,但是经常会看到他在院子里散步。据我所知,我们在这里办公十几年,周围的同事和我都没有同他讲过话,偶尔会与他的护士和警卫员说话。如果我们向他致意问好,他通常只是微笑或点头示意,并不说话。但是,他比较喜欢与院子里的小孩子搭话,我很多次看到他与在院子里玩耍的孩童说话。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随我到单位在院子里玩,恰好华老出来散步,竟与我儿子攀谈起来,问上哪个幼儿园、家住什么地方。他不与我们这些人对话,也许是一种刻意。他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在海棠树前驻足片刻,然后继续在院子里默默地走路,视周围过往人员若无物,神情落寞深邃。刚进九号院,最初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好奇,但是十几年下来,不时会看到他,就会另有感受。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隔着玻璃看见他在院子里走过,不禁琢磨:他在想什么呢?关于他执掌中国的那几年,关于他在中国政坛最高层的浮沉,他有什么感悟和思考,难道他不想对世人说点什么吗?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一次次看到他在院里散步,甚至擦肩而过,我总是出现这样的困惑。
九号院里的农村工作机构,在1979年初成立的时候,是由当时的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兼任主任,1980年初万里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改由万里兼任主任。说到九号院里的诸多“老”者,还必须说到杜老,名润生。杜老是当时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我们的单位领导。与其他一些老不同,他是一线领导,我们通常不称“杜老”,而是称杜主任,也有年轻人直接称为“老杜”。杜老在新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值得专门研究。还有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曾任安徽省长的王郁昭,曾任吉林省长的张根生,还有50年代曾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反对大跃进而被打为反党集团分子的杨珏,等等。每个人几乎都有不寻常的经历。
(原载《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9期、2010年第8期,本刊缩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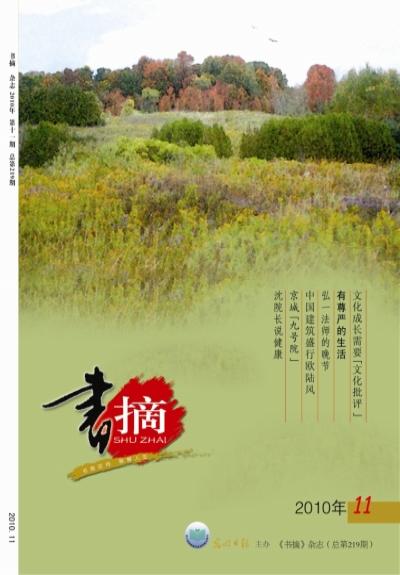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