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周立波在场上表演的是生活中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他儿童和少年时期“异常顽劣”的经历。
我妈那时天天打我,除了不打头,其他都是她的打击目标,打了之后我就像斑马一样到学校去,真的很丢人!两个女同学看到我老起劲儿了,说:“呀!周立波,你妈妈又买新拖鞋啦!?”我问:“你们怎么知道?”她们说:“你今天这个花纹跟昨天那个花纹是不一样的啊!”
我那种皮是很另类的。记得在我们那个年龄都会请木匠到家里面打家具,我家就来了一个。木匠带了个小孩,那个小孩经常要跟我玩,我不跟他玩他就哭。有一天,我把木匠锯下来的木屑、锯末之类的都放在碗里,用热水一冲,挺厚的一碗,像藕粉似的,然后我就骗他儿子说:“哥哥给你吃藕粉哦!来,要一下子吃完的哦!给你吹吹啊——来,预备,啊呜——”他就真吃了,一口进去,“哇”就哭了,因为那种樟木锯末很辣很辣。他一哭,我妈又是一顿打。第二天我就把胡椒粉撒在手背上,跟小孩说:“你想不想要很阴凉的感觉呀?”我给他示范,把胡椒粉放在鼻子跟前:“你一定要用力吸,要使劲儿,知道了吗?好,来试一下!预备,来!”好,又哭了。所以我的确是该打,很恶劣。
隔壁的一个好好阿婆好打小报告,我就想要怎么才能报复她一下呢?那会儿鸡是很稀奇的,买回来都要养着,不舍得吃。有一天,我看到好好阿婆那只浦东三黄鸡,用很高傲的眼神看我。我气不打一处来, 就把弹弓的橡皮筋卸下来喂它。我喂了它29条橡皮筋,每丢一根,鸡都非常好奇地上来,“啪”一下子吞掉了,“啪啪啪啪”,29根下肚了,打结了,不一会儿我就发现鸡看我的眼神不对了,很迷茫。然后它就慢慢倾斜,脚慢慢地撑开,往后仰,整个身子就软掉了,我一看,吓死了,一只鲜活的鸡当场就变成一具尸体了。
起初好好阿婆觉得可能是鸡瘟掉了,快点把它杀了吧,眼见着阿婆拔完毛,把内脏取出来,等她把鸡的胃拨开看到29根橡皮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转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哇!我真是被妈妈暴打了一顿,打到那个好好阿婆都不好意思了。
周立波的童年经历,在舞台上引来无数欢笑,在他那些和家人斗智的创意里让人看到一个演员的潜质,和一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
记得我那会儿坐在马桶上,旁边有杂物的,我看到了爸爸的套鞋,哎,这个鞋跟怎么这么厚?里面究竟是什么呢?我用我爸的胡子刀把它割开,一看没什么,又放回原位了,放好以后自己就有点害怕了,迟早要被知道的嘛。还好,两个星期没下雨,等到下雨的时候我都忘了这件事了,只看我爸爸回来之后每走一步都是“卟唧卟唧”的声音,两双鞋全进水了,于是我爸上报我妈,我妈继续打我。上海男的一般很少打自己的孩子,都是妈妈打,如果男人打自己的孩子会被别人认为娘娘腔的。
当时麦乳精实在非常稀奇,只有尊贵的客人来了才会拿出来泡。哦哟,我同学五六个人过来,一人一调羹,有的还再加一调羹——当然通常是加给女同学了,结果一下就没了半罐。那可怎么办?我把剩下的麦乳精全倒出来,把报纸放进去垫着,再把麦乳精倒回去,这样看起来又是一罐了哈。现在饭店那种牛肉下面垫着好多萝卜丝的菜全都是跟我学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海绵铅笔盒,那时候可是非常稀奇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玩吸铁石和海绵,所以第一天用我就把这个崭新的海绵铅笔盒一刀拉开,把吸铁石分别送给了旁边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做完这事以后知道自己闯祸了,不能回去了,居然想到了逃。下午没上课,先跑回家拿了五条年糕,三条插在腰间,其余两条给了同学,因为我是老大嘛。我说我们沿着北斗星走,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根本不懂哪里是北斗星,就是沿着铁路走,还搞得像战争片一样:“同志们,这条铁路就可以通向北京!走啊!去见毛主席!”结果从市区走到郊区就走不动了。我发现不认识路了,就又回来了。到家以后不敢上去,躲在家门口。哇,没想到整栋房子的人都出来找我,我爸爸妈妈真的被吓到了。隔壁邻居一看我躲在旁边,把我一把抱上去了。我家当时住三楼,妈妈看到我就抱头痛哭,爸爸也急死了,问寒问暖,给东西吃,给我洗澡,所有人都来看我,这时候我想差不多该打了吧?可是没打。我竟然睡得好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做很有道理。没过两星期,一闯祸,又逃了。
这次回来真的刻骨铭心了,我爸第一次打我,他是体育运动员,“啪”地一巴掌下去,就把我搞到位了,到现在为止都没再逃过。
当时家里靠墙边有个桌子,我妈妈每次回来以后我都会把桌子放在屋子当中,这样一旦挨打我好有迂回场地,妈妈追我的时候我就沿着桌子转。有一次我技术失误,妈妈追得我太狠了,我“噌”一下钻到床底下去了,以为钻进去妈妈就抓不到了,想不到我妈妈把床板翻起来,然后把一边的出口堵住,我无处可逃,狠狠地被打了一顿!后来我就再也不钻床了!
我从小就极有表演欲望,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可能是好多天没被打了,骨头有点儿轻。正值放暑假,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大热天的我把泡泡纱窗帘拉起来,把一整瓶墨水全部涂在脸上、身上,再用刀把家里的西红柿酱打开,涂在各处,好像七窍流血,还把多下来的西红柿酱抹在菜刀上,然后在家正中斜躺着,做成那种他杀现场,把我妈妈吓得尖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想引起大人的关注吧。
周立波的创造力给了家长启发,在父亲的鼓励下,不够年龄的他和姐姐一同报考了上海滑稽剧团。
当时考上海滑稽剧团很不容易,报名的有二千八百多人,最后只收了16个人,姐姐第一轮海选的时候就被淘汰了。那时候我也就15岁,没经过正式的表演训练,基本上只考原始反应,所以严顺开就考我一悲一喜。考到喜的时候,他说家里面买了个彩色电视机,你开心吗?我说很开心。他问彩色电视机怎么样?我说非常清楚!他说怎么清楚?我说,哎呀!那真是黑白分明啊!毕竟小时候知道的形容词有限,所以要描述什么叫清楚只会用个“黑白分明”。结果严老师马上反问:“慢!彩色电视机怎么黑白分明?”我说:“今天放黑白电影!”他一叫停:“就是你了!回家等通知吧!”我们共考六轮,这是第三轮,我就被录取了。
上海襄阳南路上的“大可堂”是当年上海滑稽剧团的原址,1981年至1990年之间,我在这里待了差不多十年,家人那时最头痛的回忆就是经常全家去学校挨批。最后爸爸被批烦了,就跟老师说:“要不算了,你们把他开除吧,我们也没办法,教育不好。”
当年我们完全是按照戏剧演员训练的,要开韧带。怎么开?就像渣滓洞一样,每人一个垫子躺着,老师把一条腿摁住另一条往上拉,一直要去碰头。同学们都比我大,有的将近二十岁了,韧带拉不开,很痛苦。16个人排队准备开韧带时,前面的同学一边拉一边哭喊,老师帮你撕裂,疼得受不了。我是最后一个,躺在那儿还没开始拉就哭了,哇哇地喊,“老师啊——”还企图逃跑,被老师给抓回来了,按住腿就开始拉,结果我哭着哭着发现我的腿完全可以碰到头,而且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我们住的是那种老洋房,二十米长的甬道没有灯,平时很怕人的,经常还放点布景什么的。当时我同学打热水必须要通过这条甬道,但是因为很害怕,就会唱歌给自己壮胆,我经常躲在黑暗里,等他过去了,跟在后面鬼吼,把男同学都吓哭了。
当时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写一次检查,后来写检查跟开支票一样,都有套路了,基本抬头换一换就是了。我们是三年毕业,再实习一年,等我从学馆毕业的时候,馆长给我的毕业礼物就是我所有的检查,他说:“周立波,你今天毕业了,成为上海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了!来,这些检查还给你!”我接过来一看,简直像《家春秋》一样,很厚的一摞。
注意形象的周立波在不模仿别人的时候往往温文尔雅,不紧不慢地历数流年岁月,观众鼓掌大笑,他不时微鞠一躬,一副很老派的腔调。可是一模仿起别人来,他又“坏”得让人抓狂。一些近年来走红的曲艺笑星在他的嘴里也有新的解构。
我得出一个结论,文化艺术界的人,凡是脸难看的一般实力都很强!张艺谋的脸难看哇,绝对的!他这个脸就像被菜刀劈过一样!而且是没开封的菜刀!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大师啊!奥运会恢弘巨作不得了。再比如冯小刚,他这个脸还能叫做脸吗?冯小刚这个脸,如果晚上九点半我在弄堂里碰见他,他只要走过来,不要他动手,我直接把钱包交给他!但是人家拍出来的电影怎么样!
现在我们大众心态越来越包容了,至少我们现在承认李宇春是女的了吧!我上次从电脑里打开一看,李宇春一张海报老漂亮!小姑娘老阳光!海报下面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句标语,叫:生男生女一个样!
北京有一个机构,他们想促成我和北京的郭德纲先生在上海同台献艺,我婉拒了,这当中没有贬义,为什么呢?不和谐。一个吃大蒜头的和一个喝咖啡的,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文艺界,包括我自己,凡是脸长得难看的,活儿都很干净,出来的东西都不差!
但凡我拿来开玩笑的人首先是我很喜欢的人,是我关注的人,比如我说刘欢。有很多人说,刘欢怎么这么大牌,一个奥运会,人家莎拉·布莱曼这样的月光女神都盛装出席,他怎么能穿件老头衫出来呢?我说人家刘欢可以穿有领子的吗?要穿有领子的恐怕要穿到耳朵这边了吧?关键在于你要听的是他的歌声,如果要看漂亮的去看周润发就好,可周润发唱得又没有刘欢好。
费翔长得好是因为费翔是混血儿,混血儿想混得好有诀窍。我发现混得越远,长得越好,如果我是混血儿的话,顶多是越南跟柬埔寨混出来的,所以要混得远一些,但远到太空就要混出ET来了。
有个沈阳的朋友心直口快,有一天他跟我说,立波,像你们上海男人吧,我真的有点看不惯,到你们上海出差,经常看到上海男人在马路上只干嘴仗不干真仗。在我们沈阳,一句不对,干啥呢干啥呢?就干起来了!这叫男人!我对着他笑了笑,哥们,你知道不,中国哪里出流氓的?他朝我眼睛乱翻,我说哥们告诉你:中国是上海出流氓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你们东北也出,出土匪。他说不过我,急了,我说你知道吗哥们?流氓从来不打人,打人的就不是流氓。我们上海流氓看谁不爽只说一句话:奈伊组特(把他做掉)!去做的可都是你们东北人呢!
最近法国总统脑子绝对被枪打过了,总要和我们中国对着干,结果失策了吧,绝对失策。我们温总理用儒家的方式对付他,进行了环法游,就是不进去,气死你。这个萨科齐正宗有问题的,他去和他们法国人浑身没关系的达赖碰面,达赖能给你点什么?最多给你这样(拥抱),就这个动作了,因为这个动作,我们中国把一百多亿欧元的单子勾掉了,就不给你,气死你。
我上个礼拜正好在酒吧里玩,碰到一个法国朋友,他是中国通,他说,波波,我真的搞不懂,你们中国政府也太敏感了吧?看我们法国总统想见谁,是我们总统的自由嘛!我说,哦,是吗?那你们总统为什么不去见拉登呢?
外地人夸奖我说,立波,你一点不像上海人哦!奇怪,我就是上海人!我干嘛不像上海人?北方人很看不惯我们上海人的,很奇怪,我们又没得罪过他们。你们说我们小家子气,我们上海财政收入的87%都交到国库去了。你们自己往上面查三代,哪一个没吃过我们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哪个没穿过我们上海的的确良衬衫?都得过我们上海的好!
20lO年我准备开一场“海派清口”演唱会,唱别人的歌,说自己的笑话。比方说张学友的歌,我唱一句“许多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就插一句“为什么你的幸福在别人的嘴里”?哎,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可怜,就为了别人一句“他是好人”,辛苦一辈子。接着再唱“我也知道你永远不能够爱我”,再插一句“你有毛病啊?你知道他不爱你你还爱他干什么”?接着唱“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花儿谢了还会再开的嘛。这样解构以后重新解释,会达到一种很好的喜剧效果。
50岁之前,我让大家看一个上海男人的睿智;60岁以后,让大家看一个上海男人的健康。我很顽强地跟我的团队说:“你们做计划做八年就OK了,我的生命有周期,事业也有周期,50岁的时候我坚决退出,十年以后再复出。”把前十年退出后的积累重回舞台释放。现在连申花队的队歌都变成我的话了:奈伊组特!其实“把他做掉”在上海是很广义的一句话,比如把某件事做掉,把某个人做掉,把某块布做掉。没想到踢中超的时候,申花队一千人的蓝魔队就把口号变成:“噔!噔!噔!把他做掉!”一千个人边喊边击鼓,就像当年的“四川雄起”一样。
有句话叫人生不可设计,我觉得让自己以最舒服的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是重要的,所以不想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光盘只有《笑侃三十年》是正版的,其他的都是盗版,我没出的碟他们都给我出了。2008年11月我受一个理财博览会的邀请去做了一场专业财经脱口秀,台下90%以上基本都是金融界的。做完以后我们自己留了资料带,不发碟,最后这个碟不知道怎么流出去了,变成了现在市面上的“周立波至爱:我为财狂之二”。碟上面印着我的照片,下面的简介我一看差点儿晕过去,写着:周立波,生于1908年到1978年。做盗版的人把我当大作家周立波写了,而且还说我是1932年入的党,我要真1932年入党还在这儿玩吗,有什么事儿到中南海来找我。
(摘自《鲁豫有约·开心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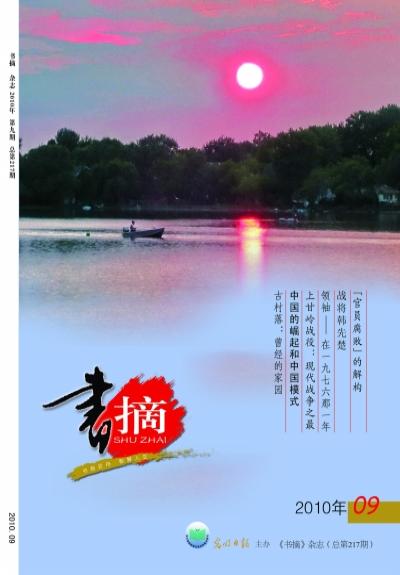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