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
我家原来有辆永久牌自行车,是舅舅在大同煤校上学时我妈给他买的。买的时候就是旧的,他骑了几年就更破旧了。他分配到晋中当老师走后,我妈就把车子寄放到了老和尚的后大殿,不让我骑,说我人小,把握不住车子,怕骑到街上出事,怕汽车撞了我,怕我把别人撞了。
初中毕业后的那个假期,我接到了大同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一中离城十里地,又没有公共汽车。这时候,我妈才说,让师父把大殿的车子取出来,擦摸擦摸骑去吧。我说我不要,旧车子闸不灵,容易出事儿,我要骑就骑新的。我妈说闸不灵,修修就灵了。我说您不懂得,车子放得年代久长了就锈了,锈了就修不好了。我父亲说,锈了修不好,闸不灵,娃娃出了事儿咋办。我妈说,修不好再说。我父亲说,修不好就出事了,到时候你哭也来不及,哪个多哪个少。
我父亲这辈子一直没学过骑自行车。他不会骑,也就不懂得车子的事。我一说他就相信我了。他说:“爹挣钱为啥,不就是为了俺娃花,爹给俺娃买辆新的。”
那是个苦难年代,车子是紧俏商品,没个关系不好买,他在大同托了好几个人都没能买到。他只好就在怀仁给我买,那次来信了,说买到了,是一辆绿色的飞鸽车,二八的,加重的,说等有了顺路车就给我捎回来。我心想哪会一下子就有顺路车,我给他回信说,太原每天好几趟到大同的火车,托运回来多方便。我还催他说,学校就要开学了,可我现在还不会骑,我总得提前学会才行,学会也还得再练练,练得很熟才行。实际上我早就学会骑车了,而且骑得还挺油,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熟练的问题。我是想让他快快把车子托运回来,才这么说。
在我的一催再催下,他把车子给弄回来了。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给托运回来的,他是一步一步地推着,一步一步地推了八十多里,给推回来的。
那天的半夜,我正睡得香,听我妈说:“招子,好像是叫咱们。”她拉着了灯,听听,就是有人在敲庙门,边敲边喊招子,声音很是微弱。我妈说半夜三更的会是谁,她就穿好衣服去开门。
我的老天哪,是我的父亲。
我妈把他扶进家,他一屁股给跌坐在地下。我赶快跳下地去扶他,他不让动,摆着手说:“缓缓,让爹缓缓。”又伸手说:“给爹倒口水。”我拿起暖水瓶,他摆手说:“冷水,拿瓢。”我便从水瓮里舀出多半瓢,他捧着瓢,一口气把半瓢水喝了个光。
他坐在地下一动不想动,我站在那里陪着他。
他的灰衬衣让汗水浸透了,上面又沾满着泥土。
裤腿挽起着,也全是泥。
他说是为了截近,趟着水过的十里河,可过河的时候,把脚给嵗了。他这硬是一拐一拐地又走了十里路,拐回了家。
他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汗水把脸上的土灰刮得一道道的,连眼角嘴角都是泥,嘴角好像是还有血。
人们都知道,不会骑车的人,推车子会更费事。走个三五里也还好说,可他这不是三五里,也不是三十五里,是八十里。空手步行八十里那也是不敢想的事,况且他还推着个车子。他从一大早就开始走了,我算了算,整整走了十九个小时。而最后这十里路还是忍着饥渴,拐着瘸腿,咬紧牙关走的。看看他那两嘴角的血,就知道他是经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看着他那大口大口喝凉水的样子,看着他那极度疲惫的样子,我心疼极了。我不住地“唉,唉”叹着气,我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
缓了好大一阵,他才让我往起扶他。我伺候着他洗了脸,换了衣裳。他让我给脚盆添上暖瓶的水,他靠着炕厢坐着扇火板凳,烫脚。
我问他为啥不托运,他说他到怀仁火车站打问了,托运得半个月以后才到,“可我怕误了俺娃学车,多学半个月跟少学半个月,那就是不一样。”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紧,像有刀子在扎,像是有鞭子在抽。
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笑着给打岔说:“过河时把车子弄泥了,你出院把它擦擦。”
当我擦完车子进了家,我妈也正好给他把饭做熟了,可父亲他却脚泡在水盆里,坐着小板凳,身子靠着炕厢,就那么的给睡着了。
吃饭时,父亲见我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反而给我说开导的话:“这有啥,爹缓上两天就好了,可这样俺娃就能早学半个月车,就能学得熟熟的,路上不出事儿,那爹就放心,爹受点苦值得。”
父亲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难过。
我真后悔,真后悔!
拉炭
我九岁那年,我们家搬进了庙院住。这个院本来是寺院,叫圆通寺。解放初期限制宗教事业,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大同县政府就占用了这个庙院,当做办公地点。1958年县政府有了新地点,搬走了,就把这个庙院当做了家属院,分给了干部们,我父亲也分得了一间。这样,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一直再没往走搬。
住平房的人家,做饭都是烧煤。冬天取暖也是用煤。
我母亲在别的方面很是节约,可唯有这个烧煤,她不仅是不节约,叫我看还有点浪费。别人家做完早饭就把火灭了,我母亲不,她要让火一直着着,着到做午饭。吃完午饭,火还不让灭,着到做晚饭。冬天烧取暖的火炉就更是这样了,这个炉子二十四小时不灭,家里永远是暖烘烘的。还有就是,年三十和正月十五别人谁家都不垒旺火,就我妈垒,在院门前垒个旺火,都快有我高了,少说也得二百斤煤。全院人都来烤旺火,拿着馒头来烤旺气馍馍。好吃完一年不肚疼。
我妈这么喜欢火。那我们家用的煤就比别家的多,最少也是别人家的两倍。拉煤的这个活儿,一直就是我父亲的。他低着头弯着腰,像老牛耕地似的拉着车,我妈鼻疙瘩黑黑地在后面跟着,为的是上坡儿时给他推一把。拉到街门口,他就再不用妈了。叫我妈回家做饭,他独自往进院里搬运。他一直就不用我帮。我经常是在放学回来,就看见家里又买了煤了,可也已经收拾好了。有时候我也能碰到父亲正往院搬煤,我要给搬,他不让。
——不用俺娃,不用俺娃。
——俺娃看把衣服弄脏,看把手弄脏。
——俺娃入家捞骨头去哇,锅里肉早炖烂了。
拉煤这天,我们家总是在吃好的。要么是吃油炸糕,要么是吃饺子。不管吃啥,锅里总是炖着肉。家里总是香喷喷的肉味儿。
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不让我帮,可我参加了工作了,他也是不让我帮。好像是我一插手,就把他的功劳抢了似的。
我父亲一个月回一回家,一回家他就侍弄他的这些煤。
厕所旁的煤垛都垛的是大块儿,他坐着个小板凳,“嘎嘎嘎”、“嘣嘣嘣”地拿锤子把大块儿煤砸成个鸡蛋大的小块儿,一筐一筐地倒在窗台前的煤仓里。差不多用一天的时间,把煤仓装满,第二天他就去煤场买新煤。煤场出租小平车,一小平车能拉八百斤煤,他连着往回拉两车,拉回来垛在厕所旁。把煤安顿好了,他这才能够放心地到怀仁上他的班,做他的革命工作。
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一年都这样。
大概是在1973年这一年的第四个月,天很冷。
那天早晨,我在被窝里躺着,听见母亲在地下给火炉加煤。我睁了一下眼.看见父亲也在被窝里躺着。母亲不把家弄得暖暖烘烘的,她是不许我们起来的。
我听他们又在说拉煤的事。我妈说:“老了,不行就拉上一趟,明儿再拉一趟。”父亲说:“咱们到时候看哇。”
这时候。我才一下子想起,想起父亲老了。已经六十三了,不能让父亲再干重活儿。
我爬起身说:“爹,拉煤的事儿,以后就交给我哇。”父亲说:“快不用俺娃,俺娃好好儿给人家做工作。”
当时我调到矿区公安局已经半年了,我的工作是在机关给写写画画。我说:“您该走就走您的,过两天单位不忙了,我给回来拉。”父亲说:“快不用俺娃,爹一辈子窝囊,没本事给娃娃弄个好工作,娃娃自个儿弄了个好工作。快不用俺娃,快不用俺娃。”
我妈说:“你老了,你得服老,六十三了,你当你还三十六?”父亲说:“老了,咱们不会少拉点。拉不动八百拉五百。就按你的,咱们今儿拉一趟明儿拉一趟。”
那些日,矿区要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我得赶着给我们局领导写发言稿。我没硬坚持着自己拉,也没留下来跟父亲一块拉,就到了单位。可就是这次的大意,给我留下了终身的悔恨。父亲心疼儿子。把脏活儿累活儿自己包揽下来,可儿子却不懂得心疼父亲。真把六十三岁的父亲当成了三十六岁。父亲就是在这次拉完煤后,身体就垮了。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感冒,这个从来不知道去痛片是什么味道的人,一下子就给累垮了。
父亲他没按我妈早晨说的那样一天拉一趟,他还是给拉了两趟。第一趟回来他说这拉五百斤跟没拉一样,于是就又去了个第二趟。可就是这第二趟,把他给累坏了。整理完洗洗脸就躺下了。连饭也不想吃,我妈硬让他吃,这才吃了五六个饺子,喝了一杯酒就躺下了。我晚上八点多回来,他已经脱了衣裳盖着被子睡了,也不知道他是怕我责怪他还是真的睡着了,一直没跟我说话。
第二天他说精神了,吃完早饭就走了,到怀仁上班去了。可走了不到十天,回来了,是让梁会计给送回来的。全身蜡黄,连白眼球也是黄的。
我领着他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肝癌。
谷面糊糊
我不能跟父亲说他得了什么病,我只跟父亲说他得的是“肝大”。肝大这叫什么病,可父亲他不懂得,跟探视他的人说:“你看我得了个灰病,肝就给大了。”
我盼着医院是诊断有误,就换了一个医院又一个医院。可医院每次也用不着我提出说要转院,他们就提出说我们这里治不了你父亲的病,你要不换个医院试试?
每住进一个医院,父亲躺在白色的病床上,他就觉得自己是有希望了。他希望着大夫能把自己肝大的这个病治好,让他精精神神地回家去。回去给家里劈生火柴,装几篓。把煤砸好,装满仓。家里都安顿好了,他就坐火车到怀仁,那里有心爱的革命工作在等着他去完成。
每过上两个星期,各种常规的和特殊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去大夫办公室,用眼睛盯着看他们。我盼着主治医跟我笑,可每次看到的都是他也看我,然后摇头。
转院。
父亲一听说又要转院,就问:“咱们住得好好儿的咋又转院呀?招子,咱们就这儿治哇。”
我知道,父亲很疲劳。好不容易这个检查室那个检查室地转完了,他不想再楼上楼下地爬那些楼梯了,但不行。明明知道这里治不好,怎么还要待在这里。得走,再换个地方试试。
到省城。
父亲在省党校学习过三年,对省城有感情。又一看医院比大同的医院都好,他认定这里肯定能把他的肝大治好。大夫让他做啥他就做啥,就像是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那么地认真。咬紧着牙,楼上楼下地坚持着。
我说:“爹,大夫让您多吃饭,只有多吃饭才能有抵抗力。”他说:“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他永远忘不了革命。
我在医院外面租了一间八平方米大的小屋,屋里有个小铁炉。那天,他跟我说:“招娃子,爹可想吃顿谷面糊糊煮山药瓣。”
谷面,就是谷子磨的面。我父亲小时候他们家穷,不舍得把谷子皮去掉吃小米,而是连皮一块儿磨成面,喝这种带着糠皮的面糊糊。
山药瓣是我们的家乡话。就是把一个整的山药蛋顺着一个方向切成四块或是六块,这就叫山药瓣。
山药瓣容易做到,可这谷面到哪儿去找。
在省城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大夫们隔三岔五地会诊。可最终也没了信心,劝我们直接回家。他们没让我们再去别的医院试试,而是说哪也别去了,回你们大同吧。临走还说了句我最不想听的话:“别再看了,老汉想吃点啥吃点啥,想喝点啥喝点啥。”
从火车站一回家,我妈问我父亲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做。父亲说,玉茭面糊糊山药辦,我妈说这好说。可做上来,父亲只喝了半碗,吃了两辦山药。我妈说,你想了半天就喝了半碗。父亲说,还是那谷面糊糊好。我妈说,跟哪给你寻谷面去。
父亲说:“我是说的个话,莫非还真的能让娃娃到下马峪去寻?大老远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父亲的饭量一日不如一日,一天只喝半斤奶子。无论怎么劝,也再不吃别的了。只是躺在那里昏睡,你喊他,他哼一声,你不喊他,他动也不动。
这可怎么办?可就在这时候,我一下子意识到,父亲说“莫非还真的能让娃娃到下马峪去寻?大老远的”,他那是在提醒我:下马峪村有的是谷子,也有的是碾房。可他又想到大老远的,怕儿子劳累着,就没明着说。
我就跟我妈说了这个想法。我妈说:“莫非就下马峪有谷子,哪个村没有个谷子?”这一下又提醒了我。
当下我就骑车到了城东。跟曹夫楼村的社员要了十来个谷穗。十来个谷穗不值得上碾子碾,我就往家返。我想到,回家用捣花椒的铁钵子捣就行了。
一进门,我就趴在父亲耳朵跟前说:“爹,我给闹回谷子了。这就能给您做谷面糊糊山药辦。”父亲眼皮张了一下,哼了一声,嘴唇也动了动,好像是在笑。
我妈也弯下腰趴到跟前说:“他爹,你甭圪挤眼,等着啊。孩子给闹回谷子了,我这就给你做。”我妈就说就流泪,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我父亲的脸上。我也哭了,说:“妈,咱们赶快做哇。”
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哭就用手搓谷穗,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放在铁钵里捣。一钵一钵的捣成末末后,又用箩子箩,往下箩谷子面。箩了有二两多。我妈说足够了,我赶快给做,你给往醒喊你爹。
我妈说这话,好像是说我父亲是睡着了,让我往醒叫叫,叫起来吃饭。实际上,我和她心里都清楚,我的父亲已经是不行了。但我妈还是在抓紧着做糊糊.我也是一声又一声地呼喊着他。喊一声“爹”他的嘴动一下,好像是回答我。可他的眼睛不往开睁了,我咋喊说您醒醒睁开眼他都不睁。
当我妈把半碗谷面糊糊山药瓣捧过来时,我把父亲扶起来,让他靠躺在我的怀里。我在他耳朵跟前说:“爹,饭熟了,谷面糊糊山药瓣。爹您醒醒,谷面糊糊山药瓣。”他一下子把眼睁开了,看碗。嘴一动,好像是要说话。可猛的,他的头垂了下来。
(摘自《曹乃谦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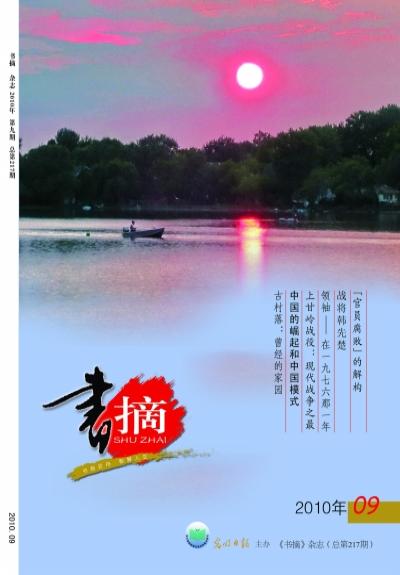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