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观光旅游而言,人们走出家门,把自己扔向什么地方,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准则:哪儿陌生——陌生到全然无知;哪儿熟悉——熟悉到常常在梦里相见,那就是该去的地方。
陌生好理解,无非是填充猎奇、探秘的心理。拉大与习惯了的事物之间的反差。而熟悉则深刻、复杂得多,大抵近乎于心灵感应的寻梦,完全是前人、高人、异人早已描绘、锁定好的,等自己活到一定岁月,才觉得那些被描绘、被锁定的,是活出了滋味,脱了俗,成了仙的心悟,是世间最好的去处。于是,也就依着“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的古训,匆匆忙忙地上路了。东边的向西而去,去闯春风不度的玉门关;西边的朝东而来,来看洪波涌起的沧海。
但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天子脚下的京城,还是旧时帝都的西安、开封,乃至大多生活在北纬33°以北的人们,但得空闲,总会不约而同地涌向灯红酒绿的秦淮,以及香风弱柳的苏杭。究其原因,据说全是因为亚热带的气候闹的,使得淮河、汉水、洞庭、鄱阳一年四季总是湿漉漉的,像缠绵的思绪,委婉的柔肠,这样的地方自然讨得北人的欢喜。他们在那里滋润肌肤,浸泡情感,享受在北方时难得的朦胧与细腻。至于那些已经逝者如斯的文人墨客,爱江南更是爱得痴迷,爱得贪婪,爱得那么有道理。小桥流水,斜风细雨;轻舟画舫,粉楼佳人,无一不令他们陶醉、销魂,简直到了一旦驻足,便忘乎所以,懒得思归的地步。伫水边、立城头、拜野寺、弄扁舟,饮残酒、倚栏杆、拥粉黛、卧花丛,不经意间,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奇辞艳句,也留下了梦里的似曾相识,这样的地方不去才怪。
“江南人。江北人。一夜春风两样情。”黄河以北则是另一番景象,关山、大漠,朔风、飞雪、枯草、寒鸦、荒村、冷月,遍地是粗犷,处处有狼烟,因此也就有了粗声大嗓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北国风光”虽也是风光,但从流向上看,好像南人刻意北上游历的远不如北人南下的火热。这种现象解释起来很是有些费劲。
如果“寻花问柳”被看做是一句好话,人们自然更乐意亲近莺飞草长的江南。那里有醉人的美景,更有诱人的繁华,而富裕起来的人们不但需要美景,也需要挥金的快感。而向北、向西一路走去,因为难见这般光景,自然也就难有一副好心情。他们会感到空旷、遥远,会感到萧条、暗淡。那点好不容易被现代文明激发出来的亢奋得不到释放。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环境实在是不去也罢。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过了头的繁华,恰如美人的浓妆艳抹,矫揉造作,油腻之余,令人无福消受,甚至唯恐避之不及。而一时的贫穷落后虽不能说是什么好事,却也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否则不会有尘封已久的古朴、真实,不会有散落、存活的历史。
如此看来,燕、赵、秦、晋,虽不及江南之灿烂,却也无“过腻”之忧,反而恰恰应了陈年老酿,古韵犹存的味道,多了些苍凉和质朴。
尖刻一点说,这样的去处,本也不是留给好戏耍喧闹、逐轻裘肥马的轻浮之人的,应该接纳的,是那些经风见雨,饱尝人世冷暖,寄情于天地之间的异人侠客。任他们去探究、去凭吊、去畅想、去构架自己内心世界的金字塔。
抑或是不付出这般“有意义”的辛劳,就算是“没有意义”的惬意消磨、漱心颐养,也该是留给这样的人的。
在太行、吕梁山区,像这种完全用石板、石块垒起来的“石屋”至今还随处可见。它们得以存在的理由不完全是因为贫困与落后,还有客观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原因。靠山吃山,石材遍地都是。造一栋石屋用不了多少花销,而且坚固耐用,冬暖夏凉,住在里面舒坦,安逸。甚至一些“富裕”到城里的人,也常常怀念它的长处,隔三差五地回到老屋住住,说是“接接地气,养人”。
实物的审美价值有时候展现得很偶然。像这座石屋,无论是远眺还是近取,它都会给你一种强劲的冲击力。然而你却很难在它身上找到能与你印象中的“屋”的概念相吻合的东西。在它面前,原本习惯了的点、线、面,习惯了的整体形象,都变得虚化起来。凸显出来的,不过是材料、色块、结构这样的元素,是可触摸到的强烈的质感。但因此我们就说它是超现实主义的,似乎又很牵强,可以试想,当初山民营造它,全部的出发点也只是栖身,抑或在设计中有传统、风俗的要素,也断不会生出这个风格,那个主义。这就为我们诠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感觉,在现实中总会找到产生这种感觉的因素。
这是一座两进院的里院,引路的主人说,院中的石榴树有着同这座宅子一样的年纪,三百多岁。
就树木在宅院中的意义而言,中外的理念没有多大区别,无非是追求与自然的亲近,使小天地多几分情趣。但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人口外来的多,城市出现的晚,所以至今还常常是瞄准了自然景观,开垦出一片住处去造屋,于是大大小小的树木也就划进了自己的院子。相比之下我们市井的形成却久远多了。
“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人们,几乎完全是先盖房子后种树,因此栽种什么,不但入了流俗,也有了规格,甚至戒律。譬如不可有松,认为那是庙宇用物,或阴宅之象;不宜有柳,是因其袅娜而有伤家风;不宜有梨,则因“离”大失和气。至于文人调侃,更是恣情妄议,虽不成机理,却颇为成趣。像“院中无槐。则如家中无主人,而无丁香,犹如房中无小妾”之说,更是将树木与庭院的关系人文化到了极致。再后来,任什么庭院,几乎无一例外地排斥杨树,认为它过分健硕、粗壮的腰身,实在难与祖宗倡导的儒雅遗风相匹配。
石榴。根系深穷,树干苍劲,其中犹结果多子象征昌盛、吉利,因此大凡庭院无不视之为必有之物。当然,还有象征富贵、雍容的海棠和玉兰。
不过,“种蕉邀雨,植柳邀蝉”也是一说。
看着两位闲适的老太太,想起发生在上世纪8 0年代前后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另一个是罗中立先生创作的“丑化农民”的油画《父亲》,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交相呼应,以各自的艺术魅力刺激着人们的感官,颠覆着人们习惯了的审美心态。这印证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变革需要两个方向的力量,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催化与侵袭,一个是自我的反思与批判。
那时,我一路南下,跑了四十几个县,一路上见到的“父亲”们,愁苦与渴望的面容依旧稳固地存在着,但已似有溶化的光亮。如今25年过去了,油画中那只直举到你面前的残破而硕大的空碗、那对充满了不甘和绝望的眼神以及那双养育了我们的粗糙的大手,都还记得吗?
老姐儿俩一个八十一,一个八十三。
在大部分农村,作为一种刚刚过时的劳动生产工具,石碾子已经派不上多大的用场了。倒是玩“形象思维”的人常常特“蒙太奇”地想到它,譬如伟人们推动着它——沉重的历史车轮滑动了;而在穷苦人面前,它又成了不堪重负的苦难命运的象征,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一段“咏叹调”,就是推着碾子唱的。再就是聪明的景观设计者,为了迎合都市群体的怀旧情怀,营造出一块老年间的田园光景,也断不了借用它的“小生产者”形象弄巧。
在庭院里、在店铺前,置上一尊石碾子,“疑似”出农家乐的感觉。
其实有些上了年纪的庄稼人还在时不时地用着它,说现代化了的电磨转动起来太热,磨出来的粮食烫手,和出的面黏,不劲道,不好吃。
而对饮食文化有研究的人说,重要的是石头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粮食跟它们化合起来才别有一番味道——这又回到了那个命题: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在于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方式。饺子得手包,面条得擀面杖擀,豆腐得经石磨磨,再用卤水点。而车间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叫“快餐”。
几乎是以龙王庙为圆心,以山坡为半径,从碛口古镇向东逆时针地划半个圆的那个点上,就是古镇晋商“家属区”之一的西湾——另一处是三公里外的李家山。
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城镇不同,碛口的商业活动和它带来的繁荣,完全依赖于商品的集散和旱路与水路的转运。晋商聪明、也更谨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一手创造的繁华与喧嚣,一方面则小心翼翼地庇护着自己的家眷,不让他们靠近花团锦绣掩盖下的是非、凶险。当然他们也更会生活,更懂得条理,一旦从黄白算计,敷衍应酬中脱身,自然就可望一片“小楼容我静,大地任人忙”的净土,一座“一帘花雨,半榻茶烟”的宅院。闲适中慵懒地哼几句梆子,吃一碗婆姨亲手擀的面条,于是有了这不远不近的“家属区”——西湾。
西湾距碛口虽然近得不能再近,但却没有像碛口那样急切地改变自己,不知道是不愿意改变,还是少了碛口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总之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由破败了的老宅、窑洞、石阶、照壁、过街楼组合成的构图中,有两件东西很发人深思。一是老宅门楼上字迹清晰可见的牌匾,二是环绕着整个村子,但如果没人指点,你怎么也不会发现的那条围堡的根基。
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命运却迥然不同。这种现象的后面,有着复杂的成因。
像别的地方的情况一样,那些设计精良、做工细腻的老宅,不要说明、清两代和民国,单就近五十年间就至少有过三次变迁: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二是“文革”中无序的“再分配”,三是“改革”初期,出于各种目的被变相租赁、买卖。就是说,这些老宅的原房主已经几易其人,那些诸如“树德”、“德行聚”、“神社”、“诒燕”之类的牌匾已经跟院落的主人失去了家风、荣誉传承的关联,它们的“健在”,更多的是得益于古典建筑本身的价值和个人对私有财产(或使用权)的维护。而与它们的历史一样久远的围墙却不然,他们不属于任何的个人,算是“公家”的东西。在种姓、家族的生活、生产联系日趋松散,安全的概念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它们的存在已经变得没有意义。至于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似乎得等到它们行将消失或完全消失的那一刻去体现了,而这正是文物价值中的遗憾。
缤纷几许,苍凉无数。今人想古事,缘何总是太多的惆怅与凄凉?
虽然土坯已经脱落、坍塌了,但筋骨还在,整体的美感还在。石阶、门墩儿、门楼,一砖一瓦,在摇曳的蒿草的渲染下,空落中透着几分凋败之气。
建筑是可用来感悟文化、品味人生的。英国人阿兰·德波顿在他的《幸福的建筑》中,对一幅1937年巴黎博览会的德国馆的照片是这样描述的:“材料和颜色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幢建筑的立面就自然可以讲述一个国家该如何统治,其外交政策该取何种原则了。政治以及道德理念完全可以写入窗框和门把手……”自然,这位英国人的议论有些玄虚,不无生硬的象征主义之嫌,但建筑风格的时代性,真是被他细化得惟妙惟肖,让你不得不相信那窗框、门把手里还真隐藏着“大德意志”的元素,弥漫着那时已经甚嚣尘上的纳粹味道。
这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庭院呢?它没有古罗马的神秘,也没有哥特式建筑。“高耸向天”的宗教意味,它只是虔诚地拥抱着大地,与人间自然、和谐地融合着。
就凭在这近70°的山坡上鼓捣出如此严谨有序的村落,你就不得不佩服山西人的韧性,不得不为晋商近于怪异的奇思妙想称绝。至于说李家山是谁谁发现的,接着又如何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看重,实在已经无关紧要。倒是这淹没在黄土高坡上的“立体式建筑群”至今还完整地存在着,而不是“风骨不在,神韵犹存”这一事实,值得人们庆幸和珍惜。由此我联想到,当年李家山的先人,不但精准地相中了这里的风水,也一定瞄上了交通不便这一“优越”条件。
果然,虽旷日持久,却没人能撼动它——因为外边的人很少知道它,知道了也不容易接近它——所以我倒担心起它今天的抛头露面,一层芳容,担心现世的风尘缤纷摇落,红绿散乱,玷污了它的旧貌陈风。
站在李家山的“这一个”面前,懵地想起了北京门头沟山坳里的“那一个”——爨底下,相距近千里,呈现出的基因竟是如此相似。
在碛口繁华的岁月里,银子像黄河的水一样流进了晋商的口袋。于是不善挥霍的他们,将置办家产当成了一件正经而体面的事业,于是像西湾、李家山这样的“家属区”出现了。然而问题是,何以要将家“藏”到如此险要、隔绝的地方呢?我想,较为妥当的答案应该是:将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财富,尽最大可能地遮掩、封闭起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外来人接触起来越难越好。门头沟的爨底下和碛口的李家山——当然还有更多的选址有一个共同点:险要,且易守难攻,只有符合这一点,日子才过得安稳,心里才踏实,才更契合他们恪守的生存观念。至于因此而给自己带来的诸多不便,那正是心甘情愿的“偷偷乐”的事。
对山西人而言,“不露富”,是持家立业的优秀品质,对于这一点,不是山西人你很难理解。你其实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始终精明而谨慎、勤劳而坚韧、内敛而恐惧着,或许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解释李家山和爨底下的奇妙。
然而眼下谁都知道,不少有了钱的山西人已经抛弃了藏着、掖着的传统,不再惧怕露富,开始享受“大奔”、“悍马”的张扬与奔放了。
(摘自《川间峁上的沉思——古村落 古戏台 古围堡》,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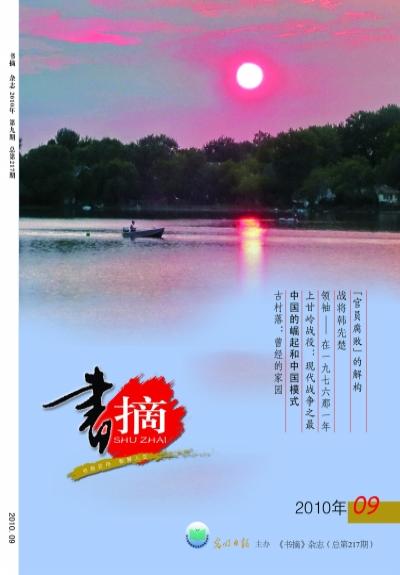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