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桌圆坐不可以
北京东部临近机场的郊区,有一所京西学校,是一所驻北京的外国人的子弟学校。我曾参观过,并在其教师餐厅吃过饭。餐厅中有许多方桌,桌子有四个边,每边刚好坐一个人。中午,外籍教师们陆续进入,男老师们坐在一起,女老师们也另坐在一起。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坐这样的桌子,最多就坐四个人,每人把住一边,第五个人就“坐不进去了”,难道能让自己坐在犄角上吗?那样吃饭不方便,同时也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可这些西方教师无所谓,五六个人围坐着一张方桌,说说笑笑,很是高兴。也就在这时,我妻子从欧洲回来,带回一些照片,其中也有这样在方桌子四面“圆”着坐的情况。在中国,如果有五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吃饭或开会,就一定要选择一张圆桌,否则就真没法坐了。这在中国是一种自古传下来的规矩,生活中有这种规矩,到了京剧舞台上就更有这种规矩了。不懂这些规矩就没法看懂京剧。
京剧舞台没有圆桌而只有方桌,而且必须是条形的方桌。四面的方桌可以用来吃饭或开会,京剧虽然也会表达这些事情,但至少得空余下一面,为的是不遮挡观众的视线。条形的方桌如果只坐一个人,那他可以坐在桌子后,也可以坐在桌子前,但都得正对着观众;如果是两个人,可以一边坐一位;如果是三个人,桌子后边坐一位,另两位一边一个,但都得脸朝观众。
舞台上的桌子除了作为“桌子”之外,还可以当成“桥”、“房顶”、“山顶”、“空中”。桌子两边各放一把椅子,演员就踩着这把椅子站到桌子上,可以一站许久,或唱或念,可以自我抒情,也可以与站在桌子前的人相互问答,这样就有了高低之分。
桌子有时还可以摆在上场门或下场门的前边,斜着摆,可以在桌子上头再摆桌子,三层桌子够高了吧?但往往还只是一间房屋的高度,而摆在舞台中间接近天幕的那张桌子,往往就能代表一座高山,甚至衬托出云雾缭绕的缥缈场景。这是艺术上的道理,您得慢慢习惯它,进而承认它。如果一开始就拒绝,那您就没办法进入京剧最美妙的境界了。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假定性嘛。
京剧舞台上没有圆桌,但坐在桌子边(或站在桌子上)的演员,一切动作却非常需要“圆”。这“圆”的要求很难一时就给您讲清楚,但它往往是通过动作的左右、高低、正斜、轻重等对立关系来形成的。您弄不懂也没关系,我这里是借机先铺垫一下,后边再仔细讲。
东西南北各不同
中国面积很大,有很多省份或城市,住在其中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东西南北:自己这个省的东西南北分别是其他的哪个省,自己以及亲人、单位之间在东西南北的位置又是如何。京剧,就像中国版图上的一位历史老人,对自己舞台上的东西南北也非常注意。
京剧剧目主要是叙说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其中涉及的东西南北非常杂乱。但具体到每出特定的戏,在处理东西南北上的办法又非常高明。它把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分解为许多片段,分成十几甚至二十几场。有些是大场,有些是小场;刚刚还在北方,忽然又去了南方。但无论怎样变更,每一场的那个平面,都是背“北”朝“南”,更是这样直对着观众的。观众永远坐在舞台之南,他们仰起头来,观看着北边舞台上悲欢离合的故事。过去的老式舞台,通常高于观众视线;现在新建的舞台,往往提高了观众座位,让观众居高临下去看戏剧人物如何展开故事。这样,观众始终坐稳了不动,把历史故事编成“连环画”,一页一页“翻”开了欣赏。
中国戏剧故事中的人物,都要按照中国的习惯去占据好自己的东西南北。在这四个方向中,最重要的是北方。任何重要的人物,一出场必然要站在中央贴近北方的位置,要面对着南边的观众说话做事。这既是对观众的重视,也是把自己的威严施加在观众头上。比如一开场时上来的是大将军,他要带队出征,于是他站在北边天幕最中央的位置发号施令;忽然,皇帝上场给大将军送行,于是皇帝站到了最中央,而大将军侧移到一旁,随时向皇帝报告并表示感谢。请注意:舞台上的东西,与观众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相反的。舞台上总是北在正面,东在出场门一方,西在下场门一方。所有人物总是由东边出场,再由西边下场,由东向西,这是一个滚滚的潮流,既是人物的流,也是事件与矛盾的流,由剧情的开始一直要流到终结。观众始终坐在南边,仰看那些戏剧人物如何演绎自己的悲欢离合。人物的地位有高有低,高的如皇帝,低的是平民,但最感动观众的戏剧人物才是主要角色。这样的主要角色永远是高高在上的,永远是能感动观众的。北,由此就变成最尊贵的方向。南,作为北的对立面,也就成为卑微的随从。所以,历来的帝王都喜欢立足于“中”,背靠着北方的坚固屏障向南瞻望,然后发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呼喊。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上,皇帝宝座的北边是一座厚重的屏风,屏风后边是高大的景山,景山后边则是雄伟的万里长城。皇帝眼睛向南看,或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目之所及都是他的臣民。但到了舞台上,就只能由东向西,为的是让帝王看着明白,也让观众看着明白。观众花钱进入剧场,也要遵从这个自古就形成的规矩。在这一刻,观众是在规矩中释放自己的满意与欣喜。
上场前的咳嗽
《群英会》第一场周瑜坐帐,要中军请鲁大夫进帐。中军走到台口:“鲁大夫进帐!”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看这出戏,是由谭富英扮演鲁肃。他在幕后一声咳嗽:“嗯哼。”台前立刻一阵掌声。随后鲁肃上场,自然又是掌声。鲁肃见过周瑜,周要鲁代传一言,请诸葛先生上场。鲁肃走到台口:“有请诸葛先生!”扮演诸葛亮的是马连良,他在幕后一声咳嗽:“嗯哼。”台前又是一阵掌声。随后马连良上场,掌声更加热烈……
试问这许多人物自何处而来?这问题曾难倒了许多人。曾有人这样回答:“从其出处而来。”这不是废话吗?可这出处又究竟在何处?比如鲁肃这样的官职,需要在帐外等候周瑜特意传点?诸葛亮是在馆驿歇息,能够听得见鲁肃在帐外这一声“有请”?如果您是位没经验的观众,尽可以为这个或那个人物,想出诸多的出处。但无论是哪一个,您又不好强迫别人就一定得听您的。所以,一个初步的回答可以是“无”,因为您实在弄不清他准确的出处,所以就只好是“无”了。但谭先生与马先生。凭着他们的经验与技能,逐渐让没经验的观众变成有经验的观众,于是那“无”也就慢慢变成了“有”。谭富英幕后咳嗽,观众立刻知道,谭先生站在侧幕旁边呢!随后马先生一咳嗽,想必马先生也站在侧幕旁边呢!等到谭、马穿着戏装陆续上场,他们立刻是他们扮演的人物了,观众踏实下来,都立刻进“戏”了。如果下一次还看这一出戏,如果还是他们二位主演,那么观众从幕后第一声咳嗽开始,大约就能看见他们的扮相了。所以说,这一声声的咳嗽,不仅仅是来自台后的一个信号,更是著名演员给观众带来的一种受欢迎的心象。
讲腰身却不看“三围”
对舞台上的男性,要看他腰腿功夫如何;对于女性,也要看她的身腰是否苗条。但作为古典京剧,在这一点上并不苛求,因为任何人物都要穿上厚厚的衣服或盔甲,至于他真正的体形如何,是无法也无须去查验的。扭着腰肢几乎裸体走在T型台的模特,与京剧舞台上的女性,完全是两码事。梅兰芳年轻时演过《太真外传》中的“入浴”,表现杨贵妃脱掉外边的衣服在华清池中洗澡。古典艺术也可以演出“脱衣舞”,一边款款地唱,一边分层脱掉衣服。古典女性穿得多,所以完全可以唱一句脱一层,梅兰芳表演时从容不迫,把人物入浴前或入浴中的种种情思表达得准确而优美。
古典京剧全部由男性演员表演,由于物质条件简陋,更由于众多男性演员多少代积累下的经验,不再以追求表面的女性身姿为目标,而是通过各种功法去表现女性之美。不采取写实主义,更不采取琐屑的自然主义,而让扮演女性的男性演员穿上厚厚的衣服,把“三围”严密地遮挡起来。他们表现的则是她们——在舞台上结合剧情的需要,展开各种舞台功法,其中不少是高难度的,是女性演员所难以学到的。比如舞台女性的各种指法,各种台步,各种水袖,同时又要有向前向后的各种屈腰。如果说运用与掌握各种技巧还在其次,那么更重要的则是对各种功法的选择与创造。请注意:在旧时的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体,女性大多不离开自己家门,因此女性在认识外部社会上有很大的局限。正是这一点使得女性演员演不过男性演员。今天,女性演员可以摆脱小家庭的束缚,从广泛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女性。但当她们结婚与生育之后,艺术生命往往远不如男性演员悠久。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已基本摒弃了男性演员扮演女性角色的传统,而以女性演员直接去扮演女性人物了。但她们在戏曲学校当中所学习的技巧,却还是旧时代“以男扮女”的那一套。梅兰芳中年时曾收过一位条件很好的女弟子杜近芳,上世纪50年代她是中国京剧院的著名旦行演员。她就曾很敏感地说过:“我过去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先学了一套男性演女性的技巧,然后让我这个女性用用他们男性的技巧,去扮演我们女性。我努力研究以我们女性扮演女性的技巧,一旦研究成了,直接拿上舞台有多好。至于那些男性演女性的技巧,我也是努力去学,其中能用的我就用了,不能用的我学过来‘存放’在衣服口袋中,等有机会时再说……”
这番话,是20年前我采访时她对我亲口所说,非常有见地,也非常可贵。京剧毕竟是一种延续了200年的剧种,想从根本上改变表演思路及技巧,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真沿着杜近芳的设想再走上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或许这套办法就能成熟。如果仅仅有一代人的自觉,那么还远远不够,一旦运用起来就势必与已往的传统“打架”。真要那样了,京剧自身功法也就不再纯粹了。
印匣中的秘密
京剧舞台上常用印匣,常常是新官上任,旧官捧着印匣出来迎接。旧官站在上方,高举印匣,新官下跪,拜印如同拜君。然后是印匣的交接,新官就此上任,旧官卸任而去。一场权力的变更,也就此结束。梅兰芳扮演女性,其中就有元帅角色。元帅也是有印匣的。出征之际,元帅为何总是威风凛凛?原因之一就在于身旁高擎这方印匣。它只是一个用黄绸子包裹着的六面体,却代表着王权。有了它,就能够调动军队,能够指挥千军万马。
梅兰芳在1958年排演的新戏《穆桂英挂帅》当中,也动用了印匣。在她正愁闷之际,宋王朝把印匣送来,要她率领宋王朝的将士出征北国。这肯定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回想起丈夫一家满门忠烈,宋王朝从来不闻不问,只有等到如今朝廷危急之时,才又想到要用杨家将了。这印匣能接吗?不能。不能!但佘太君的态度是鲜明的:“一事当前,以国家社稷为重。你实在不肯挂帅,就让我这个百岁之人挂帅!”真是掷地有声的言语。穆桂英内心矛盾了,她拿起印匣,擎举在手里,左走走,右看看,心中情绪激荡。梅兰芳在表现上述过程中,恰切地运用了哑剧舞蹈,没有一句唱,也没有一句念,就靠水袖的翻飞,就靠步伐的移动。梅兰芳以其独到的艺术手段,把“这一个”穆桂英演活了。观众很惊奇地发现,这一方印匣的六个面都很光滑,也没个把手去抓,梅先生是怎么把它擎举得如此平稳?至于剧团中的晚辈,惊叹佩服之余,也没人去思索。因为他是梅兰芳嘛!梅兰芳的演出,自然就应该出神入化嘛!唯独来到“文革”,造反派就敢怀疑梅兰芳了,他们心想梅兰芳虽然已经去世,但威信还在,尤其是《挂帅》当中的这方印匣,给我们批倒他带来多少阻拦!他们终于抄到这方印匣,使劲晃了晃,发现里边有响动!莫非其中藏了什么机关?他们找来一个大榔头,高高举起,重重砸下,印匣粉碎了,从中滚出一颗生了锈的铆钉!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再也想不到梅兰芳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会想出这么简单的方法去保持印匣的平衡!
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人纪念梅兰芳,也经常缅怀到这个举动。是的,凡是有大智慧的人,经常又是非常朴素的。
“悠闲了”才能成大器
艺术有忙的时候,也有闲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由忙到闲。初期,这一批艺人要生活,要赶场,整月整年忙忙碌碌,奔波不停,等这门艺术大抵确立了,等它在社会大市场上也有了地位,这批艺人就比较幸运了。而看它的人对之也比较关注了,甚至要代替艺人去设身处地想一想这门艺术的发展前途,并且运用自己的力量(也包括美学观点)去影响这门艺术了。京剧自从由城乡结合部进入城市之后,就遇到了这种命运。最初是被动与不自觉的,后来就变成主动与自觉的了。
京剧的出现,正好赶上了一个“空白”。在它出现之前,剧坛还没有在艺术上超过它的剧种。京剧的前身有好几个:徽剧、汉戏、昆曲以及其他,这些剧种都相对简单,哪个也不具备后来京剧的那种综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剧真是横空出世了。而城市人及皇朝也都有足够的悠闲,喜欢更愿意帮助京剧变成让自己更加悠闲的一个剧种。于是,戏园子中在膝盖上叩着节拍的戏迷出现了,在大街上旁观富连成小学员排队行走的戏迷出现了,大批涌上街头观看谭鑫培、杨小楼出殡的闲人出现了,甚至连西太后在其优游养生的颐和园中,也不时召集最优秀的艺人成为“内廷供奉”。是全社会的努力,再加上艺人自己的用心,让京剧与中国传统文化挂上了钩,在各方面都逐渐讲究起来。京剧不再将就了,它要求自己讲究了,只有讲究了,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价值。梅兰芳演出的早期,l916年开始的18个月当中,他排演了四类不同性质的剧目,这应该是他最忙的时候了。可后来他成了很大的名,他变成了梅博士,变成了全中国人民引以为骄傲的艺术权威,他生活才安定下来,每分每秒的意义才更明确下来。他越是闲了,其艺术生命的价值也才越发显现出来。
忙的艺术,尽管可能会一时大红大紫,但最终不免衰落低迷。而只有由忙转闲了的艺术,才能逐渐增加其古典性,才能长踞历史长河中的一隅,成为所在国家、地域、民族的象征。回想地球上的这些国家,最初的文明是从哪儿来的?那些忙的艺术可能帮助过国家之间的迁徙、建设与战争,当这些兴亡之事慢慢淡漠了之后,地球上的秩序相对稳定下来,人们需要更多的欢娱——艺术来到这时,也就有了由忙转闲的可能。目前,一些急需在经济上起飞的国家,往往注重艺术的忙,而经济已然腾飞,社会需要在深层次上稳定的国度,则需要艺术的由忙转闲。我希望,由忙转闲,由将就变讲究的艺术,能够早一些在我们国家出现。
(摘自《京剧下午茶》,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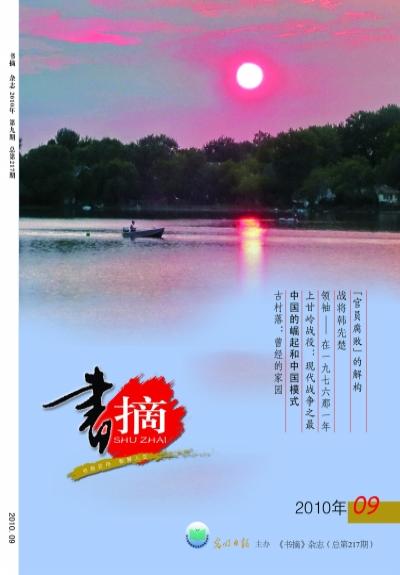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