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进筒子楼是1967年春,那是19楼中文系男教员单身宿舍。房间十平米大小,两人一间,单人床、二屉桌、五层木书架,每人一套相同的家具,人人埋头书本,楼道里非常安静,以至于我的出没会引人注意。周日我常骑自行车从定福庄广播学院到19楼会赵祖谟,那时他和陈绍鹏同屋。我们结婚在44楼招待所,还是筒子楼,一张四屉方书桌靠墙,三面围放三张食堂里用的条凳,从l9楼借来两个暖壶和几只玻璃杯,桌上放着水果糖,上面悬着25瓦光秃秃的电灯泡,床上一新一旧两床被子,一对有芯无套的棉花枕头,各盖着一浅蓝一浅绿的枕巾,上面印着硕大的粉红牡丹花,我说,这枕巾不是一色的,赵祖谟才发现,我真希望他是色盲而不是粗心。傍晚,由林庚先生、王瑶先生等五六位不能参加“拉练”的留守人员,带着一套马恩选集前来祝贺,那是1970年12月底。
10年两地期间,我每年冬天从青海德令哈由公路而铁路大约用七天奔波而来,在19楼首先遇见的是郭锡良老师,他腋下夹着红绸面的小被窝卷,笑眯眯跟我相向而行,他在为我“腾地方”。后来我成了他的学生,郭老师教我们汉语史课。
住筒子楼时代,大家生活都很简朴,我们都没有户口本(集体户口),因而就没有北京市民能享受的鸡蛋、白糖等副食供应,基本上吃食堂。每月由一人领取全楼道人的粮票,然后按定量分发,大家轮流执行;因为没有私人摆设,大家都使用相同模样的公家家具——木床、书桌、书架;又因为“阶级斗争天天讲”,倒使得人人地位平等,原来的“老师辈”、“学生辈”浑然不分了,这给我们带来了相互间更多的了解和交流。这里像是一个大家庭。晚饭后几乎全楼道的人都集中到一间公共电视室,看新闻节目。每天两顿饭的时候,大家在楼道里边吃边随便闲聊。金申熊老师周日的常客是中华书局的沈玉成先生,他从城里来跟金老师吃开水烫蚶子。我家来了山西客人,我的对门邻居张钟老师就不声不响地把醋瓶放在我的门外小桌上;一天晚上我怪赵祖谟不给我借书看发生龃龉,第二天早上张钟老师就递给我两张他的借书卡,让我自己去借书。忽然有女同志帮商金林打扫房间,哦,原来他要结婚了。看了电影《甲午风云》,张宏翼在楼道里感叹:“‘文革’前还有这么好的作品?”我明白了为什么工农兵学员出身的人会“跟”得那么紧,他们生活在文化断层之中。王若江、李晓琪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去“五四操场”念外语,也让我了解了他们海绵吸水般的对知识的渴求。但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楼道里异常压抑和沉闷。一天中午,张钟老师小声对我说:“天安门那场面真壮观呐!”然后转身回屋了,他知道我一直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那一刻我们的心是那么的相通!张卫东曾在房间里跟一些同事议论过天安门事件,包括我和老赵在内,不幸被人告发了,当时的系领导和工宣队负责人找他谈话,让他承认错误并且揭发别人,他只坦言自己说过反对当局做法之类的话,但拒绝揭发任何人。由此,当年还是“小字辈”的他,在大伙心中威信陡增,后被选入总支委员。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刘丽川选择了去深圳大学,临行时前去告别的人一拨接一拨。
金申熊老师1981年以前一直两地生活,夫人屈育德老师上世纪70年代后期曾被借调到位于沙滩的文物出版社工作。她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背着一网兜菜。初冬的一天,她去学生合作社(现在是新华书店北边的一片绿地)买橘子,回来时走在楼道里气哼哼地说,“售货员给我的净是烂的,我说,你们自己买就不是这样了。售货员却理直气壮地批评我:你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哼,真是气死人了。我要是七仙女,我才不下凡呢!”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跟“真理”绑在一起。但身材瘦小、温柔敦厚、又属于“臭老九”的屈育德老师,那么智慧地发泄了她的怨恨,她的语言让我顿时感受到中国民间文学那永恒的生命力!金老师对她宽慰说:“我在哪儿都是孙子,上课是学生的孙子,上车是售票员的孙子,上商店是售货员的孙子。”其实那年头,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无奈。在19楼金老师住我斜对面,到21楼他住我右隔壁,那时屈育德老师已经带着女儿调入北大了,他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那是两张27公分宽的学生床拼在一起的。唯一的书桌属于女儿舒年,她就要参加高考了,屈老师趴在床沿备课,金老师则坐在马扎上,两脚伸出门外,抱着案板做学问。他多次在言语之间表达了他在最受挫折的时候,游国恩先生给予他的恩情,他也用他恩师的行为方式对待我这样的后生。文学史课上,他嘱咐我们,要记住著名作家的室名谥号,他那“书名卡片要查司马温公集而不是司马光集”的声音至今还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他生动流畅的语言、潇洒飘逸的板书,是每个学生的享受。他逐字逐句地给我修改古汉语作业《报任安书》翻译,他鼓励我在一定时候要动手写文章,他告诫我要好好利用图书馆,日后我熟悉了图书馆北大、燕大、中德、中法等藏书,甚而“未编书”,确实从北大图书馆受惠无穷。让我最后悔不及的是,金老师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鼓励我练习书法,“将来要写草书,写狂草”,他说。但我当时却很冬烘,没有利用那段宝贵时间,直到退休才开始上书法班,如今我遇到草书难题,想想金老师的话,心想不能一个错误犯两次,尽管我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与书法家对话,但我鼓起勇气,在吴小如先生精神尚好的时候,冒昧地去请教了“书谱”,可惜先生只能“点拨”不能细讲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空前的大地震。大约震后的第四天,张剑福的妻子张桂莲从唐山钢铁厂宿舍废墟中爬出来,幸运地搭上一辆厂里的大汽车,艰难地回了北京,一到19楼就直接上三楼奔我们家。张剑福当时在大兴干校劳动,一周回来一次。桂莲衣衫不整,脸色惨白,表情呆滞,语言迟缓,一见到我们,泪水砉然而下。骤然间我们家挤了好多人,听桂莲讲述那可怕的经历,有的要支援饭票,有的要支援钱,有的为她打饭,那一晚张剑福没能赶回来,幸亏有这么温暖的筒子楼。
筒子楼里除了埋头于书本之外还有乐声,每天晚饭后“晚自习”前,石安石老师悠扬的二胡声总会在楼道里回旋,裘锡圭老师在盥洗室一边洗衣一边旁若无人、字正腔圆地放声高唱样板戏,不满意的句子会反复重唱,这种“艺术”只有筒子楼的居民才能享受得到,也让人难以忘怀。
赵祖谟告诉我,在那不能读专业书的年代,裘锡圭老师把64开本的《新华字典》背下来了,连蹲坑都《新华字典》不离手。朱德熙先生曾对老赵这些中年人说:在你们同辈人中,裘锡圭是书读得最多的。文字学课上,裘老师写古文字的板书跟写简化字的速度一样快,我上他的课,笔记总也跟不上趟。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职称评定,裘老师被第一批由助教擢升为副教授,据说他的业务水平受到郭沫若先生的嘉许。
石安石老师出身不好。赵祖谟告诉我,“文革”中,系总支副书记找他谈话,警告他不许外出串联,他第二天就背着书包串联去了。晚年他得了癌症,仍然坚持上课,他跟学生的关系特别好。在凛冽的寒冬,那么多学生前去肿瘤医院为他送别,那场面对一般教员来说是少有的。他的超乎一般的自尊和顽强,让我深深地佩服。
倪其心老师由于对先秦两汉文学史的精熟及其那了得的注疏功夫而成为么书仪的“备问”。一次我考试后回到楼里,倪老师在楼道碰到我,问:考的什么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给这首诗标韵脚”,我答。他立即告我:仄声韵。他不仅指点我学问,还蹬三轮车到海淀西大街家具店帮我拉回来小衣柜。倪其心老师的婚事,是大家都关注的大事。听说他跟石家庄的一位上海姑娘谈恋爱,大伙纷纷为他出主意,有的让他搞好个人卫生,有的让他千万别端架子,他风趣地回答:我百分百投降还不行吗。他终于娶回了姚诚,后来又添了倪猴(申年出生的,我们都这样叫他),大家都深深地祝福他。
上回炉班的时候我读的是语言专业,我对自己的国际音标没把握,在赵祖谟建议下我去请教徐通锵老师。在筒子楼徐老师一直跟王福堂老师住同屋,当我找上门的时候,徐老师欣然接受了我这个学生。后来我对近代西学东渐史发生兴趣,遇到来华传教士早期使用的汉语记音符号,我从未见过,就去畅春园请教徐老师,他耐心地给我讲解。一次,徐老师为我解惑以后嘱咐我:“文章写好以后,起码放半年再修改。”回家后我反复琢磨徐老师的话,豁然明白为什么以前写完文章反复修改,颠来倒去,自己总也不满意,放上半年,有新的积累,思维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不急于出手,沉下心来,才会有更成熟的思考。这是徐老师给予我的莫大财富!
今天,当我坐下来回忆往昔筒子楼的时候,我无比珍惜那谈笑有鸿儒的集体生活,中文系的学术传统蕴藏于斯。
(摘自《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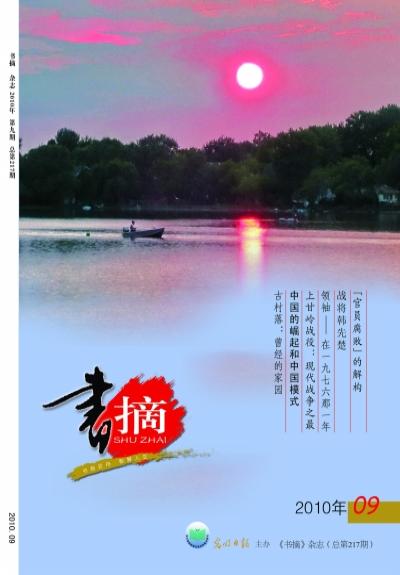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