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出生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对他简直就是灾难,但差生遇上了教导有方的恩师,使他最终完成了学业并当上了教师和作家。
一位法语老师
我上二年级。
他发现了我是怎样一个人:一个真诚的爱编故事的人、高高兴兴的自杀者。
我功课学不会,作业不做,准备的理由却越来越有创造性,对我的这种能力,法语老师无疑十分惊讶,他就决定免掉我的论说文,让我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必须每周写出一章,一个学期内创作出一部小说。题材自由选择,但是要求我提供的稿子没有错别字,“提高批评水平的故事”。(整部小说我全忘记了,但是还记得这句指点的话。)这位教师已经上了年纪,他将一生的最后几年贡献给了我们。他要贴补点退休金,就到巴黎北郊这所私立程度最高的学校。他发现了我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于是心里就想,不管会不会拼写,要让我学习开窍,就必须用讲故事的形式激励我。我满怀激情写这部小说,借助词典,一丝不苟地修改每个词(从那天起,我就词典不离手了),每周交出一章,就像专业的连载小说家那样准时。现在想来,那篇故事一定很悲惨,当时我深受托马斯·哈代的影响。哈代的小说就是由误会酿成灾祸,由灾祸导致无可挽回的悲剧,这特别迎合我对命运的兴趣:从一开始,人就无能为力,这正是我的看法。
我并不认为那一年,我的学习有了实质的进步,无论哪门功课,但是从我上学以来,一位老师破天荒第一遭给了我一种身份。在某个人的眼里,我以学生身份还是存在着,如同一个人要沿着一条线路走下去,而且要坚持到底。显而易见,我对恩人感激涕零。老先生尽管保持一定距离,还是成为我的秘密读物的知情人。
“说说看,佩纳齐奥尼,现在看什么书呢?”
要知道,闲书还是看的。
当时哪里晓得,看闲书会救了我。
那个时期可不像如今,看闲书并不是什么荒唐的壮举。那时看小说,被视为浪费时间,以妨害学习而著称,在我们的学习时间里是禁止的。因此,我有了秘密阅读的爱好:小说包上书皮,好像课本一样,藏在一切可能藏匿的地方,夜晚打着手电阅读,不去做体操,只要我能单独捧着一本书,什么办法都行。正是住校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我需要一个属于我的世界,这便是书的世界。我在家里,主要是看着别人阅读:父亲坐在扶手椅上,一边抽着烟斗,用无名指漫不经心地划着一丝不乱的头发分缝儿,一边在圆锥形的灯罩下,看着放在交叉膝上的一本书。开头阶段我看书,也许仅仅是为了模仿这些姿态,并且探索别种姿势。我看书的时候,身体摆好姿势;处于持续不断的惬意中。问我看什么书吗?安徒生的童话,只为在《丑小鸭》中体会认同感;当然还有大仲马的小说;欣赏那些侠肝义胆、斗剑飞骑的故事情节。还有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精彩小说《古斯泰·贝林》,我不知疲倦,陪伴这位被主教革职的醉醺醺而杰出的牧师,陪伴埃克比庄园其他的骑士,一同经历那种冒险生活。还有《战争与和平》,第一次阅读,看了娜达莎和安德烈王子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就被我压缩成一百来页;第二次阅读是上三年级,看了拿破仑史诗:奥斯特利茨战役、博罗底诺战役、莫斯科大火、从俄罗斯撤退(我曾画过巨幅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图,我秘密绘制的那些小人儿在战场上相互厮杀),顶多有两三百页。上二年级又看了一次,主要是彼尔·别竺豪夫的友谊(另一个丑小鸭,但是别人想不到他懂得那么多事情);最后,到高中毕业班时,通读了整部小说,了解了俄罗斯、库图佐夫这个人物、克劳塞维茨、农业改革以及托尔斯泰。当然也看了狄更斯的小说——奥利佛·退斯特也有我这种需要——艾米莉·勃朗特,她的精神在向我呼救;还有史蒂文森、杰克·伦敦、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赌徒》。就是这样,我在家里能找见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当然还有《丁丁历险记》、《假丫头史比露》、《足迹》以及《鲍伯·莫兰一家》,这些都是那时期风行的读物。我带到学校的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列入教学计划。谁也不会向我提这方面的问题。任何目光也不会从我肩上射过来,读这些文字:我和小说的作者,我们就单独相处。我阅读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在自学成才,不知道这些书唤起我内心的一种欲望,甚至在书中情节忘记之后,而这欲望犹存。少年的这些读物的终结,就是四扇通向世界标志的门,四本不可能再迥异的书:《危险的关系》、《逆向》、罗兰·巴特的《神话集》和佩雷克的《物》,然而,这四本书却在我身上织成紧密的亲缘联系,这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我至今还没搞明白。
我不是个品位高雅的读者。请福楼拜不要见怪,我看书就像15岁的爱玛·包法利那样,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受,而我的感受,幸好没有餍足的时候。我阅读这些小说,对我的学习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补益。同我接受的所有思想相反,狼吞虎咽看过的数千页文字,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加强我的拼写能力,直到今天,我提笔还总是犹豫,什么时候都离不开我那些词典。是的,暂时克服我拼写错误的作品(暂时这个字眼使拼写错误成为常态可能了),则是我那位老师要求我创作的那部小说:他审读我的小说,绝不肯降低水准,来纠正错别字。我交给他的手稿,不能有拼写错误。总之,一位教育天才。也许仅仅对我如此,也许仅仅符合这种情况,但不失为一位天才。
另外三位老师
巴尔先生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吗?还有,次年教我们的吉小姐,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吗?再有,我复读的毕业班的老师S先生,也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哲学家吗?想必如此,不过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仅仅了解这三人身上寄寓着传授他们课程的这种激情。他们就是用这种激情武装起来,一直下到我气馁的深底寻找我,等到我在他们的课堂站稳脚跟才放手,而他们的课堂显示,这正是我一生的前厅。他们并不是特殊关怀我,无论好学生和差生,他们都一视同仁,并且善于激发差生听懂课程的愿望。他们一步一步陪伴我们的努力,乐见我们的进步,对我们的迟缓也不丧失耐心,从不把我们的失利视为个人的耻辱,但是要求我们很严,尤其这种严格要求是建立在他们本人教学的质量、一贯认真和慷慨的基础之上。此外,很难想象还有比他们更不同的教师:巴尔先生,笑眯眯的平静神态,就是一尊数学菩萨;吉小姐则相反,应是一种陆地龙卷风,把我们从懒惰状态中拔出来,以便把我们卷进历史纷乱的课程里;至于S先生,怀疑论者的哲学教师,以尖形为特征(尖鼻子、尖帽子、尖尖突出的肚子),沉稳不动,极有洞察力,他给我脑子留下乱哄哄的问题,到了晚上我还急切想回答。我交给他写得很长的论说文,他誉为详尽,从而暗示他更喜欢批改简洁的作业。
综合考虑,这三位教师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不放弃。他们不容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有多少回因为拼写错误太多,吉小姐让我重做作业?有多少回巴尔先生见我在走廊失神,或者在自习室冥想,就给我上辅导课?“既然我们都在这儿,佩纳齐奥尼,我们学一刻钟数学好吗?好了,就上一刻钟……”)
此外,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风格。他们在传授知识中是艺术家。他们讲课,当然是言传的行为,但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知识的传授近乎自发的创造了。他们游刃有余,将每个课时都变成一个事件,我们因为亲历而能牢牢记住。看来,吉小姐复活了历史,巴尔先生重新发现了数学,苏格拉底通过S先生的口表述!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如同构成那天讲授内容主题的定理、和平协定或根本思想那样令人难忘。他们讲课就在创造重大事件。
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就此而止。至少,他们表面的影响是如此。在他们所体现的课程之外,他们就不想对我们施加影响。他们不一样,而那些爱炫耀的教师,就总讲自己影响了多少苦于缺少父亲形象的青少年。至少,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救学生的老师吗?至于我们,我们是他们的数学课、历史课和哲学课的学生,而且仅仅是他们的学生。诚然,我们就像一个非常封闭的俱乐部会员那样,产生一种略显时髦的自豪感;不过,假如他们得知45年后,他们的一名学子多亏了他们而成为教师,出色地扮演弟子角色,为他们立起了一尊雕像,那么他们肯定会头一个感到吃惊!尤其是他们正像我的那位勒布朗—梅尼勒的大提琴手,一旦回到家中,除了批改作业或者备课,恐怕就不大考虑我们了。他们肯定还有其他关注点,有一种开放式的好奇心,借以增长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上课能那样紧凑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吉小姐,我觉得她那胃口能吞下她那些图书和世界。)这些老师让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知识,甚至还有对知识的渴求!他们教给我们的是传授知识的兴趣。因此,我们饥肠辘辘去上他们的课。我不敢说我们感到他们喜爱我们,但是肯定看重我们(今天的青年则讲“尊重”),这种看重一直体现到批改我们的作业,批语完全针对我们每个人。典型是我们上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年级的历史老师博姆先生的批改。他要求我们的论说文后面留一张空白页,他好能用打字机以单行距,用红铅字打上每份作业的详尽答案!
我在中学最后几年遇见的这些老师,大大改变了我对其他那些教师的看法。那些教师总把他们的学生简化为“这个班”,一个不稳定的整体,他们一提起“这个班”,就使用“最差”的字眼。在他们眼里,我们总是他们教学生涯中教的最差的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或毕业班,他们教过的班级从未如此……这样……就好像他们的受众一年不如一年,不配听他们的课了。他们向校领导抱怨,在班级委员会上,在家长会议上大发牢骚。他们的诉苦唤起我们身上一种特殊的凶残,类似遭遇海难的人那种疯狂,非要揪住让船触礁的懦夫船长同归于尽不可。(对,这不过是一种意象……这么说吧,他们尤其是我们理想的罪人,我们也同样是他们理想的罪人;他们通常的抑郁症维系着我们身上一种解气的凶狠。)
他们当中最可怕的人是布拉马尔先生(布拉马尔是个绰号),我9岁那年的可鄙刽子手,他给我打的坏分数,多如雨点落到我头上,时至今日,我还被卡在行政级别的尾部,有时不免把我等候的票号视为布拉马尔的判决:“No.175,佩纳齐奥尼,总是远离祝贺!”
再如那位自然科学课教师,在我中学最后一年教我,正是由于他,我才被开除出那所中学。他抱怨“这个班”平均起来,也不会超过3.5/20,而他的不慎之举,就是问我们是什么缘故。他扬起额头,伸出下颏,耷拉下眼皮,问道:
“怎么样,谁能解释一下这种……功绩吗?”
我礼貌地举起食指,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或者我们班的统计出现巨大谬误(32名学生,在自然科学课不可能超过3.5的平均数),或者这种饥饿的结果表明这种可有可无的教学质量。
他一定对我的回答满意,我猜想。
不料却被赶出教室。
“英勇,但是徒劳,”一个同学向我指出,“你可知道一位教师和一件工具之间的差异?不知道?坏教师不可救药。”
结果被开除。
我父亲当然怒不可遏。
那些年日常的怨恨,留下不堪回首的记忆!
(摘自《上学的烦恼》,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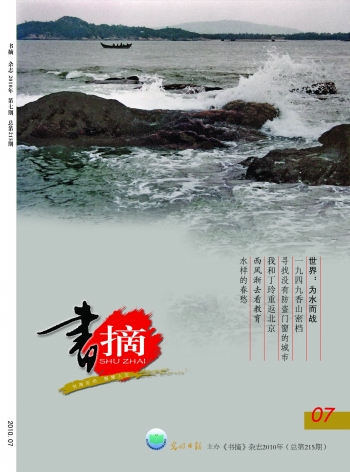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