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至2001年作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就职
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面临的第一个巨大挑战竟然是进入总部大楼参加自己的宣誓就职仪式。玛丽莲、我和四个孩子提前抵达了第九大街通往地下停车场的入口,我们大家都挤在一辆沃尔沃旅行车里。弗兰克·约翰逊正在等候,总统快到了,而我却急切地想做完这些繁文缛节的事情然后投入工作。但在地下停车场入口,身穿制服、正在执勤的联邦调查局警员却把我拦住了。
“你有身份证吗?”他问我。
我试着拿出我的驾照给他。
“不行,”他说,“你有联邦调查局徽章吗?”
“还没有,”我告诉他,“但我快有了。有没有人提到过今天要为新局长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他知道这事,但他没有客人清单可以核实。
“好吧,听着,”我说,“我就是要宣誓就职的人!”
至少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天晚些时候,也许是为了弥补对新老板的冒犯,联邦调查局安全特遣队派了三辆车跟在我的沃尔沃后面上了街,经过30个街区,跨过波托马克河到达我们准备下榻的基桥万豪酒店。这几辆车等了几个小时后又随我们去用晚餐,接着跟随我们离开餐厅,然后直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离开酒店的时候还在等候。
“你们是不是还准备跟着我一段时间?”我问了其中一名司机。
“一直跟着。”他说,而且确实打算这么做。
我们很快就搬入了弗吉尼亚州大瀑布城一幢租来的房子里,这里正靠近华盛顿大都市区郊区的边缘地带。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迪克·卡尔森和帕特丽夏·卡尔森是一对非常友善的夫妻。迪克是一位媒体天才,并曾任大使,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美丽聪颖的帕特丽夏则成了玛丽莲最好的朋友。他们共同教会了我们如何在特区生活下去。
我们认为大瀑布城是个养育孩子的好地方,想一边物色房子,一边让孩子们在这里上学。几天后,我们安全特遣队的队长来见我。
“局长,我们正考虑在你家外面放一个活动房。这样我们就可以安排人员全天待在那里了。”
“你们不能这么做,”我告诉他,“你们不能在那里放活动房。”
“那好吧,”他说,“我们把活动房放在后院。”
“那更不行!”
当然,孩子们喜欢受到关注。我们去参加周末的足球赛、去超市、去所有的地方时都有护卫。不过除了像名人那样出行,我的新身份也给了孩子们第二个好处。
在我做局长的初期,有个周六我们在护卫的陪同下去了百仕达(美国的音像连锁店——译者注),我的一个儿子当时就说:“这太酷了!”
“别瞎说,”我跟他说,“你不觉得护卫到处跟着咱们太烦了吗?”
“不烦,这样当着别人的面你就不会对我们大喊大叫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他说得非常对。孩子们去哪里都有六名特工看着他们。这样的话我就必须始终做个模范父亲了!于是,我决定了:我不需要保护。
我的前任威廉·塞辛斯所喜爱的庞大的安全特遣队很自然地传到了我的手中。我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全部开除,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设法将所有人都安排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或他们想干的职位上。最后就留下了两位司机作为我的安全特遣队:一位很快就要退休了,另一位叫约翰·格利格里奥尼,他从前是爱荷华大学橄榄球队的队员,曾经做过联邦警察,所以他可以带枪。
出于责任感,约翰在与我一起制定新的安全措施时,带我来到联邦调查局停车场的深处,给我看了那辆局长们外出时偶尔乘坐的重达三吨的防弹轿车。
“我们用不着这个,”我告诉他说,“它像喜歌剧里的东西。”
“那太好了,”他说,“我讨厌开这玩意儿,每开几百英里你就得给它换刹车。”
结果,我们开了一辆雪佛兰郊外型车往返于调查局和大瀑布之间。约翰带着他的枪,我带着我的枪,在车里和差不多一切所到之处我们都带着。作为后备,我们还有一挺机枪放在仪表盘下。这就是我们的新安全措施。(随身带枪并不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传统做法,虽然有具体的规章允许这么做。但对我而言,这是代替安全特遣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我也喜欢和特工们一起每季度测一次射击。)
“如有情况,”我告诉约翰·格利格里奥尼,“你开车,我射击!”
几乎和调整安全要求一样困难,我也很难调整自己在埃德加·胡佛大楼里说话的力度。我在政府担任其他职务时,官僚机构的轮子转得非常非常慢。现在,我的小小要求会从局长办公室里扩散出去,然后在穿过每个楼层时被放大,等到从另一头传出去时已成了一声巨吼。
当我打电话给我那极其井井有条的秘书诺琳·高利(她已经先一步搬去为我整理办公室了)时,我依然处于将自己和家庭向华盛顿迁移的过程中。我告诉她我想在墙上挂几样东西,打听墙壁有没有承重限制,办公室里有没有承重墙,还是说所有的墙壁都是摆设。诺琳把我的问题传达给了设施部的人员,随即她发现一名设施部的人员正在办公室里进行测量。
“你在干什么?”她问。
“我们在这儿给局长挪墙。”
“为什么?”
“有人打电话下来说局长要求办公室再大点儿。”
我已经有很多空间了。诺琳也有很多空间。在我们俩之间是一个会议室,它十分巨大,以至于每次我想引起诺琳注意时都得大声喊叫。(尽管J.埃德加·胡佛没能一直占有这套办公室,但这是由他亲手设计的,他显然没打算用喊叫的方式让秘书听见。)我不需要空间,我只想知道我能否将我孩子镶了框的画作挂起来而不至于把夹板墙拉倒。
关于预算
虽然我可以理解,但我从未真正习惯于将那些对我而言应该是基本的和每日要做的实际决定和政治挂钩。在我当上局长约一年后,我在一份内部报告中顺便提到,由于部分预算被削减,我们将不得不限制特工射击的子弹数量,不仅训练学院使用的数量要减少,而且用在季度考核的子弹数量也要受限制,而包括局长在内的每个特工如果想继续携带武器就必须通过季度考核。简单来说,由于目前的预算限制,我们没有钱购买足够的子弹。结果呢,华盛顿就是华盛顿,内部报告居然泄露给了报界。接着,利昂·帕内塔打来电话,他刚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调到白宫当办公厅主任。我很喜欢利昂,我们是好朋友,但利昂这一次来电不是为了聊天。
“你干嘛在报告里写联邦调查局没有足够的子弹呢?”他要求了解情况,“这让政府多没面子啊!”
我不知道利昂期待我怎样反应。我会发怒吗?还是大声喊叫,或者后悔?他待在华盛顿的时间很长了,而且我十分尊敬他,我猜想他应该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不过对我而言,我只能对这种荒谬的事置之一笑。
等平静下来后,我就解释我当时申请更多的钱买子弹的理由就跟五角大楼在它的预算中申请更多的军火一样,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子弹,因为特工们在抱怨这一点,还因为如果你要求下面的人在执行任务时使用武器的话,为了他们自己和平民百姓的安全,需要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训练。至少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理由,而一旦染上了政治色彩,理由通常是第一个被宾夕法尼亚大道忽略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不合理”的合理预算申请居然被批准了,调查局从那以后总有过多的弹药不知该用到哪里。
另一个处理预算的例子则是这样的: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届任期过半时,我正在苦苦游说要求购买一架远程飞机以替代调查局目前打算处理掉的老式桨状喷气飞机。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围捕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和寻找目击恐怖主义行为的证人,并说服东道国政府允许我们将他们带回美国。通常我们无法找到我们的猎物或得到带走他们的许可。这是行业的特性。但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我们一般只有很短的时间将嫌犯带走,有时只有12小时。在这类情形下,我们必须争取到一架军用飞机进行运输。如果搞不到军用飞机,我们只有给美国航空公司的那些关系比较好的首席执行官们打电话,看能否搭他们公司的飞机去卡拉奇或多哈或任何我们要去的地方。
对我而言,这种情况十分荒唐,所以我开始游说申请一架湾流G-5型飞机。这种飞机的价格并不便宜——约4000万美元,但毫无疑问,我们非常需要。由于白宫很显然不想管这件事,我只能求助于国会;求助于阿拉斯加州的泰德·史蒂文斯,当时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负责人;求助于阿拉巴马州的理查·谢尔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们两人都同意看看能为这件事做些什么,而就在此时,1998年5月,我破天荒地接到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新主任打来的电话。
“你不能这么做。”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你什么意思,我‘不能’这么做?”
“你没有被授权做这样的申请。”
我告诉他我们需要飞机并试图快速解释清楚,但他无动于衷。
“我们已做了分析,”他最后说,“而我们的看法是你们不需要它。”
“好吧,”我说,并努力克制着心中开始形成的愤怒,“你在反恐方面的经历如何?”
不出所料,他不喜欢被这么质问,而我也不在乎他会说什么。
几周后,乔治·特尼特和我一起来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讨论我们的预算需求。在听证过程中,主席说:“哦,顺便问一下,弗里局长,是你们需要一架远程飞机吗?”
这是一记慢投,正好在中位,而我起身将它击出了球场,但我有点过火了。毕竟乔治和我一样都需要一架G-5,而他也和我一样因花费过多而遭到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严厉批评,所以我决定为我们两个人进行辩护。
“是的,主席先生,”我答道,站起来并渴望得分,“我们急需飞机,而且由于某些原因,我们无法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人那里获得批准。”接着我转向乔治并补充道:“他也需要一架:而且他比我更需要。”
乔治看着我笑了,但也许我当时应该闭嘴,因为他比联邦调查局先获得了G-5。我后来戏弄乔治(我的密友,也是出色的中情局局长)说,他应该将他那架飞机命名为FBI。
每年我们都要经过这种可笑的预算操作。调查局要详细说明自认为所需的预算,接着将预算送往司法部并期望他们将提交的数字削减到实际所需的范围。司法部随后将预算送往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预算将被进一步削减。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再将预算按照同样精神送往国会,如果我们最初的预测是准确的并且所提交的数字比实际想要的高出足够多的话,我们最终得到的预算就可能满足需要。这就是预算的操作过程。
生活中的风险
作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我当然不能忽视针对我家庭和我个人的威胁。我拒绝了护卫车、后院的安全活动房屋,也不让防弹大怪物拉着我到处跑,因为玛丽莲和我不想让我们一家生活在保护罩里。我们住的地方是华盛顿特区树木葱茏的郊区,不是在贝鲁特分界线或巴格达绿区。我也不想让一群安全特遣队的人员像保护其他局长那样围着我们,另外如果真的有人盯上了我,我可不想让那么多人因我而受到伤害。因为目标是我,而不是别人。
我也尽量让自己显得过于愚蠢。自当上局长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让自己的一生暴露在人类心灵的黑暗里面了。我的朋友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他的妻子在西西里被炸死。我在海伦·万斯受重伤后不久去看了她,她的丈夫罗伯特·万斯法官被罗伊·穆迪的一枚邮件炸弹残忍地杀害了,在每个周年纪念日我都会给海伦打个电话。无论事实如何,我不得不假设坏人已将我锁定为目标,因为我将本·拉登纳入了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的名单,并且监督了对他的调查、控告和追捕。我一直假设我的家人和我都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邮件也会经过处理。所有收件地址是我们家的邮包和信件都经联邦调查局拦截,并在确认安全后送到我们家。这是目前保护高级政府官员的标准操作程序。
孩子们则是另一回事。在我八年多局长任期内,玛丽莲和我一直在担心他们的安全。除非将他们纳入证人保护计划,否则无法完全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而如果我愿意采用这种极端的保护措施,当初就不会接受这一职位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零风险是不存在的。
对于让特工跟着孩子们整天呆在学校里这个问题,我的想法也是如此:这根本不是孩子们自然成长的方式。因此,我们选择了简单实用的应急措施。由于可预测的线路上是最容易发生袭击和劫持的,所以我们的人会跟着孩子往返于学校。我们还确保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了解我们对孩子安全的忧虑。感谢这些学校的官员在这方面的出色工作,他们采取并保持了对进入大楼的每个人进行安检的措施。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警察会一天数次在我们家周围进行巡逻,他们是我们出现紧急情况的第一回应者。
至于家庭旅行,我们每次都尽可能悄悄离开,到哪里都不大张旗鼓,即使在玩得高兴时也保持低调,但这未必总能奏效。有一次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黑德度假,我的一个小儿子把自己弄伤了,我就带他去医院并坐在他身边等着大夫来缝针,当时正好有几名当地的副警长押着四名带着手铐的犯人来治疗。
“等会儿,”其中一名犯人边说边盯着我看,“我在哪儿见过你。”
“不会,”我告诉他,“我们从外地来的。”
“不,不,”他坚持道,“我见过你!”
“你当然见过他,”其中一名副警长最后大声说,“他是联邦调查局局长。”
“谢了。”我再一次暴露了。
为了保障开车进出城的安全,约翰·格利格里奥尼和我将那挺机枪放在我们郊外型车的仪表盘下,当我离开家或办公室的时候会随身携带一把九毫米的手枪:在我走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去喝咖啡时,去见司法部长时,在白宫或中央情报局时,在飞机和火车上时,在教堂时,观看校园演出时,开着家里的车去度假时,晚上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工作时。大概唯一不带枪的时候就是睡觉(而这时候枪在床头柜上,一伸手就能拿到)和清晨出去慢跑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非常理性的做法,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跑在阴暗的街上,但有些事情你只能仰仗自己的信仰)。
其实我在设想,如果真有高手决定要我的命,他们很可能会成功,无论我带不带我那可靠的九毫米手枪或是身边有没有愿意舍身保护我的特工,但我依然把它带在身边,既是为了保护,也是为了不断地提醒自己绝不要让我的警卫倒下。多年来,我怀疑这种心态可能已经成了我的个人习惯了。
(摘自《我的FBI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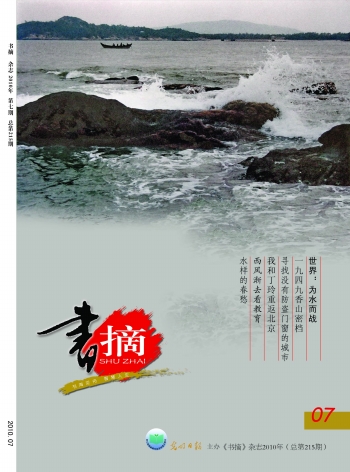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