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 仨
我们仨,自然是指张国立、张铁林、王刚三个人的组合。
三个人中,我年龄最大,比张国立大七岁,比张铁林大九岁。
私底下怎么称呼?我称呼他们是国立、铁林,有时候起点腻就“立立”,但一直就是铁林。国立和铁林跟我,有时候是“老哥”“哥哥”,有时候无厘头,来一声“刚刚”“小刚子”,我也怡然受之。嘿,也就在这时候敢玩点“老扮嫩”。总之,关系已经随便到说什么都无所谓的程度了。当然,也不是一点尺度没有,当着外人面,包括记者采访时,他们往往就称我为王老师、王刚老师,假惺惺的,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呢,在这种场合下还一如既往地“国立”“铁林”叫着。
三个人性格迥异。一般而言,不同的人,能在一个戏里面,而且由一个戏以后,又在好几部戏里面,能够非常快乐地合作这么长时间的,几乎很少。一般都难免犯这样一个毛病,谁主谁次、谁多谁少,争个不休。但我们没有,从来也没有这么去想过。
第一什么东西都看得比较透了,名也好、利也好,大家看得相对也比较淡了,尤其是一些虚无缥渺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你多两场戏,他多几句词?
比如《五月槐花香》,我记得张国立将近三百场戏,张铁林一百八九十场戏,我演的蓝一贵八十九场戏,这个比例就是三二一的比例。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是“名”,这个名跟你露脸的数量往往成正比,还牵扯到“利”,片酬是按集来结的。但是要想让观众喜欢各自的人物,看出这个戏的好来,提高整个剧的收视率和美誉度,最好各得其所。否则于全局不利,于自己也不好——费力不讨好!
这是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戏剧关系的映射,所以才显得有趣。像卡通片里的猫捉老鼠。两个人互相不停地捉又捉不到,互相在那里斗,不断地延续下去,这个过程当中就充满着智慧。我跟国立的戏,当中有些笑料,类似相声的情节,总之直接交锋多一些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讲,不要把镜头切来切去,镜头的转换不如我们语言节奏的把握更准确,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好我们两个人都在一个镜头里。
两个人演得特别“腻乎”,节奏的把握特别舒服,观众看着也特别过瘾。
演戏演到一定境界,就可以不断自我“创新”,有感而发,即兴台词顺嘴就秃噜出来了,这种演员之间合作的默契是很难得的。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国立、铁林三个人有一场戏,是纪晓岚安排乾隆扮店小二,且皇上大半拉脸蒙着布,和珅不知道那是皇上,因此纪晓岚趁着喝酒就把他的心里话全都套出来了。这段戏好多都是即兴的,导演都不知道在哪里“Cut”了。当这场戏可算停了,全场哈哈大笑。
我们演戏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有时都绷不住。现场工作人员是第一观众,他们能接受,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就更容易接受了。
我们演戏默契,风格上很快能够互相融入。开始我跟国立的风格更容易沟通一些,更接近,铁林是后来慢慢融入我们的。跟我合作的男演员里面,不用对词上来就演的不多,张国立是其中一个。以至于每次进场,赶上今天是我和国立的戏,我就踏实了,知道很快就能收工回家。因为我们有一些经历是相似的,比如,他也曾跟曲艺门的人接触过,也试着说过相声。另外他是个很优秀的主持人,原来也在电台演播过小说。
张铁林就不一样了,俗话说:“热馒头——端着。”他很难放下身段来,所以他演皇上很合适。
平时大家互相开玩笑难免挤兑人,多半是我跟国立来挤兑铁林。
那一回湖南卫视把我们三个请去,节目是何炅和李湘主持的。记得李湘问:“三位老师在一起,你们两个演臣子,平时演皇上的张铁林一定是高高在上了?”
张铁林不听这话则已,一听,旧恨新仇全涌上心头:“什么呀?恰恰相反,他们俩老欺负我!”
全场观众笑翻了天,没想到,三个老男人戏里如此好玩,戏外也是照样童心盎然。
有人问我:三人中是不是张铁林脾气最好?
这一点不能简单论之,更不好光看表象。三个人都有脾气,我的脾气可能更突出一点。自从张国立负了点儿责以后(除了做演员还要做制片人,后来还兼总导演),我开玩笑说:“国立啊,我特别愿意你负起更多的责任来,这样我的脾气要发起来更自然了。我在这个剧组活得会洒脱一些,你就会哄着我。咱们仨人要都是演员,班儿对班儿的,这还就麻烦了。”
拍《纪晓岚》第4部的时候,在现场有一个执行导演,但是很多重场戏,张国立得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忙得团团转。预备——吆喝一声后,忙又归到我们堆里演戏。歇着的时候,我们这儿扯别的,他又忙着“公务”,好几个合同得签。
我说:“哎哟,悠着点儿吧,你活得忒累了。”
其实心里很是佩服。
铁林当过导演,现在他当院长。你不要以为他这个院长是空的,他是实实在在当了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
经常在一起搭戏,也不意味着平时一定要热热闹闹地总在一起。我们时聚时散,一有我们仨都参与的戏就聚在一起了,没有,就各忙各的。偶然有事就打个电话。我们住得相对远,不像很多影视界的人在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别墅群里面,经常凑一起,串串门儿啊,打打牌呀,我从来没有,我也不喜欢打牌。
国立的应酬一定和正事有关,比如,他说今天有个饭局,一定是跟拍戏的事有关。铁林的应酬,颇有点名士之风。“非典”期间,他专赴上海拜师学戏;再回京,一句满工满调的西皮倒板,唱得我目瞪口呆。平素,他雅好收藏,专攻尺牍手札;他书法也颇有造诣,虽常接触的一些人,多非书画界主流,可他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闲扯”。总之,平素交游纯属个人兴致所至,几乎没有任何功利色彩,这是张铁林的特点。他与梨园行、书画界都颇有渊源。
演和珅也是为人民服务
说起来,大伙可能觉得挺逗的,《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大火以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郑重其事地通过“一级组织”(通过中央电视台还是通过谁,忘了)找到了我。
我拿起电话,对方热情洋溢地说:“王刚同志你好啊!找您真不容易呀……”
我忙客气地应承:“不敢当不敢当,您好,请问您是?”
对方介绍说:“我们是高检的。”
我没听明白:“唔,高检……是谁?”
他忙说全称:“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嘴里“咝啦”一声,心想:没事吧?我就犯了错误也不至于惊动高检吧?
我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想聘你做反职务犯罪宣传顾问,聘书即刻送到。”
我哭笑不得:“你们不会是找错人了吧?我可是演和珅的。一个演贪官的,反职务犯罪让我当宣传顾问?……合适吗?”
那边的回答挺干脆:“王刚同志,正因为你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你对贪官心理变化一定非常了解,对于这种人的症结,你能说出一二三来。”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这么一个戏剧角色,我扮演的一个特殊意义的“反面教材”,居然可以进入“政法警示”的视野。这是编剧演员的“荣幸”?还是反腐倡廉“急急如律令”造成的时代尴尬?
让我感到特别难忘的是:曾经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两次邀我到西城区他家中做客。万没想到当年的华主席也是我的戏迷。
华老特别有意思,开口便用他那醇厚的山西口音对我说:“王刚同志,你演的那个和珅,演得实在是好嘞……”
听我讲述演和珅的趣事和社会效应,华老时而开怀大乐,时而陷入思索。我记得华老有一次插话,评点了一句:“你演和珅,也是为人民服务。”
说实在的,真是欣慰。但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华老的一番话,有几分凝重和酸涩。
“主持人里最好的收藏家”
我的收藏与演艺生涯是交叉的。在宣传电视剧《玉碎》时,我在去天津的车上,还在遥控指挥藏友在日本大阪的一次拍卖会上的叫价。当时正在拍一件元代剔黑荷塘鸳鸯纹盘(我曾在大英博物馆见到过类似的一只),因品相一般,不到300万日元就落了锤,那才是我心理价位的一半!那一刻,天津也到了,真个是:天津萝卜——心儿里美呀!
这种情形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发生。说来也巧,拍卖分春秋两季;拍戏也多半在这两个时间段。这就难免撞架了。平时拍戏时我都关了手机,但如果那天有拍卖会,我若是急了,会在演戏时突然喊一嗓子:“停!”往往搞得周围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我就躲一边接电话,开始叫价。
记得有一次,为了一对儿乾隆柠檬黄地儿洋彩花卉碗,我在拍戏现场用手机竞拍。没几番,对手就剩一个。我充满信心势在必得,对手也毫不气馁步步紧逼,两人轮番叫价,又叫了二十多口时,我扛不住了,与我心仪已久的宝贝儿失之交臂了。然后踏实演戏。
一旁的导演告诉我,王老师你刚才喊那声“停”时,嗓子都“劈”了。
不过,时间一长,大家都习惯了。
有媒体称我是“收藏界最好的主持人,主持人里最好的收藏家”。我明白这话里有褒有贬;再有记者问我以为然否时,我便笑答:哈哈,然也,然也,精辟!准确!
把演艺跟收藏连在一起说,我肯定绕不过和珅了。演了和珅之后,我也有意收藏一些和此人有关的东西。我有两个和珅的折子,其中一个是贺乾隆喜得五世孙的贺折,还被我拿到电视上展示过。某次有拍卖公司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和珅的大卷轴书法,拍前买断价15万元,简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当即表示:“乾隆的字才3万元,不要。”
结果,证明是我判断失误。在拍卖场上看到那幅字后顿足大悔——这幅字品相极好,最后以六十多万元的价格被一个企业家拿下。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只好自我安慰说:“他花那么多钱买一贪官的字,有毛病吧?”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拿艺术品投机的人,自己也几乎是只进不出,顶多玩腻了,出手几件,再换回一件更好的、往往也是价钱更大的。先去伪存真,后去粗取精,这也是收藏的一般规律。而其间不断碰到的尴尬就是,品位提高了,钱跟不上,财力总是跟不上眼力。好在前辈早就撂下话了:过眼即拥有啊,聊以自慰。
我与成方圆——惭愧与感恩
1997年,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我们很低调地处理两个人的事情,包括喜酒,就是两家人,简单地吃一顿饭。
但毕竟,两个都属于“公众人物”,真的想低调,那也是很难的。这段婚史,在当年见报率挺高的,媒体欢迎这种素材呀。
在1998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到圆子(圈中好友都这样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那时,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总管。音乐剧头一轮在保利大厦要演十场,我天天下午还要到北京电视台主持两场《东芝动物乐园》,完了之后我自己开着车到保利大厦已经五点半了。圆子就在我们俩共用的一个化妆间,提前把凳子、椅子铺好,让我睡上二三十分钟。
虽然累,但是每天演完以后那感觉特别好。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还跳着舞,向中间的观众、两旁的观众还有向楼上的观众敬礼。观众也不走,因为舞台剧它就有这样直接的反馈,它不像演别的。哎呀!那感觉真的很美好。
与圆子共同出演《音乐之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里。
往家开的时候,我记得成方圆说了一句非常发自内心的话:“天天这样多好啊。”
圆子曾说:“我和王刚有一种互补性,王刚属于传统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圆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
我的“酒史”,是从知青点——特别是26年的部队生涯中延续下来的。有美好,也有负面的插曲。
我这个德行,给了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我妹妹王静,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时,我竟要拉车门跳下去……几番折腾终于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
夫妻随团去欧洲演出。在法国的时候,当地华人非常热情,一连串的酒场酒局。得意忘形之余,坏了,不行了,身子灵魂都在坠落了。他们把我送往枫丹白露的急救中心。
路上,我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闭上了,心想:死了算了,太难受了。
这是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
记得成方圆掐着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终于躺在病床上,当两个洋人的脸朝我俯下来时,我彻底昏过去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急救,我才醒了。
近些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情节”,让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笔墨澄清: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学费而分手的,这个事情实属子虚乌有。
人家说了什么,你又不能去反驳,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真的,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摘自《我本顽痴——王刚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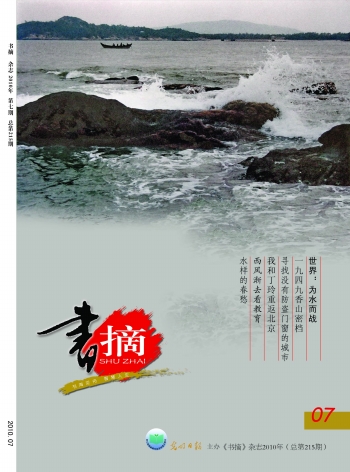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