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梨园
在旗的管祖母叫“太太”,她老人家姓托氏。我祖父荣福公原居德胜门内正黄旗界后海南沿的小翔凤胡同官房,原配王氏早故未遗子女,我祖母是续弦,生下十一位子女,仅存四子,父亲行四,旗名承麟。祖父绰号“荣胖子”,40岁时突患暴病逝世,遗下祖母带着四个孤儿靠官府少许钱粮生活。清末皇朝经济每况愈下,加上二伯荣寿从中克扣,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只得靠变卖家产维持一家五口生活。进入民国,祖母的长子、次子因宣统出宫也从紫禁城禁军班上遣散回家,祖母不得不被迫从小翔凤胡同祖宅迁出。最初搬到京郊清华园附近的小营,以后又搬了十几次家,无外乎都围着京西旗营子转悠,最后落到了北京南城天桥东大市。这地方俗称“穷汉市”,顾名思义就是地道的贫民窟了。老祖母带着年仅六七岁的两个幼子——我的三大爷和父亲,靠自己给人缝衣维持一家生活。父亲眼见得这么下去一家子非饿死不可,就央告我祖母允许自己去卖身学戏。那时人们都认为唱戏能挣钱,唱红了成了“角儿”,更能挣大钱。祖母是名门望族出身,怎么能让孩子去作“下九流”的事由,更不愿把儿子送进火坑受罪。架不住父亲苦苦哀求,这才狠了狠心同唱武旦的荣蝶仙先生签了为期九年的卖身契,放我父亲去魏染胡同荣宅作手把徒弟。祖母把极大希望寄托于老四,几乎隔长不短就到正阳门的关帝庙烧香祷告,盼望儿子早点儿学成,上台演戏挣钱养家。谁知老师把徒弟当“小催巴”使唤,也不教戏,祖母急了,多次找荣先生催促。经过六年苦学熬练,父亲两条大腿内侧因练功时挨师父毒打瘀血不散,落下成串的血疙瘩,阴天下雨痛得走不动道儿。父亲受的那份活罪真是一言难尽了,只能用“极其悲惨”来形容,祖母为了儿子能学成出师登台演戏,苦熬了多少岁月啊!亏得我三大爷后来在信阳铁路局混了个小差事,才多少帮补帮补家用。父亲常说自己的三哥顾家,孝顺母亲,至于大哥、二哥就不能恭维了。所以后来父亲对我三大爷特别眷顾,这已是后话了。学会了唱能上台演戏是一回事,那最多在大戏班里给名角儿当个三四路角色,给名角唱个开场戏,或当个小配角什么的,就算不赖了,要能熬成为挑大梁的名角儿,谈何容易。何况,出师以后还得给老师白唱三年呢!前面的路确是坎坷而曲折呀!正在这节骨眼上,父亲又“倒了仓”(少年发育中的变嗓),若是熬不过这一关,嗓子缓不过劲儿来,就甭吃这碗戏饭了。可是,荣老师急于让父亲给他唱戏挣钱,竟同上海戏院签了合同,收了人家600块现大洋的戏份,父亲不能唱也得愣卡鹅脖给师父挣钱去。幸亏顺德罗瘿公先生在这节骨眼上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找到中国银行总裁张嘉敖先生说:“荣蝶仙光看见钱了,叫艳秋倒了仓还去上海唱戏,就把这孩子给毁了!”罗公向张先生借了600块现大洋给父亲赎身提前出师,从此离开了荣家。罗先生是一介名士学者,本身并不富裕,却为父亲一家租赁了北芦草园9号一所宅子,把祖母和三大爷从天桥东大市贫民窟接了出来,每天亲自指导父亲学诗词写大字,督促练工养嗓,介绍父亲向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求教,带着父亲到大马神庙王宅向王瑶卿先生学戏,大力扶持培养,全出于一片惜才怜才之爱心。等父亲嗓子恢复以后,罗公针对父亲本身的特点量体裁衣亲自编写剧本,充当公关宣传,千方百计地设法叫父亲登台演出。从借台学艺、搭散班献艺,到自组班社独挑大梁的每一阶段,罗公都身体力行亲自布置。直至父亲一炮打红,罗公也因操劳过度而沉疴难挽一病不起了。罗瘿公临终之时仍为父亲今后的发展嘱托金仲荪先生代行编剧及其他文墨职责,安排各项演剧事宜。罗公真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说:“程有今日,罗居首功”。罗瘿公先生病故,父亲扶柩亲葬罗公于西山八大处,每年清明必携全家扫墓祭奠。正是有了罗瘿公先生和王瑶卿先生的精心扶掖及培育,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父亲才能成了名角儿。
拳不离手 曲不离口
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每当忆及父亲的时候,总满怀深情感慨地说:“你父亲这一辈子没有享过几天福,他全身心扑在艺术上,下的那个功夫,受的那份苦,就没法说了。”作为京剧界中够上“角儿”的人,哪个不是如此过来的!越是名气大的“角儿”,受的“罪”就越大越深,内行管这不叫“受罪”,叫功夫、功课,所谓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父亲最早住在后院北正房的东耳房。父亲卧室犄角放着一个涂了褐色漆皮的瘦高长腿木架子,架子顶端装有半月牙形的木托,托着一个绿釉绳纹饰粗陶敞口坛子,其高度恰恰与父亲一米八的身量相合。最初我们不知道这是作什么用的,也不敢当面向父亲问询,日子长了,对这奇怪的装置也便习以为常了。
父亲每天起床晨练之后,便回屋洗漱,不久,便从他卧室传出念白的响亮声音。我常趴在窗户玻璃上向屋里偷窥,看到父亲站立在木架子前,面向坛子,一扳一眼地念道“督廷大人……”,接着又从一念到十。念白的喷口从坛子反弹而出引起全屋强烈的共振,声音传至户外犹如撕云裂帛般,父亲每一轮练声长达40分钟,每天上午下午各练一次,从无间断。京剧界常说“七两道白,三两唱”,可见老一辈京剧演员是如何注重道白的功夫。无怪吴富琴先生曾告我说,“你父亲在台上演戏念道白时,气贯丹田,喷口的劲道噗噗地响,把鬓边垂发都吹得飘飞起来。”根本不需在台前放置麦克风之类的扩音器,道白的每句每字都会打到全场,即使剧场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演员的每段唱腔每句道白,可见演员功力之深。现在,许多歌星,甚至是名星大腕,总要在身上或头上安着扩音器,即使如此,也常常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词儿,实在应当劝劝这些名星,还是虚心地向老一辈演员学习,真真正正在练声上下点儿苦功夫,免得总吊个麦克风叫人看了丢份!
父亲的音乐修养
父亲创腔之初主要得益于王瑶卿先生,凡罗瘿公先生编撰之新剧,在声腔音乐设计和导演方面,均赖王大爷亲自指导和把关。罗公辞世后,金仲荪先生继承罗公未竟之《碧玉簪》一剧,其编导设计已不假手于人,而由父亲“另起炉灶”独立进行创作了,因为当时连买罗瘿公面子的王大爷对父亲的态度也变得冷淡和疏远了,说《碧玉簪》这种本子只能拿到天桥去演!梨园界不少人都等着看程砚秋失去罗瘿公这座靠山之后,定会丢人现眼,从此完活!所以父亲才有重打锣鼓另开张之说。父亲的老伙伴吴富琴先生曾回忆道,罗瘿公编制的最早本戏《龙马姻缘》和《梨花记》在唱腔上仍按“以字行腔”的旧法,以后《红拂传》等一系列新剧则按“以字生腔”的新法设计,故新腔迭出。《碧玉簪》即是父亲按照“以字生腔”的原则独自设计编腔导排的第一出新戏,它也是程派艺术形成的重要标志。
父亲虽深通音律,然他没有机会接受现代音乐教育之训练,故对五线谱或简谱仍不熟稔,记得也多是工尺谱,所以他极想同马思聪先生合作,希望他参加京剧音乐现代化的工作,为此父亲把他从意大利买回来的一把著名的小提琴送给了马先生,父亲常说无论是周昌华或钟世章这些被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琴师,都比不上名琴师杨宝忠,杨先生会拉胡琴又善于小提琴,能工尺谱又能记五线谱。
关于父亲的音乐修养,吴祖光曾回忆到,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与音乐家盛家伦先生颇知交,常去东单芳嘉园探望盛家伦和吴祖光等。祖光曾提议由家伦以口哨吹出一段西洋歌剧的主旋律,请父亲当场将这旋律变成京剧的板腔体式旋律。盛哼了一段,父亲静聆之后,没有超过五分钟便将这旋律化成京剧的曲调,令祖光大感惊异,敬佩不已。父亲在音乐修养方面确实已达到炉火纯青地步。
1957年父亲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回到北京时,我正从苏联返京休假。父亲风尘仆仆地一进家门,便问我道:“《世界青年进行曲》的主旋律很美,是不是这样……”,说着他便边走边哼了一段。我说是这样的。他说:“把这主旋律变化一下可用于京剧唱段的”,说着边走边思索着,去宽衣休息了。
与其他行当、流派的合作也是如此。据我二哥永源回忆,父亲同杨宝森先生有莫逆之交。1956年,宝森先生在天津处境很不好,心情和身体均欠佳。父亲与杨先生商量决定合作,将老两位的对儿戏都灌成唱片,一方面可以把两位的拿手剧目流传给后代,另一方面也可给宝森增加些经济收入。永源兄见父亲整日拿着二胡琢磨《武家坡》的青衣唱腔,父亲说杨先生的老生唱腔有许多新的创造,自己也不能守着老腔不变。有时拉一段腔让永源听,问他好听不好听,像不像京剧唱腔的味道,直到得到肯定的回答,这才放下二胡休息。谁料到重病在身的杨先生与父亲录完了《武家坡》便一病不起,没有多久就病故了,仅隔一个月,父亲也撒手西去,《武家坡》遂成了老两位的最后绝唱了!
由此可见,父亲真正是全身心地扑在艺术研究上,他真的是时时刻刻能将凡能与京剧艺术搭上界的世间万物,从容化之并变为自己民族的东西,这便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艺术大师的庖丁解牛“以技进乎道”的真本领啊!
(摘自《我的父亲程砚秋》,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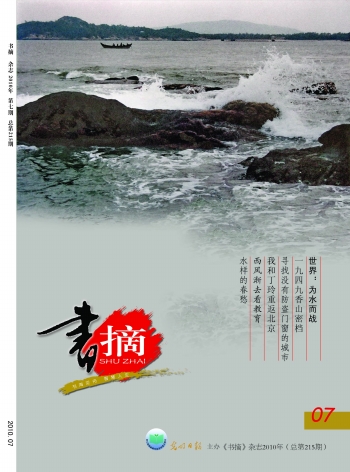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