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书是毒药
曾经有个朋友的孩子找我荐书,我遵命开了一列书目。也不知他看不看,反正后来不再来找。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看见孩子的床头放了一大摞书,随便翻了翻,自然没有我推荐的,倒是有一大堆所谓《职场防身术》、《做人不要太老实》等等。孩子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拿着我的书单去书店,有的没货,有的太难找。倒是店员跟他推荐,有一类书很热销,就是这种“职场指南书”。对他这个职场新生自然更有诱惑力。
我绝对不认为他应该按我的书单购书,但我却对这一类所谓“职场智慧”之类的书深有忌惮。
首先这一类书,挖掘的是人性中“邪恶”的细胞,让这些本该死去的“邪恶”复活,表面上看它在保护你,实际上它在教唆你。打个比方,你的爸爸为了让你知道打人是不好的,照你妈妈脸上抽一巴掌,然后疾言厉色地说:“看到了吧,这是不可以的。”
找回几本“职场指南书”一读,发现它们都源自一个老祖宗——《厚黑学》。
李宗吾写《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他的题旨是揭露鞭挞官场弊病,所以当时让人很是痛快。《厚黑学》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文化虚无主义。即便这样,李宗吾从头至尾对于“厚黑”都是毫不掩饰地批判和痛斥的。
今天的“这一类书”却把李宗吾老先生唾弃的“厚黑”,捧起来加点时尚的化学原料,变成“面膜”朝今天年轻人的脸上涂。这一点是李老爷子始料未及的。而且,今天的书商们还把《厚黑学》对“官场”的描摹放大到“职场”乃至整个人生现场。这就让人不得不追问: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出版界、影视界长期在回避一个真实的社会,他们无视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底层人的难题,却臆造了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社会。所以在国外,对中国总有两种印象,来过的知道这里跟他们那里同在二十一世纪,没来过的以为中国人还是男人梳辫子、女人裹小脚的清朝子民。我们的书店、荧屏充斥着“朝廷的故事”,每天中国人都在电视上施展权谋、不择手段。官场如此,商场如此,职场如此,民间也如此。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大人如此,小孩也如此。
可以想见,读这种“实用类”书籍长大的青年,他们人性中的善良火种怎能不灭?
我们需要传播智慧,但智慧必须建立在善良的地基上,邪恶的智慧等于毒药。
我告诉朋友的孩子,“职场系列书”中有些属于“心灵鸡汤”,无益也无害,虽然加了味精,但治不好病也看不死人。这种书可看可不看。但大部分属于毒药,无益而有害,虽然加了香料和色素,但最终书会杀人的。
我还告诉他,你这里的这本《执行力》,前段时间被捧为“职场圣经”,但这本书完全是一部假书。此书由一个书商伪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作者——哈佛大学的保罗·托马斯教授,该书商还一口气推出了七本“执行力系列”,并且还用保罗·托马斯教授的名义为另外一本假书《赢在执行》写序。
我告诉他,这才叫“厚黑”。
至于他能否听进去,天晓得。
丑闻也是生产力
今天是个“话题时代”,每天睁开眼都要面对一大堆层出不穷的话题。早晨有早新闻,中午有午新闻,晚上有晚新闻,发达的传媒机器是话题的舞台。饭桌上、公交车上以及几乎一切的公共空间,都被话题充塞着,一级话题、二级话题、三级话题,乃至无级话题……
与“话题时代”相适应的是另一个词:眼球。可见夺人眼球的无疑是话题,而能够充当话题的肯定吸引眼球。
但现在要深究一句,恐怕没那么多人愿意回答了。
这一句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话题?
大部分的人也许认为这个追问很多余,话题就是话题,只要有人传播有人接收,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划定范畴呢?
诚然,我们经历过一个没有话题的时代,或者说单一话题的时代,为了和那个时代告别,我们欢迎多元,喜欢丰富。但在多元和丰富中,我们逐渐失掉了底线,我们把有限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了无限的话题和信息中。
比如“艳照门”事件,本来这是一个让道德蒙羞的事件,只配在报屁股上呆着的新闻,现在却成为所有媒体追逐的话题,主流也追,非主流也追,不入流的也追。而且在这种追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太多媒体的声音和立场,只是每天忙着连线,连不上线也成了话题。话题中的人物在和媒体的捉迷藏中充分地享受着,那天看见话题人物回来开新闻发布会,身上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仿佛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媒体英雄,以至于他在口中道歉的时候,也没有正眼看记者。
媒体是公共平台,为什么我们如此慷慨地把公共平台廉价地让渡出去?
奥斯卡拒绝了一个“话题人物”,她就是鼎鼎大名的帕丽斯·希尔顿,她的一段性爱视频也曾在网上流传,但除了一些小报报道以外,主流媒体不屑追逐,甚至发生了女主播米卡·布热津斯基拒绝播读希尔顿的八卦新闻,并焚烧新闻稿的事情,这就是美国媒体的立场。据说为了来奥斯卡走走红地毯,希尔顿大手笔花了400万美元置装,结果被奥斯卡拒之门外。她必须为她的丑闻付出代价。
我们现在的某些情形刚好相反,丑闻居然成了身价的助推器,“艳照门”的个别女主角,这边厢暗自垂泪,那边厢有广告商找上门来,以为难言之隐,真的可以一洗了之。丑闻并不可怕,当丑闻成为生产力的时候,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过去有句话,看一个人品位如何,就看他谈论什么。同样,看一个社会的品位如何,也许就要看大众媒体在被什么话题占领。
在今天,有太多的话题应该让我们关注,我们刚刚远离一场特大雪灾,很多地区还没有从灾情中苏醒过来。我们的全民医疗问题,我们的全民教育问题,我们的劳务工问题,甚至我们的股票问题等等,一系列话题都在等待认领,媒体和公众应该学会对一部分话题保持兴奋,对另一部分话题保持必要的缄默。
区分兴奋与缄默的话题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是否无聊。
无聊者,免聊也。
经典的被流放
在这个不尊崇经典的年代,看见一部又一部经典被颠覆,看见一个又一个古人被恶搞,似乎已经没有了愤怒,有的只是漠然。以至于这两天孟京辉带着他的话剧《堂吉诃德》来深圳,宣称要“尽最大可能忠于原著”,倒让我张大着嘴吃惊半天。
本来我以为作为先锋话剧骁将的孟氏,大约要狠狠地拿西班牙大师开涮的,却不料他当众坦承改编《堂吉诃德》的时候,第一稿剧本竟有17万字,因为有太多东西无法割舍,第二稿删到5万字,但这5万字相当于舞台上的3小时40分钟,最后为了不让大家都在剧场晕倒,只能再删到目前的2小时25分钟。而且还带着主创去西班牙领略了一番。
仅凭这一点,我几乎就要向孟氏鞠躬了。当然戏还没看,这个躬先留着,等看完戏再鞠也不迟。
因为这些年被各路神仙弄怕了。电影《孔子》刚杀青,导演胡玫就发了昏话,说“我们非常有幸跟国内外知名度这么高的演员周润发合作,不仅仅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幸运,也是我们先人孔子的幸运……”其实周润发演孔子,究竟是孔子的幸运还是发哥的幸运,本无须推测,但就导演这句词不达意的马屁话,实在是辱没了祖宗,用我家乡骂小孩的话叫“失了教”。
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失了教”的人太多,有些还貌似有些文化,或者还在干着跟文化有些关系的勾当。这就让人越发担心起来。
本人不是一个古板至极的冬烘先生,也不认为经典就不能碰一指头,可是看看某些拙劣的颠覆,实在让人觉得走得太远了些。有部电视剧《金瓶梅前传》,居然把武大郎变成了“暴发户”,对小保姆潘金莲一见钟情,致使潘金莲与两小无猜的小学徒西门庆的纯真爱情受到严峻考验,此时警察武松出来干预……这种肆无忌惮的恶搞,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时尚。
这当然不能算完,四大名著都逐个被游戏一遍,《三国》被“水煮”过,《西游》被“大话”过,《红楼》成为“噩梦”,《水浒》也出了“歪传”。名著如此,其他作品就更不在话下了,孔乙己偷书是为了“资源共享”,荷塘月色是为了欣赏MM洗澡,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个促销女郎。如此这般热闹下去,真不知再过几十年,人们能否分辨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因为那些印刷品和荧屏上的惊人之语,会让人误认为进了疯人院,比如“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比如“寂寞啊寂寞,不在寂寞中恋爱,就在寂寞中变态……”在对经典的颠覆和恶搞中,无知者获得了短暂的快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和饱学之士之间已经抹平了鸿沟,对于他们而言,用简单而粗鲁的方式,实现了对知识的嘲弄,这种嘲弄与用功比起来,实在是轻松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生活并不是永远只是轻松和有趣的,真正的轻松和有趣往往只有通过艰苦和枯燥来获取。就像甜蜜的生活并不只是吃糖,更多的时候是在种甘蔗。
经典对于任何民族都是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英国有一句风行的格言:“宁可失去英伦三岛,绝不失去莎士比亚”。这句话告诉我们,任何物质性的东西都可以失去,只有精神的领地是不容失去的,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哪怕他仍然衣冠楚楚,却只等于行尸走肉。玛雅文明的消失,最初就源于他们文化原典的散佚。中华文明决不能成为第二个玛雅文明,但如果我们继续无视甚至肢解我们的经典,如果我们继续让汉字加入各种字母和符号的混合,总有一天,会面临玛雅人在十七世纪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新版话剧《堂吉诃德》让我们一反常态地受宠若惊,是不正常的正常,也是正常的不正常。虽然不能说明孟京辉有多么伟大,但却能说明在一个经典被流放的时代,我们是多么渴望经典的回归。
(摘自《冒犯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定价:21.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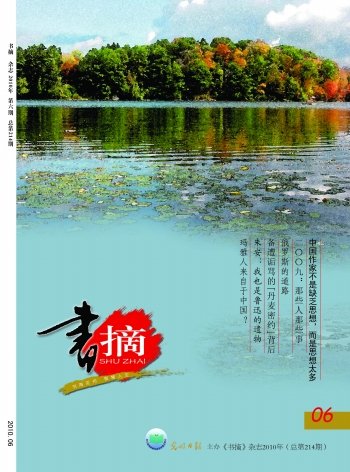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