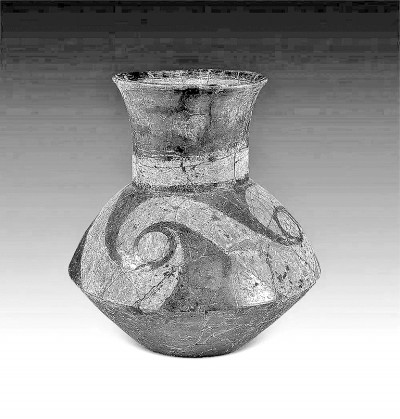【读书者说】
近期由王子今、孙家洲、高从宜等著名文史专家联袂撰写,西北大学出版社付梓的《陟彼山河:晋陕黄河左岸的历史与人文》(以下简称《陟彼山河》)以其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从众多黄河文化书籍里脱颖而出,引人注目。这是继《出入龙门:晋陕黄河左岸的历史与人文》之后,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又一精品力作,该著在实地勘查的基础上,以双线结构、多元叙述方式,展开了一轴波澜壮阔的晋陕峡谷黄河左岸的历史人文画卷,对传承黄河流域的中华优秀文化,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探讨区域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尤有意义。
文化源地与早期中国
黄河晋陕大峡谷是5464公里大河上险象环生,并且是最长的一个峡谷,受两岸高山夹持,黄河在九曲十八弯的峡谷中蜿蜒前行,左襟吕梁、右带陕北黄土高原。《陟彼山河》书写的就是这段黄河左岸的历史文化,涉及中条山南麓黄河左岸、汾渭谷地黄河左岸及其腹地、晋陕峡谷黄河左岸区域,描绘出一幅河东地区的摩崖、碑刻、古建、古迹、文物、墓葬群等一系列黄河自然地理景观与历史人文画册。史前文明的圣火在三晋大地燃起,汾水之滨诞生了早期中国,晋国在此缔造了百年霸业,北朝在此经过文化融合缔造了大唐盛世,明清晋商在此创造了中国商业传奇,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讲:“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是此时。”
作为“黄河岸边的中国”系列丛书之一,贯穿《陟彼山河》的核心主线是发现三晋大地上的民族文化源地和探寻其上遗存的华夏文明根脉。芮城境内的西侯度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里有史前人使用过火的遗迹;汾河入黄河处的后土祠是海内祠庙之祖,从西汉至清末2000多年来祭祀不断,彰显着华夏文化“地母居中”的信仰理念。还有秋风楼上瞻鲁望秦牌匾,万荣县城门上的东仰泰岱、西望豳岐题额,无不显现早期中国灿若星河的历史文化。
黄河东岸的陶寺遗址与西岸的陕西石峁遗址是黄河文明的双子星座,人类尚处于万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文明遗迹。今天看来,在陶寺周围发现的城址、王墓、最早的观象台、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是探究国家产生及夏文化的重要依据。尧舜禹三代均在晋南留下深深踪迹,鸣条岗上舜帝庙高高耸立,垣曲县下辖的厉山镇同善村,有舜根、舜井、舜王坪等景观遗存,夏县禹王城安邑的历史轨迹演变,皆向我们展示晋南这片土地强有力的民族文化自信力,4000年前华夏民族在此崛起。踏上河东这片古老的土地,探寻三代先贤耕耘劳作过的土地,俯拾皆是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由此触摸到华夏民族最坚韧的文明根脉,感受到民族最强劲的怦然心跳。
山西平陆县境内黄河岸边石崖上累计5000余米长的黄河栈道上,遗留下华夏民族较早开发黄河漕运的历史遗迹,1000余个方形或长形壁孔,600余个牛鼻形壁孔,以及栈道岩壁题记200余字,河流的交通运输能力决定着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延续,从春秋始到唐代的黄河漕运都是王朝重要生命线。今天,当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踏上这段黄河栈道遗址,抚摸着栈道沿线的壁空、桥槽遗迹和历代题记碑刻,眼前仿佛看到黄河纤夫步履踉跄地行走在栈道上的历史画面,耳边倾听到他们发出的振聋发聩的黄河号子声,不由得痛惜纤夫们的血泪生活,河槽遗迹创造者的智慧,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地理景观与历史人文
黄河文明是在自然与人文双重元素塑造下而形成的大河文明,表里山河的险要地势,以及黄土高原的特殊地形地貌形塑了山西壮丽的黄河自然地理景观。逆流而上的作者们依次将晋豫峡谷、汾渭谷地、山陕峡谷黄河左岸奇丽景观呈现在我们面前:三门峡的“中流砥柱”,据说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砥柱,自古被喻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寄托着华夏民族在艰难险恶环境下敢于斗争、不甘屈服的独立精神。位于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间黄河干流上的壶口瀑布惊涛拍岸、吼声令人震撼,形成了旱地行船、壶底生烟、谷涧惊雷、彩虹飞渡、十里龙漕等蔚为壮观的黄河地理景观。黄河在中游曲折前行,像极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个性。位于晋陕峡谷南端龙门出口段的黄河大梯子崖,是依悬崖边地势开凿的“之”字形古代军事建筑,高空俯视宛如悬挂在绝壁上的天梯。津渡在黄河文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陟彼山河》中阐述了蒲津渡、风陵渡、太阳渡、茅津渡、龙门渡五大渡口。山西黄河沿岸有42个渡口,蒲津渡是连接秦晋的重要通道,风陵渡具有一渡通三省的地理优势,大禹渡是大禹导河治水、观察水势,踏勘地形之处,由此大禹上凿龙门、下开三门,治水十三年,终获成功。茅津渡是秦穆公济河焚舟,大败晋人之处。
三晋大地遗留下来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皆是黄河文明的象征,正如一位作家所讲:“黄河如一个文学大师,唯因环境险恶,才有名作连连,给后世留下阐释的残业,暗自圆缺,如姣好的月色。”三晋大地文明更迭、王朝兴衰,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却使山西境内古建保存较为完好,从寺观庙宇到城池、民居、衙署,桥梁、陵墓、石窟,各种古建都显示出建造者的匠心独运。芮城永乐宫的斗拱设计巧妙,三清殿壁画描绘的道教朝元盛况引人入胜,中华第一木楼飞云楼与应县木塔堪称奇绝,李家大院的民居建筑巧夺天工,山西大地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厚重文化,古建规模之大、构建之精美,造型之独特皆美妙绝伦,尤其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里的晋北沿黄军堡与老牛湾在晋北大地相握,是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游牧民族文明碰撞与交融的隐喻。长城一线也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分界线,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与贸易,使得中国的黄河文明较之长江文明具有更大开放性和文化纵深感。
三晋大地人文荟萃还在于作者们对黄河历史地名的科学释义。地名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见证与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黄河地名释义来自学人们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讲“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三河是夏商周三朝相继经营的文明重心地区。“河东”“河内”“河南”西汉分别置郡,秦代曾为河东郡、河内郡、三川郡。“三川”,文物资料可见又写作“叁川”。秦汉之际已有“三河”之称。刘邦集结征伐项羽的联军,称“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司马迁所谓“(三河)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强调这里是中华文明早期奠基的地方。所在经济发达的黄河中游,承受了“河水”所赐之福。
晋陕峡谷两岸人才济济,出现了太多的圣君名相、文臣武将、学子贤者、才子佳人。王之涣登上鹳雀楼吟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千古绝句,司马光祠前古冢累累、树木森森、石刻遍布。显然,文明因绵延而永庚,河东因地杰而人灵、物阜文兴。
田野考察与多元叙述
如果说对黄河左岸历史人文的追寻奠定了《陟彼山河》的历史深度,那么撰写者以考察自然、历史与人文精神及遗存,插入考察者的历史文化感知,微观的具体考证,以及宏观的历史人文神文的深入解读,从而使这部著作有了双线结构和多元叙事方式。
双线结构是指《陟彼山河》以实地田野考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构著作,力图建构起一部扎实、可信的黄河流域中华文明信史。从2020年至2023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先后组织了三次关于黄河左岸区域的沿黄考察,第一次以永济为考察起点,进入了中条山沿黄区域,从而搞清楚了中条山和晋南地区与早期中国形成的关系,考察中他们穿越中条山,足迹踏上晋南运城的许多土地。第二次由临汾的乡宁开始,沿黄以吕梁山为主轴北上考察,先后踏进了吉县、隰县、柳林、离石、临县、兴县、河曲、偏关等地。第三次是沿黄补充考察,亲临河津的历史遗迹。作者们走进黄河中游历史场域,获取了直观的历史现场感与鲜活的地方资源,在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无论是描述黄河自然景观、历史人文,还是表达考察的见闻与感悟,皆引经据典,所持论据皆有文献支撑,显现出撰写者丰赡的历史知识、精深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陟彼山河》显现出史学阐说、神文演绎、诗文补正等多种叙述方式结合的多元叙述模式,从而使著作有了更多耐人寻味的深意。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战国名士虞卿曾以大阳(今山西平陆)为封地的故事,韩信“以木罂缻渡军”的历史典故,戎子酒庄地下酒窖的蒲桃酒趣闻,重耳十九年流亡传奇、河曲娘娘滩离奇传说,河津鱼跃龙门的民间典故等。《陟彼山河》还注重神文与史料相互印证的叙述方式。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史前神话传说非常丰富,书中记叙女娲、精卫传说、牛郎织女故事、黄帝与炎帝征战往事、后土(地母)传说,以及随处可见的禹迹。黄河中游肥沃的土地资源和便利的灌溉条件,产生了最早的农耕生产方式,这些神话传说正是华夏民族处于童年时期的文化记忆。
不仅如此,《陟彼山河》还充分发挥以诗证史的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推崇史诗并重,诗歌具有史实的时间、人事、地理要素,有记史、叙述时事功能,以及补充史料缺失,匡正史实的作用,故此,《陟彼山河》中引用了大量诗词歌赋以叙述、佐证历史。譬如,描述黄河漕运遗迹时作者以《挽船曲》《挽船行》《点夫行》等诗篇,展示“邨邨逃避鸡犬空,长河日黑涛声怒”的场景;叙述秋风楼时运用了汉武帝的《秋风辞》;风陵渡的故事叙述里借用了唐代诗人许浑的诗句;蒲州铁牛的雄姿以李商隐、顾炎武等诗人的诗作来展示;最有审美意味的是,在描述晋北沿黄军堡时作者引用了唐人王昌龄的《出塞》诗、李白的《关山月》诗,从而描摹出黄土高原文化与边塞军堡文化绘就的长河关山、崖堡塞月的壮美景观,营造出“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灯火护偏关”的孤寒凄美意境。
《陟彼山河》还有意凸显黄河文化的旅游价值。全书以三十一处大景观为切入点,每一景观按照简介、知行提示、深入阐述的体例进行写作。在每一个“知行提示”中都详尽告知读者出行路线、所至景区空间距离和需要观看的景观点,图书的开本设计也适合随手翻阅、随身携带的旅行需求,并配以大量彩色图片,平添了作品的可读性与观赏性。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依河而生、傍河而居,黄河之滨王朝更迭、荣辱兴衰更替,《陟彼山河》书写出晋陕峡谷大河奔流,黄河儿女在河东大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的灿烂的历史文化,华夏民族铸就了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并昭示中华民族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创造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作者:刘宁,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