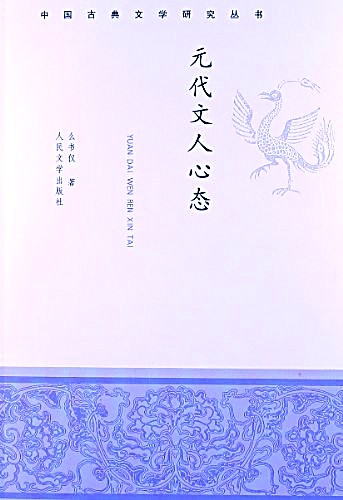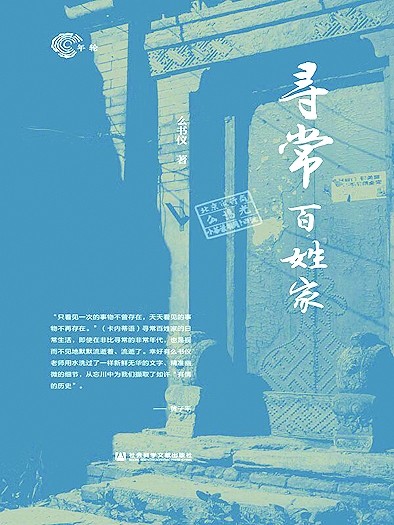么书仪,1945年出生于河北丰润。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元杂剧与元代文学、晚清戏曲。著有《元代文人心态》《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元杂剧和明传奇比较》《元曲十题》《中国戏曲》《晚清戏曲的变革》《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等。参与编辑《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另有随笔集《家住未名湖》《两意集》《见闻与记忆》《两忆集》,家族个人史《寻常百姓家》。
回望与评价一位人文学者的研究,不免以“知人论世”为前提和标准。一般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研究著作,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流行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以往当学界论及么书仪先生的两部大著《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和《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时,均将其视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学研究在不同阶段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前者是在整个社会追求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之下,对元代文人生命历程与学术追求的深层追问与探索;后者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戏曲研究主动在方法、视野上求新求变,并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融通后的成果,在戏曲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么老师另一部脍炙人口的著作《寻常百姓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则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一名学者对研究领域的选择,自然与其所受的学术训练、外部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但是也与幼时的家庭氛围和教育不可分割,更为幽深层面的心灵感触和由此触发的问题意识可能会影响其一生的学术道路。
么老师说,家庭和父母在她的生活中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自己在精神上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父母的家。在么老师的学术生涯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学术问题的提出,写作风格的形成,有可能在她正式进入学术研究界之前的36年间,已经由她个人成长过程中养成的性格、气质决定了。她的学术研究从元代一直跨越到清代,从表面看似是一个巨大转变,但内里自有另一条力量强大的精神内核将其串联起来。
数数儿
么老师1945年出生于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韩城镇刘各庄,1947年随父母迁居北平,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新疆奇台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其后分别在新疆乌鲁木齐、河北隆化县担任中学老师。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她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届研究生,师从邓绍基先生。1981年,么老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主要专业方向是古代戏曲。
从1981年至2006年退休,在这25年中,除上述两部代表作之外,么老师还出版有《中国古代文体丛书·戏曲》(1994)、《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元杂剧和明传奇比较》(1997)、《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1997)、《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2009)等多种专著;又参与编纂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和《中国文学通史·元代文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元曲鉴赏辞典》等反映了时代学术风尚的大型学术项目。她对成长、教育、工作、家庭等人生经历的追忆,则结有《两意集》《两忆集》《见闻与记忆》《家住未名湖》等随笔集。在2022年出版的家族口述史著作《寻常百姓家》中,么老师以她为父母亲录制的36盒录音带访谈为素材,细致入微、情真意切地勾勒了一部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百年家族史。
我读么老师的作品,甭管是学术著作还是随笔散文,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折服于她的记性之好。比方说,她在多年后还记得小学一年级同伴的名字,能准确数出8岁搬离小茶叶胡同14号时卖的家具:架着大条案的两个架几、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四只方凳……再比方说,她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文艺理论课和俄语课考了3分,中国文学史课和古代汉语课考了4分……有的数字非常精确:父亲花383元为母亲购买了一块手表;为筹集上大学的花费,她勤工俭学21天挣了10块5毛钱……性格的敏感与感知问题的敏锐,最直观地反映在具体数字上。从《寻常百姓家》对往事的记录中,我们知道这一特点遗传自她的父亲么蔼光先生。
么蔼光本是一个出生于刘各庄的农村小青年。20世纪30年代,他为自己选择了新的生活——去大城市,利用自己在记忆和心算上的天赋,在北京、唐山、天津的市场做“股票”。他成功了,由此得以“旱地拔葱”,举家搬到了北京,也由此形成了对现金、账目、股票近乎执拗的记挂,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记账。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71岁高龄的么老先生重操旧业,研究股市,很快就可以对300多种股票的行情涨落倒背如流。
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黄金时期,雨后春笋般的论文、论著旨在逐一梳理经典作家作品,重新绘制中国古代戏曲史的整体面貌,着意建构中国古典戏曲学自身的文学理论和艺术美学。这一系列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摸清古典戏曲剧目的家底,于是和各种各样的“数字”产生了莫大的关系。从戏曲目录学的角度来说,古代典籍中记录的曲目的名称、曲本的版本状况、曲家的作品数量、演员的行当,决定了后世对古代剧本创作和演剧基本面貌的认识。么老师对“数字”的敏感和执着,帮她推导出了“平阳是元代杂剧的摇篮”等一系列基本事实,奠定了《戏曲》一书对中国戏曲整体发展脉络叙述的基础,决定了《元杂剧和明传奇比较》对元、明两个不同时代戏曲特征的分辨。从戏曲文献发掘和整理的角度来说,“数字”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她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的编纂中:作为一种对孤本、珍本求全责备的大型戏曲总集,《丛刊》五集中收录清代杂剧曲本的数量、篇幅,对版本年限的判断、作者生平交游的考订,无不需要对相关数字作出清晰的认定。
最为重要的是,对戏曲相关“数字”的关注和积累,让她形成了特有的戏曲史观。清代宫廷演剧是21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引发了戏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当时,记录宫廷演剧情况的升平署档案等一手文献材料较难获取,2003年、2004年,么老师在《文学遗产》杂志上一连发表了两篇商榷文章,针对一名学者在研究乾隆时期宫廷演剧问题时引用材料不够准确的问题提出批评,对其著作中宫廷演员数量的统计标准和方式发出了质疑。这两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全是关于如何“数数儿”,方法不对,谬以千里。清代宫廷演剧中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都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统计方式,准确、详尽的数字和表格足以影响学界对清代演剧基本面貌的认识和判断。
较真儿
在我看来,“真”,是最适合形容么老师的一个词儿。“真实”是么老师对学术和写作的追求,“真诚”,则是对她个性和心灵最恰当的评价。么老师以“不虚美,不隐恶”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她的爱人、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在《寻常百姓家》序言中说:“本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坚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信条,真实是认识的前提,也是最高标准。她确实也是按照她自己对‘美’‘恶’‘真实’的理解来处理所写的生活情境的。”“真”是贯穿么老师的人生的一个基本态度,“有时认真得有点过分”,就成了“较真儿”。
“较真儿”反映在么老师的写作和研究中,是对材料、文字、观点的不断审视与打磨。如何收集和处理写作对象的相关文献,是对“真实”的第一重考验。《寻常百姓家》中涉及的文献资料,除了么老师为父母亲专门录制的录音带,还有“档案”、信件、账单、收据、工分本等。为了最大限度达到“真实”,么老师对这些材料,还不厌其烦地查对,找知情人反复核对事件发生的日期和细节。么家举家迁居到北京后,租住在小沙果胡同1号,当时的房东刘大中,据么老师父亲回忆,曾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么老师为此专门到清华大学档案馆,翻查到了刘大中1947年和1948年领取物品的签字。在原本的设想中,《寻常百姓家》是一部较为轻松的非学术作品,但她在写作时也带有记录历史真实的苛刻“自觉性”。她对待学术著作更是如此,在退休十多年之后,2017年10月,《戏曲》一书收入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丛书,易名为《中国戏曲》再版。么老师亲力亲为,一一核实书中的注释,还多次到同小区的邻居、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简教授家中查阅原书,核对引文。
“较真儿”也反映在么老师对待戏曲版本的态度上。20世纪80年代初,在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的特别关心和多次呼吁之下,中止了20余年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纂工作得以重启。承担出版任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要求对第一次送去的文稿重新查找版本,并对作者、版本进行考订。主编吴晓铃先生年事已高,么书仪与同在文学所工作的吕薇芬老师临时受命从事《古本戏曲丛刊》的具体编纂工作。对么老师来说,她的学术志趣原本并不在于参加这种大项目、大工程,不过受邓绍基先生指派,加之和吕薇芬老师同是北大中文人,有作为“姐们儿”的相投和默契,她全情投入,“较真儿”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郑振铎20世纪50年代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原本计划出版十集左右,出版四集后,因郑振铎意外逝世,戛然而止。《丛刊》第五集编纂命运多舛,80年代项目重启后,条件与郑振铎作为文化部副部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主持这项工作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吕老师曾说,做《丛刊》的心得是“搞版本你非得摸在手里”,为了“摸在手里”。她们俩的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济南等地多个图书馆。她们按照吴晓铃先生制定的《〈古本戏曲丛刊〉作品调查表》,详细记录每部作品的署名、撰人、时代、藏家、书号、刻家以及长、宽、叶数等版本情况。么老师说:“版本的问题最麻烦:如果是刊本,是哪一朝的刊本?是家刻还是坊刻?如果是抄本,是家抄本、传抄本还是稿本?这些都要弄清楚。”每发现一处错简,每找到一个年代更早的版本,她们都会感到“好高兴啊”。出于对自己认真、严谨工作的自信,在责任编辑府宪展追问“为什么这样编排”时,吕老师特有底气地回复:我们当然是有根据的!
较真儿,在具体写法上,对如何谋篇、如何表述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以“较真儿”的态度求“真”,本身也是对自我记忆和深层心理的拷问。么老师的女儿洪越在《寻常百姓家》序言中写道:“妈妈写姥姥姥爷的一生,涉及很多在世的亲人,不可避免地,对一件事的记忆,叙述上的取舍,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对此,洪子诚老师曾谈及此书写作中的“真实”标准问题:“在她最初确立的真实坐标上,有的地方标准有所降低。‘降低’当然不是说真假不辨,以假乱真,而是说有所节制。”他们一家在欧洲的旅途中,还在讨论此书文字的删削。
人文研究者的对象是“人”和“文”。对于文本的解读,阅读者个人的经验、情绪和感受,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也引导着么老师进入了元代文人心态和晚清戏曲变革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议题。“心态”,本来是最难以落实为文字的。对世情和人情的体味和把握,却又反映了么老师对“真实”的执着和“较真”,也让她无论是对元代文人、元杂剧的作者,还是对清代“男旦”演员,都是同样带有平等的、设身处地的同情之理解。
她在《元代文人心态》中,对元代文人复杂的思想、心理世界和行为、情感矛盾的书写充分而且细致,由此延展到对元杂剧作者的分析:他们在作品中同时展现出对出将入相、富贵荣华的渴慕、追求与对等级制度、豪门权贵的揭露、抨击,所反映出来的是立场、心态的摇摆。在评价元代杂剧的作者和剧中人时,她说,元杂剧的情节和结局的处理,并不能与封建伦理教条的规范相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结局也不理想,《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的宋引章、《诈妮子调风月》中的燕燕等女性的形象不够完美,要么过于世俗,要么堕了志气。对于元代作家思想上的局限性,她认为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书会才人对市井百姓的实际生活情景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对笔下女性角色所做出的不那么理想化的选择,持有一种宽容、通达的态度。这样的解读,在当时是别具一格的,今天的我们读来,也会感到具有相当的前沿性。
1999年,么老师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转向,发表了研究晚清戏曲的第一篇论文《明清剧坛上的男旦》,首先聚焦的仍然是戏曲研究中刻意回避的敏感人物和话题。歌郎、男旦、堂子和打茶围,一度是学界避而不谈或含混带过的现象,却是明清演剧史上一个普遍的存在,也是晚清演剧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北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效应:晚清堂子的发达,直接推动了北京南城作为娱乐中心的发展,与京剧成为时尚艺术互为表里。在么老师看来,演剧史中被遮蔽的,理应被重新挖掘和重新叙述。
懂行儿
戏曲是文本与舞台结合的艺术,戏曲研究者最好能通表演、通演唱,方能对戏曲有一个通观的认知。么老师爱唱、能唱、懂唱,也有来自家族的基因和遗传。她的父亲是票友,常常和母亲一起到前门大栅栏看戏,还专程到天津“追”谭富英,家中还藏有时慧宝题写的扇面。她哥哥小时候就会拆开口琴自己组装,中学时是学校民乐团的指挥,在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京剧团里票戏唱老生。
么老师自己高中时迷上了京剧,对登台演唱也并不陌生。在北大念书时,她参加了学校京剧队,唱过《二进宫》《红灯记》,曾与金开诚、裘锡圭二位学者一起表演《沙家浜》。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63年,她大学一年级给老师们拜年时,与吴小如先生对唱《打渔杀家》。因为熟悉表演,她对戏曲的体会超出了纯粹由文字阅读带来的感受,分析文本、演员与戏曲的发展,也就自然有了新的视角。她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元杂剧和明传奇比较》一书里,就显示出对曲本之外的世界颇感兴趣: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元杂剧戏班的演员人数,从《四友斋丛书》里严嵩对教坊乐工的打赏金额来考察明代演员的收入,又从传奇体制的角度,提出明代戏班的结构不再是以一个旦角或末角为中心的家庭戏班,而是根据演出需要,各种角色的搭班合作。
《晚清戏曲的变革》在戏曲史研究中是一本具有开创性意义和里程碑性质的学术著作。从学理上来说,它不再将戏曲视为案头的“死文学”,而是把围绕着戏曲舞台演出的方方面面都纳入了戏曲研究的视野之中。王艺先生在此书的书评中写道:“走出文学进化史的思路,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在社会生活史、娱乐史的视野下,我们绝对难以跳过‘打茶围’‘堂子’这样奇突、复杂的历史元素来谈论文学史。”如么老师自言,她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下的晚清戏曲,立足点并不是文学文本,而是和历史演进、社会变革同步的演剧和戏曲环境。戏曲,在文学史上是文学,在戏曲史上是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是娱乐,是消费,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来观察,才能完整感受它灿烂的光辉。
如果我们沿此继续追溯么老师对晚清戏曲变革中一些重要的学术判断,就会发现,这种“多棱镜”的观照贯穿在她的整个戏曲史观之中。比如,宋代以来,戏曲被认为是流行于民间的俗文学、俗文艺,基本不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戏曲的影响。金元是戏曲发展的高峰期,个中缘由,么老师有过这样的论断:辽金元入主中原,在一般汉族人看来都属于历史的非常时期。契丹、女真、蒙古这些马上民族,给中原带来剽悍的习俗和粗犷的风气,胡语、胡音俨然成为正统语言,唱胡曲、跳胡舞也成为习见的娱乐和技艺。这种变更和取代,不再是缓慢渗透,而是迅速漫衍,擅盛一代。由于有政治权力作为后盾,这时候,影响和接受的进程和强度,当然就更为快捷和凶猛。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有时候会影响一代人的好尚和风气。她从戏曲史的发展着眼,跳出了单一中心的思维模式,这是出于对戏曲这一种艺术形式的深刻了解:从戏曲的特点出发,必须以动态的思维来对待戏曲,戏曲是不断变化、不断适应、不断提升的。明代的祝允明在《猥谈》中批评南戏盛行的“无端”,有“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而这正是戏曲为民众喜闻乐见,数千年不衰的关窍所在。
起范儿
么老师的学术著作和随笔散文有一个共性:以不疾不徐的笔触娓娓道来,平静的文字之下从不隐藏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褒贬态度,蕴含着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
么老师正式从事学术研究是36岁研究生毕业之后,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投身学术的二十余年中,她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所从事的文学研究,都凝结为具有高度个性化的写作。学术研究有天赋和才华的影响,也与人格和性情密切相关。么老师曾在《回忆我在文学所研究戏曲的往事》一文中提到,她研究戏曲谈不上是什么“选择”,而是一种境遇使然。么老师自谦,选择元代和晚清的戏曲研究,在当时是出于资料便于获取等现实的考虑。但是,看似并非个人自主选择的题目,却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最终展示出一种纯乎“性灵派”的整体风格。《元代文人心态》关注文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复杂心理和性格矛盾,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元代杂剧与元代社会》对元代杂剧的作家和作品研究,都是围绕着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不难发现,她对复杂的、社会的议题具有浓烈的兴趣。她本人在多年前就总结过:社会现象,以及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情绪,是不可能自动进入作品中的。学术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思考和结论,是研究者长期观察、体验、感受的结果,自然也带出了研究者本人的审美和心理。
在进入学术界十五年之后,她在五十岁知天命之际,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将研究重心放在晚清戏曲。当时,清代宫廷戏还完全不在学术界视野之内,以社会学的方式来看待演剧也还是一片荒芜,任由她“开疆拓土”。其中自然有她的学术敏锐性和兴趣驱使,无疑也有着来自父亲的影响,受到了大胆、独立的个性和内心喜好的驱动。
老一辈北京人总是很在乎和赞赏一种“范儿”。在学术研究一途,什么是学者的“范儿”,很难用职称、级别或者项目、人才“帽子”来衡量。“范儿”,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讲究”,即对自己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对学术的执着和坚持;其次是一种人格魅力,一种发自内在的坚定和力量,引导着对人生意义和生命厚度的持续追问;再次,我想是一种人文情怀,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不会失去对真、善、美的信心和追求。
么老师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大时代风云中的普通人。如么老师自言,她的一生,无论是生活、事业、还是为人处世的规矩、习惯,那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大都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认真、坚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难的是知行合一、坚持始终。母亲离世前,她在给母亲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母亲的教诲“气是清风”,这一股清风,也借由么老师深情的文字,吹拂过晚辈研究者的心头。
2006年11月,年过花甲的么老师从文学研究所退休。她没有“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所以并没有亲自指导的学生传承她的学术衣钵。不过,她关于元代文学和清代戏曲的学术思考,在近20年的元代文学和清代宫廷戏曲研究中都得到了再三挖掘和深化。她的人格魅力、学术涵养,也在她陆续到东京大学、东吴大学、彰化师范大学讲学后,得到海外学生们的交口称赞和真诚崇敬。我很喜欢《寻常百姓家》中的这么一句话,“几十年过去了,在我们都体验过人生的冷和暖之后,才知道母亲说的那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话,都是经过验证的人生的道理(人间其实也就是那么点道理)”。《寻常百姓家》所附书签上印着:“真正能穿透时间,是常情常理的韧性和普通人的坚持。”认真、坚忍,正是这样一些古朴的特质,支撑我们每个人,支撑我们民族的文学与文化,走得更远、更长久。
(作者:李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