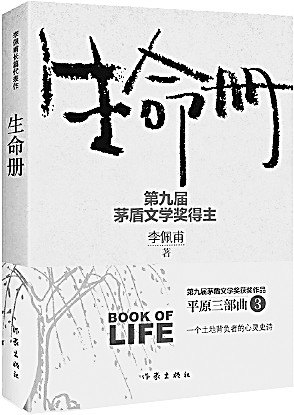是五年前的事了。
那个电话很突兀,来自西安。西安?我有些迟疑。那边马上说:“我是陕西人艺的,是从陕西省作协要到了您的电话,想跟您谈谈《生命册》改编话剧的事宜。”我心想,拙作《生命册》改编成话剧是不可想象的。可她说得那样诚恳,那就谈谈吧。不料,话音未落,她说:“我们已经到郑州了,想去看您,可以吗?”到郑州了?我愣住了,这人“出马一条枪”,是个响快人。
初见面,女子短发,秀丽飒爽。她说她叫李宣,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过兵。接着,她背了一首艾青先生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被震动了。她说,《生命册》她是夜里读的,读得泪流满面。她还说,他们陕西人艺改编演出过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是有光的。接着,她说了一句:“我们是排‘良心剧’的。”我当即就应下了。
《生命册》是一部切入方式较为特别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近五十年的心灵史,是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写一个大名叫“吴志鹏”、小名叫“丢儿”的孤儿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精神成长史。从戏剧的“三一律”来看,它的时间跨度太大,重要人物太多,在舞台上几乎是无法呈现的。况且,这部小说,我把它称为“树状结构”,就是把一个人内心的思想“流动”作为树的主干,主写一个人身后的“背景”,在一个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里,呈现一个文字的“气场”。“背景”是身后的三千张脸、六千只眼睛、五千七百多亩土地,还有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尔后扩而大之,主写一望无际的平原,写人与土地、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写一花一草一树……而且,他走得太远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文字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在具象的话剧舞台上,时空该如何衔接?再说,这片古老的平原,艺术家们真能走进去吗?
一个月后,李宣院长又来了。
这次,她带来了一支队伍——几乎是一个创作班子。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国家一级导演宫晓东、国家一级编剧李宝群,还有响当当的舞美、音乐设计等一众大腕。天已冷了,李宣院长让我引领他们深入生活,去走平原。一行人走在西伯利亚寒流中,看平原上飘落的黄叶。细雨蒙蒙,在寒风中,哈一嘴白蒙蒙的气。
李宣院长巾帼不让须眉,组织起了一个在国内堪称一流的创作班子,俯下身子深入生活。她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服了。
作为向导,我引着李宣院长带领的队伍一连走了三个县。
天是冷的,心是热的。过镇串乡,走集市,喝羊汤,看乡人磨豆腐,学编席,边走边聊,拊掌大笑。迎着无遮无挡的凛凛寒风,盯着乡间瓦屋的兽头看荡荡落日……临分别时,李宣院长信心满满地说:“明年请你来西安看话剧!”
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这是困难的三年,是全国各地共同抗疫的三年。前前后后,五年过去了。有时,遥望西安,我会想,这也太难了。
然而,这些年里,几乎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接到李宣院长的电话。她告诉我的,全都是好消息:话剧的创作班子已经开始工作了,宫导和宝群都来了,上级领导很支持;剧本正在修改中,北京的专家很认可;剧本立住了,方方面面都在进行……我不知道她遇到了多少困难,从她的声音里是听不出来的。有时我会想,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呐。记得她说过,她是当过兵的。
我是在北京天桥剧场看话剧《生命册》的。这是“大戏看北京”的闭幕演出。陕西人艺的李宣院长,把话剧《生命册》带到北京来了。
整整五个小时,人们一直在剧场里“钉”着。陕西人艺真的把过去和现在、背景与现实同时呈现在了具象的舞台上。这也是在纯艺术领域里,来了一次时空大挪移,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当是话剧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的又一次飞跃!
在舞台上,话剧《生命册》的时间和空间是广阔的。编剧李宝群先生再现了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吴志鹏。应该说,是宝群先生给了丢儿一张脸,那是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让他背着老姑父,背着虫嫂,背着梁五方,背着杜秋月,背着六千只眼睛、五千七百多亩土地,一同活色生香地出现在了话剧舞台上,让他背着家乡走南闯北。
在话剧舞台上,一个背负着家乡沉重包袱的孤儿,从乡村走向城市,跟着绰号为“骆驼”的昔日同窗闯天下。他是渺小的,因为他是一粒移栽进城市的种子;他也是强悍的,因为他有整个乡村为依托;他是卑微的,但他同样渴望爱和被爱。他进城了,成了从家乡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渴望报恩,渴望给予,他深知给予是高尚的,索取是卑微的。可是,他人生的包袱太重,他没有给予的能力。在舞台上,他的人生节奏先快后慢。他被一个大时代裹挟着,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他在前行中迷茫,在迷茫中迟疑,在迟疑中思索,他既有广阔的人生空间,又困顿在一个个无形的精神牢笼之中。他在前行中挣扎、思考,一直在寻找“让筷子立起来的方法”……他想回去,可他回不去了。
在话剧舞台上,导演宫晓东先生用他的激情一次次点燃了整个剧场。宫导的导演风格丰富又细腻,整个舞台深沉宽广、复杂多变、耐人寻味。轰隆隆的时代变迁、众声喧哗的城市和乡村、历史对个体生命的裹挟、个人与不可知命运的抗争、温馨的日常与狭隘的戾气、轻松的讽刺与沉痛的悲悯……一轮不停旋转的转盘、几把来去如飞的椅子、舞台深处摇曳的芦苇……在他的调度下,一切灵动而自然,细致而宏大。
宫导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骆驼。骆驼是吴志鹏很重要的人生参照系,也几乎是他的引路人。骆驼是精明的,也是一个身心都有残疾的智者。他最先预见到了一个大时代的到来,怂恿吴志鹏辞掉大学教师的铁饭碗,从北漂“枪手”开始,到股票操盘手、证券经纪人、上市公司老总,一步一步带着吴志鹏成了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就像骆驼说的那样,一个大时代来到了,经济与世界接轨了,可我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在市场经济领域里,我们没有“标尺”。“标尺”是人家的,“红绿灯”也是人家的,有什么办法呢?“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抢,必须抢!
导演宫晓东先生,通过舞台上骆驼的表演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骆驼,都渴望或曾经渴望成为骆驼。骆驼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在他身上,悲剧的种子是一开始就埋下的,是藏在血脉里的。最后,拥有亿万资产的骆驼从十八层大楼上跳了下去。杀骆驼的是他自己,是他精神上的贫穷。骆驼不是坏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一个个活在“背景”中的人。
五个小时的话剧,是极为考验艺术表现力的。话剧《生命册》创造性地在舞台上复盘了一个个生命的成长与凋零,以及寻找灵魂的过程……那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是我们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剧中每个人物的再现,都有着令人信服的张力和表现力。整出剧的舞美、灯光、音乐,也无一不体现了陕西人艺尽善尽美的追求。“阿比西尼亚玫瑰”的歌声是深情的告白,贯穿始终的鼓声敲击着灵魂,犹如警钟在我们内心一次次地敲响: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保罗·策兰的一句诗,以此与陕西人艺《生命册》的全体演职人员共勉,并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数一数杏仁,数一数那些苦的,让人醒着的杏仁,把自己数进去。”
(作者:李佩甫,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曾获茅盾文学奖)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