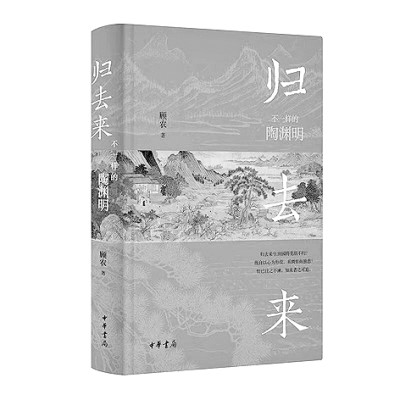陶渊明,被称为隐逸之宗。虽然昭明太子萧统已为其编辑了较为完整的集子,然而关于陶渊明生平的文献却极少。关于陶渊明的生卒、仕隐等信息,世间存在不少争议。这些争议影响了对陶诗陶文的正确解读。其中特别关键的就是,陶渊明为何多次出仕、迟迟而归去来?他对东晋被刘宋取代的态度如何?戴着有色眼镜去读陶诗陶文,往往会将其艺术与思想的境界缩小,从而引发误会。
顾农先生的新著《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以下简称《归去来》),是近年来解析陶渊明的力作。作者通过传记与诗文、思想解读的结合,尝试为我们清除迷雾,还原真相。
本书曾引述鲁迅先生研究魏晋风度的一句话:“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若以此来评判本书,则是详尽地占有文学与历史的各种资料,周密地解析全部陶渊明诗文,然后又以严谨的考据与诠释,呈现出与旧说不同的真实的陶渊明。
再说《归去来》一书的构成,分为上下两卷以及五则附录。在我看来,其核心就在上卷《陶渊明的人生》,大体完整地告知读者,几度出仕又几度归隐的陶渊明的真实人生,作者的主要观点基本包括在其中,原本也可以单独成书。而下卷《陶渊明的诗文与思想》则是分别从陶诗、陶文以及小说家、家庭教育等方面为上卷再作补充,丰富而立体地说明其人其文之不同侧面。下卷还有第十一章《陶渊明的思想与艺术》与第十二章《陶诗陶文选析》,可以看作本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前者讨论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与如何在艺术上复古而开新;后者包括31篇短文,对陶诗陶文进行具体而细微的赏析,大体囊括了陶渊明全部重要的作品,其中也多有对疑难问题的考辨。如果再增加一些关于诗文创作技巧,也可以单独出书。所以说,《归去来》一册,乃为顾先生关于陶渊明的传记、思想与艺术研究、作品赏析三合一的精华荟萃。
为了认识陶渊明的真实人生,本书抓住了与之相关的四个重要历史人物,将其关系网络说明之后,其实陶渊明本人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已经一目了然。一是其曾祖父、寻阳陶氏始迁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封长沙公,他的一生从低级小吏做起,最后做到“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的权臣,事实也暗暗生出不臣之心,只因上了年纪而功成身退。陶氏家族渐趋衰弱,陶渊明的叔叔陶夔还担任过尚书,推荐他担任彭泽令的就是这位叔叔。陶家,其实与此前的琅琊王氏及当时的江州桓氏一样,都曾是掌握权势的大士族,他们都不见得会对东晋王室特别忠心。二是外祖父孟嘉,原本是陶侃的女婿,故与陶家是亲上加亲的关系,他先事于庾亮、庾翼,后事于桓温,陶渊明的初次出仕就与他有关。三是桓玄。江州桓氏先有桓温,乃是孟嘉的府主,陶渊明对其持有相当的敬重。桓温的侄儿桓玄,则是陶渊明出仕服务多年的府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桓玄取代东晋一度建立“楚”政权,并将晋安帝司马德宗安置于寻阳的时候,正好遭遇母丧回乡守孝的陶渊明对此不置一词,感情上明显向着桓玄。四是刘敬宣,其父为北府兵名将刘牢之,后来击败桓玄而成为南朝之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也曾是刘敬宣的部下。陶渊明在刘裕幕府短暂担任参军之后,就在刘敬宣的幕府担任参军,并且为期较长。无论刘牢之、刘敬宣还是刘裕,其实都是与桓玄目的相似的权臣,晋安帝也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而已,至于陶渊明在他们手下的几次出仕,目的只在养家糊口。至于东晋王朝,原本就是士族们扶植起来的政权,先有“王与马共天下”,后有陶侃、桓温、桓玄以及刘牢之、刘裕,原本就不像一个王朝,又有什么为之“忠愤”的理由呢?
此外,推翻“忠愤说”的另一个小证据就是陶渊明归隐之后,曾两次得到朝廷的征聘,故被称为“征士”,一次是在东晋末的义熙年间,另一次则在刘宋王朝的元嘉四年。在萧统《陶渊明传》中说其“将复征命,会卒”,也就是说,改朝换代之后请陶渊明出山,他本想同意,可惜不久去世故终未出山。本书对后一次征聘的考辨,无疑进一步说明了“忠愤说”的荒谬性。
陶诗陶文的细读慢品,则更可以说明决定其人生选择的性格特点。本书结合《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各本宋版《陶集》中皆为“一去三十年”,考证出其20岁左右就第一次出仕,任职于江州刺史桓伊,主要负责在外地执行公务,这是相对自由的职务。后来担任江州祭酒则比较拘束,故为时较短。“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不习惯于在衙门里看长官脸色,为长官折腰,至于担任参军之职为时较长,也因此职务多有外出而相对自由。至于彭泽令则有不同,除了上有长官,还有督邮前来检查,故80多天之后挂冠而去。他在诗中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因为“亲老家贫”之故,不得不多次出仕“代耕”,但其平生志趣皆不在此,生活方式也不能兼容。“质性自然”,无奈之下盘桓于出仕与归隐之间,正好进入一个螺旋形怪圈。
诚如《归去来兮辞》所说,程氏妹丧于武昌与应束带见督邮二事,成为陶渊明最终彻底归隐的两个直接理由,但其根本还是因为久已厌倦官场,且有可以养活全家的资本了。另一说法则是他预感到了改朝换代而逃离。就东晋长期的混乱而言,即便改换也无碍于只求“代耕”的出仕,更何况对晋朝本无好感。本书特别指出,陶渊明的最后归隐,其实还是“结庐在人境”,他的归隐方式与常跟其交往、怀着复杂心态的“寻阳三隐”等人不同。他的隐居是世俗的,不必遁入山林,而是回归园田;不必隐于僧道,而是以儒为宗。所以,才有诗句“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他过的是士人兼农夫的正常生活,无须如嵇康、阮籍那样咬紧牙关不开口。他可以随便话桑麻、写诗赋,还可以务农、读书、饮酒、访友。只要离开了羁绊重重的官场,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洒脱了。
陶渊明的诗文,似乎多有矛盾之处,他会告诫世人:“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他也会安慰世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如何呢?生活在人间的真实的陶渊明,其实就是该种豆且种豆,该饮酒且饮酒,是一个生活在人间的隐士,并不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官场是非而闹心,故而扬弃了北宋方才出现、明清注家无限扩大“忠愤说”等曲解,贴近平常人生的理解,才能贴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平视,才能看清陶渊明这位大诗人,他既热爱生活,又视死如归;他除了忠诚于生活本身、忠诚于自己内心之外,从未有过其他忠诚,故也从未有过任何悲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世俗,同时也是最真、最纯的隐士。
除了结合对“忠愤说”的辨析,以及平视陶渊明的诗文与人生之外,本书还针对许多具体的问题加以还原。比如详细解释《述酒》全诗,为其翻案;再如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中指为伪托的《五孝传》和《四八目》以及《搜神后记》的辨析,特别是《搜神后记》,本书从其辑本多篇小说出发,指出与《桃花源记》的密切关联。陶渊明原本就喜欢神奇洞府故事,这也与其隐逸心态一致。于是,作为小说家的陶渊明,便更加可爱而完整了。
(作者:张天杰,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