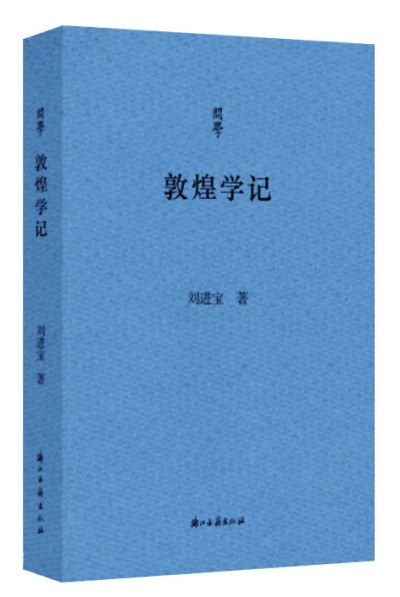【著书者说】
长期以来,敦煌很“热”。自然而然,关注敦煌学的人也多。然而,深究起来,何为敦煌学、其内涵与外延囊括什么,非长期研习的学者难以道明。笔者以为,向读者普及敦煌、普及敦煌学,是吾辈学人在对敦煌做深入研究的同时,所肩负的任务之一。实际上,社会各界对敦煌学普及读物的需求也客观存在。如潘絜兹先生《敦煌的故事》,虽然只有5万多字,但自1956年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喜爱,发行量很大。再如1988年第8期的《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也是广受好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敦煌更受关注。当浙江古籍出版社策划“问学”丛书时,我便将一些知识性短文、学人介绍和学术论著的评介等编入了一个小册子——《敦煌学记》。学记出版后,得到了读者喜爱,一年后又重印发行。在此背景下笔者应邀撰文,对学记所涉内容略做介绍。
敦,大也;煌,盛也
作为一本普及性知识读本,首先应提供准确有据的知识。
笔者在书中完成的第一项任务,是溯源与廓清何为“敦煌”。《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一文指出,敦煌最早见于《史记》《汉书》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乌孙“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应劭对“敦煌”的解释是:“敦,大也;煌,盛也。”将“敦煌”取义为大盛,这并非实指,而主要是说汉代敦煌的兴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一解释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西域地区有重要作用,因此而得名。可见,对同一个地名、同一件事,不同时代会根据当时情况做出不同解释。
从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笔者对敦煌作了这样的界定:“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而敦煌就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走向辉煌的。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其走向如何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
书中《“五凉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学》一文,则阐述了敦煌学的基础与背景。所谓“五凉”,是指西晋末年北方各民族统治者相继建立的政权。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张氏、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和北凉沮渠氏这五个政权。五凉文化,则是指这些政权创造的文化。它们不仅继承了汉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渐趋成熟。敦煌的文化与艺术,正是在五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还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成为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如大家所知,今天的敦煌,只是中国西北偏远一隅的一个小城市,规模既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相比,也不能与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并论。但是,世界上却没有“北京学”“伦敦学”。为什么敦煌会如此特殊,能形成一门以地名而命名的国际显学?
在汉唐长达千余年的时光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则在西北。而西北对外交往通道只有一个,就是“丝绸之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在今甘肃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设置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西面建立玉门关和阳关。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即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或作为网络状不断变化,从长安到敦煌可以有好几条道路,从敦煌进入西域后也有北道、中道和南道等,但敦煌,几乎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因此,敦煌成为彼时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也具有了以地名命名学科的条件。
学理再辨
《敦煌学记》所收录20篇小文,从不同视角对敦煌学做了介绍。
如《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一文,梳理了几十年来学界对敦煌学概念的研究历程。文章指出,虽然敦煌文献发现已经120年了,但学界对这门学科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对象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学界或称其为“敦煌学”,或称其为“敦煌研究”,或称其为“敦煌文献研究”。即使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对其涵义及研究范围、学科性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敦煌文献的内容非常广泛,古代学术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有反映或记载,如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学、宗教、法制、科技等等。敦煌石窟,是壁画、雕塑和建筑三者为一体的艺术宝库,尤其是敦煌壁画气象万千,被誉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敦煌史地,与吐鲁番学、简牍学、西夏学、丝绸之路学、西北史地学等密切相关。敦煌学理论,除了传统的艺术、历史、语言、文学研究外,内涵与外延也随着时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敦煌学界,有一个大家熟知的观念,即从1981年开始国内流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并指出这是日本学者藤枝晃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演讲时说的。笔者在西北师范学院学习时,正好聆听了那场讲座。后来在1987、1988年,也与藤枝晃见面座谈聊天。听闻藤枝晃曾解释,原话不是他说的,他只是转述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笔者溯源发现,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已经有代表提出,“敦煌学”在国外已成热门,“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书中《“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其反响》一文,是对这一说法来龙去脉进行的辨析。
敦煌学的产生,是因为1900年在莫高窟发现了约6万卷古代文献。发现敦煌文献的第17号窟,就是一般所说的藏经洞。本书所收《千古之谜谁解说——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一文,对此做了比较清晰的介绍。藏经洞是凿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一个小窟。它面积不大,窟内地面近于方形,地面四边的长度是:东壁2.75米,北壁2.84米,西壁2.65米,南壁2.83米。由于四壁向窟内略倾,故四壁顶部的长度较地面处为短:东壁2.49米,北壁2.55米,西壁2.57米,南壁2.46米。各壁的高度也略有参差。窟内除去低坛占去的空间不计外,它可利用的空间只有19立方米略多一点。
藏经洞原为洪[~符号~]的影窟(纪念室),后来变成了收藏寺院经书和其他文献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藏经洞是什么时间封闭的?其原因又是什么?百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假说。经梳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避难说——逃避敌人侵扰,其中又有避西夏之乱和避黑韩王朝之乱等意见;废弃说——所藏的都是一些已经无用的东西;排蕃思想说——藏经洞原来的窟主吴洪[~符号~]是吐蕃到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北宋时期敦煌寺院中保存的旧经典、旧文书中很多东西都与吐蕃有关系,所以就封存起来了;佛教供养法物说——分存在各个寺院的经书及法物需集中起来供养;经像瘗埋说——对残破、过时的佛教经典与造像有计划地、礼仪性地收集瘗埋。
除封闭原因外,藏经洞是由何人封闭,封闭时间和原因是什么,学界也众说纷纭。由此也知,虽然藏经洞发现120多年了,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来者解决。
“莫高人”,敦煌情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是莫高窟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
本书中《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常书鸿:暗夜中不灭的烛光》《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和《孙儒僴先生谈敦煌与敦煌学》等文,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莫高人”的敦煌情。
看了先辈学者常书鸿的传记后,笔者写到,常书鸿在他那个时代能从法国巴黎到敦煌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去工作,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这在今天是无法被理解的。就算现在敦煌的条件已经好得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我们好多学者也不愿意去敦煌工作。而常老,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几十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到兰州后和他离婚了。除了研究环境的艰辛之外,他还遭受了来自家庭的打击,但常老毅然选择了坚守敦煌。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佩常老。
近百岁的孙儒僴先生,晚年移居兰州后,让他魂牵梦萦的是敦煌。他说:“莫高窟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怀念,人离开了,心却离不开”,“我心永远在莫高”。
有人问百岁老人万庚育先生:“从北京大都市来到敦煌几十年,你后悔吗?”万庚育果断地说“我不后悔,自1954年我和(李)贞伯决定从北京到敦煌莫高窟那天起,我们就没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我们热爱敦煌艺术,能在世界瞩目的莫高窟工作,学习传承研究弘扬敦煌艺术,是多么荣幸!”
回想起来,常书鸿先生也曾说:“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看了这些敦煌老人的故事,确实很感慨。“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我遇到这些情况我会怎么样?能否坚持?我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撰写学记里这些文章的过程,也是笔者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深省。
相较于那些先生而言,我对樊锦诗老师比较熟悉。从樊老师的自述可知,她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同班同学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1967年1月他们在武汉大学结婚。因为家庭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樊锦诗也曾尝试离开敦煌,但都没有成功。当樊锦诗决定留在敦煌时,她就意识到:“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樊锦诗说,“我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我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我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
笔者在看樊锦诗的自述时,就感觉像和她在聊天一样,没有造作,也没有拔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在《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一文中,笔者写道:“对于个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如果能做到‘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就算成功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樊锦诗先生有多年的接触和交往,读她的自述作品,深觉该书所写非常真实,书中描述的传主与我了解的樊锦诗是一致的。”她认为我写的“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是对她最真实的解读。有次我和她聊天后感慨:这哪里是和大名鼎鼎的樊锦诗聊天,完全就是和一位邻家老太太在拉家常。
自笔者1983年毕业后留在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至今,已过去了40年。40年来,笔者一直在敦煌学的领域耕耘劳作。除出版有严肃的学术论著之外,这本小册子也算多年来笔者的一些所思所感。希望这本小册子,能使读者对敦煌和敦煌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