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梁沙生朝樟子松王虔诚地鞠了一躬,和满女登上瞭望台。站在瞭望台上向远望去,他感觉樟子松森林就像一条条绿色锁链,将科尔沁沙漠的一只爪子牢牢地摁住了。梁沙生心里一阵涌动,说:“满女,这一片大林海,真是想不出来他们怎样一棵一棵栽出来的,他们真的是舍命……”
樟子松林弥漫着一股浓雾。雾袅袅静静,没一点声响。隐隐地,远处响起一阵呼哨音。那是松涛的呼啸声。在那声音里,他知道,那个他既期盼又厌烦、既熟悉又陌生的脚步声就要响起……果然没多久,一阵足音就由远到近,扑踏踏地响在栅栏外的水泥路上。转而滋滋地走进院里,拍拍衣服就推门了。
松木门吱吜一声,就有一片光亮晃在床前。他欠欠身,咳嗽了下,颤颤地问:“梁沙生吗?是梁沙生来了……”他哑着嗓子,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应着他的声音,那个叫梁沙生的就径直走到他面前,熟练地将手中拎的苹果、梨子、李子什么的放在桌上。
他住的这幢砖石瓦房建在樟子松林环绕的山坡空地。瓦房上空有几条高压线横贯而过,下方是一个圈牲口的木栅栏。自从瘫痪在床,他一双眼睛局促在这低矮晦暗的屋里,看不到樟子松林,也望不见他心爱的“樟子松王”。
不能下床,平日里只有满女伺候他。给他端水喂饭,缝衣浆衫。而由于到了忙季,村里能到这里走动的人就越来越少。也只是梁沙生。梁沙生这一年几乎三天两头地就来看他,且每次都没有空手。这就使他感到有些宽心。
“福树叔,最近好些了吗?”梁沙生问。
“好些了。”每当这时候,他总是先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哪里能好,没有指望了!”
“不会呢!”梁沙生安慰着说,“福树叔,不会呢!”
福树笑了笑,便不再吱声了。他知道这是梁沙生在宽慰他,讨好他。自从梁沙生那一次来看他,郑重其事地提出要在樟子松森林建立生态旅游休闲基地,他脑子里那根敏锐的神经就欠欠地疼痛了下,心里一沉,他感觉面前这个喊他叔叔的梁沙生,不只是冲着满女来了。
正如怕什么来什么一样,果然,梁沙生开口了:“福树叔,和您说的事,您老想好了没有?……”
“……”福树斜躺在床上,侧着身子正想如何搭话,没提防梁沙生这回竟是单刀直入,几乎是吓了一跳。“嗯哼”一下就咳嗽了起来。喉咙里有痰,那声音就变得阴沉。
刚开始瘫痪在床时,梁沙生与乡亲们一样经常来看他,他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有一回,满女给他端茶时,漫不经心地说了句:“爸,梁沙生在他家那片樟子松林建了一个生态旅游休闲基地,当上小老板了。”他心里莫名其妙地咯噔了一下。满女走后,他躺在床上,在想起许多事情的同时,想起满女说“梁沙生在樟子松林建了一个生态旅游基地,当上了小老板”的话,心里沉思了良久。
再后来,梁沙生隔三差四地来他家,冠冕堂皇地以生态旅游休闲基地老板身份来找他,“福树叔,福树叔”喊得执拗,且每次都不空手。他这才觉得梁沙生别有用心里,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偶尔无言,他就偷偷地打量梁沙生。梁沙生端正的脸盘上有一双精明的眼睛,粗壮的身胚透着北方男人的剽悍,乌黑的头发卷着,有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头。他突然觉得梁沙生和他倔强的父亲太像了。
因为瘫痪在床,这些年他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梁沙生的到来,特别是迎合他的心思天南海北地神聊,不仅消散了他的寂寞,还使足不出户的他没有了“洞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的隔世感。
双手挣扎着,他想往上爬起,梁沙生搀扶起他,拿起一只枕头给他垫靠着。哆哆嗦嗦地,他从梁沙生的手里挣扎着,“哇”地吐出了一口浓痰,揉揉发蒙的眼睛,看看梁沙生,忽然又急遽地移开,问:“你进门,看见满女了没有?”
“满女?”梁沙生脸红了红,拿起桌上的橘子,取出一瓣鲜嫩的橘瓤,有点巴结而讨好地递上去。福树毫不客气地张开了嘴。
“满女?福树叔,满女哪里去了……”梁沙生说。
“满女不晓得野到哪里去了!”不想这回,福树竟是恶狠狠地出声了。只是那声音很不自然。福树或许感觉到了,支撑着身子又躺了下去,眼里滚落一滴浑浊的老泪,说:“满女野得很,梁沙生,你得帮我降降她,满女喜欢你,我晓得……”
“福树叔,说哪里的话?满女是一个好姑娘……”梁沙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好姑娘?”望着梁沙生,福树忽然就恼羞成怒了,“你怎么说她是好姑娘?要是好姑娘,她怎么现在还不嫁人?……”说着说着,福树干巴巴的脸涨得通红。气喘吁吁的,他又大声地咳嗽。床随之也吱吱响着,像是下一道逐客令。
草原上的风刮了一天,到了黄昏收敛了些,只在樟子松林低低地回旋着。接着就停了。没有风的天气,樟子松林就静得吓人。天慢慢黑着,屋里裹着一团淡淡的黑气。福树躺在床上,眼睛无神地望着屋梁。他开始整天睡不着,架子床在他不停地翻身时发出吱呀声,这声音就像老鼠咀嚼着他的神经……五心烦躁的,他有些渴,扯着嗓子喊满女。可当满女温顺地端一碗茶来,他又大声叫满女出去,要一个人静静……
满打满算,福树已在床上躺了七八个年头。
那七八年前,他长得壮实得像一头牛,在这一带可是活蹦乱跳的一条汉子!他脑袋瓜子好使,眼睛一转就一个主意。乡亲们佩服他,选他当了村主任。
横亘千里的科尔沁沙漠逶迤而来,到了这里突然就像只胳膊肘拐进了他们村。于是这里就成了一个大沙窝。冬天,风沙像风刀;夏天,沙窝像蒸笼。当地人形容这里是“一碗米、半碗沙,走一步、退半步,五步不认爹和妈,早晨沙堵门,出门跳窗户。”村里连一棵大树也没有,种子落地就被大风刮跑。
政府认为不宜人居,让他们整体移民。他带头不同意,嚷着故土难离。哪里也不去!他鼓动村民栽树,说树长大了,风沙就撵不走我们。但流沙堆成山,一锹挖下去,树坑没成形就被流沙填平了。可这样,他还是不停地栽。他找人贷款承包沙地,把苞米秆子平铺在沙地上,在苞米秆子的缝隙里栽小树苗,让树立了根。接着,他摸索出先栽下坡、后栽上坡的自下而上沙丘植树法,尝试用差巴嘎蒿、黄柳、锦鸡儿、紫穗槐、胡枝子等固沙植物,最后樟子松栽植取得了成功。如此领着乡亲们在寸草不生的沙地,栽了几百万棵树,将防沙第一道防线向前推进了十几公里。
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和乡亲们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用“前挡后拉、顺风推进、分批治理”的综合治沙方法,培养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治沙林草。这样,没几年时间,这里就有了一片樟子松林。生态一改善,当年粮食亩产竟达到了千斤。樟子松林从此也成了他的星星和月亮、他的寄托和希望。
可是,现在这个长高长大了、人情世故学得猴精、当上了老板的梁沙生,竟然要在此打造一个生态旅游休闲基地。说是生态旅游休闲,说穿了,不就是建一个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的地方?这不是糟蹋草原,成心毁掉他的樟子松林吗?他能答应吗?可拒绝梁沙生,会伤透满女的心,梁沙生也不会来看满女,告诉他外面的世界。
“满女,满女,沙生这一阵子怎么没来啊?……”有时躺在床上,他不停地念叨。
“没有来?爸,你怎么啦……”满女常常被父亲奇怪的举动弄得晕乎。嗔道:“爸,人家不嫌弃您,您还一百个不愿意,人家不来,你又惦念人家。爸,你是想人家觍着脸求您吗?”
“是爸爸不好,满女,是爸爸不好……”福树让满女呛得没话,独自埋怨自己,乜斜着眼睛望满女。
满女双手落寞地绞着胸前的衣扣。他看了,心里一酸。
梁沙生终于还是来了。
走进那间晦暗的砖石瓦房里,梁沙生笑着照例将随手带的人参、李子、梨子,还有一盒海参放到桌上,然后坐下来。可面面相觑,两人一时无话。随着经常上门,梁沙生已变得很自信了。他觉得他能成为这屋里的主人,成为这片樟子松林旅游休闲基地的经营者。他知道现在离成功还有障碍,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他不能落下一个不忠不厚的骂名。况且一想到福树叔用瘦如枯柴的手摸着他的头,嘱咐他“要常常看看满女!”他心里就有什么痴痴地涌动。
“坐,坐,沙生,你又花钱了!”瞥了一眼桌上,福树眼窝里有些发湿。微微侧过身子,在床上弓成了一个虾状。突然,冷不丁问:“梁沙生,你父亲死去几年了?”
“我父亲?”梁沙生愣了会,答道:“六年了。”
“六年!这么快……你记得吗,这樟子松林就是我和你父亲一起栽的……”
“……”
这个梁沙生当然记得。当年,眼看着漫漫黄沙席卷家园,乡亲们一下逃离不少。可他父亲没走。也跟福树一样贷款,承包了一千多亩沙丘栽树。为了把流沙治住,他俩一起找到专家。听说固沙要先种沙打旺,他俩就种沙打旺;看羊蹄子踩小坑撒草籽行,他俩就赶着羊在下雨前上山,顺着羊蹄印子撒籽。樟子松林遭虫害,他俩就赶猪崽进林子吃松毛虫,放鸭子上山吃蛾子。栽树需要投入,两家就同时承包了邻县人家的田地,用农业收入找补林业;付不起找人的工钱,他俩又带着家人给人打短工,硬是造出了这一片樟子松林。
后来还是出了大事。樟子松林突然成片地衰败枯死,并有蔓延之势。这下,两人吓坏了,慌忙找到当地的林业科技人员,发觉竟是当地过度开采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了地下缺水,同时成林树种单一和密度过大,对病虫害防治又过于大意。找到原因,两人立马进行人工修枝,通过生物灭虫、调整树木密度等,很快制止了樟子松林的枯败。
“福树叔,这个我怎么会忘呢?”梁沙生说。
“还好,你没有忘记。沙生,你家樟子松林现在好吗?”
“好啊!成老林了。那里树长得老好,我还修了一条路……就在那里,我办的生态旅游休闲基地……”梁沙生一听福树问起他的事,高兴得一时兴起,就滔滔不绝,“福树叔,我办的樟子松林生态旅游红火着呢,北京、武汉、南京和合肥,都有人来这里消夏……”因为旅游休闲基地是他亲自筹划的,他说着就有些手舞足蹈,话里也有些许自豪与炫耀。
随着他的手势,福树眼里惊奇和新鲜的光亮一点点暗下去,嘴角一滴涎水流下来了。
吮吸了一下,他叹了口气。转过脸,望着一边默不作声的满女,突然用手招着梁沙生,说:“我不是和你说这个,不说这个……梁沙生,你对满女要好……”
满女一听,双手捂脸转身就跑了。瞟了瞟满女,福树闭上眼睛,对梁沙生正色道:“沙生,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说这事的,你回去吧,你不要指望我把樟子松林给你糟蹋,树要皮,人要脸,你不要假借生态搞旅游,一门心思想赚钱,坏了你父亲的名声!……”
“……”梁沙生一愣,随即下意识点点头,尴尬地笑笑,忐忑不安地出了门。
到了夏天,空气里弥散着一股青草和樟子松林混合的清香。樟子松的密林不仅鸟多起来,野鸡兔子也多起来了。一到清晨,鸟儿们叽叽喳喳地鸣叫。福树经常在啁啾的鸟声中醒来。有时,他还看见一只兔子在门口拱着门。这给整天躺在床上的他带来了不少的快乐。但自从入夏以来,他身上开始一遍遍冒冷汗。即便是阴霾密布的阴天,也是一身的汗。他艰难地翻一下身,床上立即露出一大片汗渍。
那一个夏天很快就过去了。
夏天过去,福树的病情似乎在日益加重。架子床吱呀呀老鼠一般叫唤,那声音就像无数根炸刺,扎得他心里火辣辣的。
他先前睡的也是土炕。原来的两间房屋,四壁结实,窗户密不透风,炕硬邦邦的。满女妈从山清水秀的江南嫁给他,跟他结婚好几年,还说睡不习惯炕。他就置了一张床。满女妈病逝后,他搬到砖石瓦房,嫌搭炕麻烦,也不愿意困在上面。但随着身子骨整夜剧烈疼痛,架子床也叫唤到天亮。天一放亮,他就陷入迷糊中,感觉自己在樟子松林跌跌撞撞,又像陷在茫茫的沙漠里,漫漫黄沙如一条大蟒蛇紧紧缠绕着他……
屋外,他亲手栽植的樟子松林搭起了一片阴凉。水泥路上扑踏扑踏的脚步声,自然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经常有人来看他,和他聊天。但大都说天下没下雨、地有没有收成这些不咸不淡的话。梁沙生很长时间没来,以前从梁沙生嘴里听到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甚至他的生态旅游休闲基地,别人都无从谈起……
满女的话一天比一天少。喂饭、端尿、抹汗、洗衣……只知闷头闷脑干活,仿佛一只贤淑而温驯的小猫,默默尽着一个女儿的孝道。看着满女的样子,福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老鼠不死不活地牵扯女儿。想着,自己就暗自垂泪。
这以后,梁沙生当然也来。来了,就默默地陪他或者帮助满女做家务。然后又寡言少语地离去,再也不提他建旅游休闲基地的事。仿佛也是行使某一种义务。但就是这样,他也感到了某种慰藉。要是梁沙生几天没来,他就扳着指头数,数着数着自己就糊涂了,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他盼望自己尽快结束生命,但一听梁沙生那最初犹豫而又变得坚定的足音,他却又生出几分生的渴望。
“满女啊,满女呢?”
恍惚,他觉得有一团红丝线胡乱地摆在面前,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有时竟猴声猴气地大哭。
“爸,爸,您是做梦吗?”满女听见了,惊叫着,扯声扯气地喊。福树四肢颤抖,双手一哆嗦,突然抓住满女,叫着:“满女,梁沙生这两天没有来吗?”
“来过了。”满女心一酸,泪水扑簌簌地滚下脸腮,“来过了,还有许多人打老远地来看您、喊您,只是您昏昏沉沉的,不晓得……”
“那,那是爸爸不好?……”福树咧嘴笑笑,无力地摇摇头,自语道,“是爸爸不好。满女,爸爸日子不多了……”说着,又迷迷糊糊地睡去。
洋洋洒洒的,天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鹅毛大雪。樟子松林恍若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絮。只是樟子松林莽莽苍苍,广阔无边,一时还不能全部遮住。樟子松身上披挂的白雪泛着浅浅的绿色,逶迤地耸立在茫茫的草原。
福树竟在这个浑天缟素的天气静静仙逝了。
那天一大早,满女照例像往常一样起床喊着爸爸。福树没答应,满女心一慌,便用劲摇了摇,发觉他的身子已变得僵硬……满女吓得大哭了起来。
听闻福树的死讯,远远近近,三三两两的乡亲们冒着严寒赶过来了。他们一边操办福树的丧事,一边想起他生前的趣事,说了一大堆的笑话。说福树命大福大,说他一生下来家里养不起,把他扔在一个沙窝里,原以为他会被风沙埋了。可等第二天早上去看,竟不知哪里来了一只狗给他喂奶。家人于心不忍,又把他抱回了家。有人想起有一次福树在沙地里栽树,中午吃饭,饭碗一打开,沙灌了一嘴,他当是炒面,留了句名言“沙子拌饭,有滋有味”……还有人说樟子松林生发病虫害那年,福树在烈日里疯了似的搜集标本,把家里门板当标本的案板,晚上把病虫标本偷偷存放在冰箱里,吓了满女妈一大跳……
他们心里都明白,福树瘫痪就是因为治沙落下了病根。都说沾他的光,不然早背井离乡,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福树的逝世自然也惊动了上面的领导。作为这一片沙漠的治沙劳模、治沙英雄,他早就高山打鼓,名声在外了。几十年来,他的英雄事迹一直在草原森林流传。省市县领导得知他病逝的消息,立即派人慰问和处理丧事,想把他的骨灰埋在樟子松林,立一个石碑。只是听说他生前留有遗嘱,说把骨灰撒在樟子松林里,只好作罢。
梁沙生和满女忙了几天,在乡亲们帮助下,按照福树的生前愿望,将骨灰撒在了他栽的那片樟子松的密林。那天,梁沙生安慰了一番满女,端详着她家墙壁上挂的一幅老照片。照片上的福树手拿锹镐,神采奕奕。梁沙生沉吟了下,似乎明白了什么,便执意要看那一棵樟子松王。
满女泪眼婆娑地带着他去了。
说是“樟子松王”,其实,就是福树开始治沙那年栽的一棵樟子松树。实打实算只有几十年的树龄——那年,樟子松林生发虫灾,边上许多樟子松都枯死了,只有它顽强地生长下来,孤零零地树立着。等到四周的樟子松林都长起来,它长得更壮实、更高了,没几年就成了这里最为醒目的一棵——“樟子松王”也就这样叫开了。为了保护这棵樟子松,福树给它垒了个石头台子做隔离。在石头台子旁又搭起一个高高的瞭望台,这样,他就能看护这一大片的樟子松林了。
梁沙生朝樟子松王虔诚地鞠了一躬,和满女登上瞭望台。站在瞭望台上向远望去,他感觉樟子松森林就像一条条绿色锁链,将科尔沁沙漠的一只爪子牢牢地摁住了。但举目北望,他发觉科尔沁沙漠那雪地里的黄沙暗涌,仍像一头巨大的黄龙在蛰伏、窥视着,稍不留神就会扑向这里……
梁沙生心里一阵涌动,嘴里喃喃有词。说:“满女,这一片大林海,真是想不出来他们怎样一棵一棵栽出来的,他们真的是舍命……”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看正是这一片森林挡住了风沙,我们这里才变成这样。难怪他们把樟子松当成了宝贝疙瘩……”满女调皮地笑笑,嗔怪道:“可你还在打我爸爸的主意,你不是成心吗?”
“……”
这下,梁沙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听着满女的话,他眼窝里一热,心里一动。他想,他要在松树王台前真的立一个石碑,上面刻上“大漠忠魂”几个大字,把这里当作一个宣传福树和父辈们艰苦奋斗,战风沙、治风沙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样想着,他嘴角就不由欠了下,咧嘴一笑。
满女问:“你笑什么?”
梁沙生说:“不告诉你,你猜?”
满女没有猜——她看见葱葱郁郁的樟子松森林,因为大雪的覆盖变得雪白雪白,宛若一片深不可测的林海雪原了。而她身边,那樟子松王却像一颗晶莹的翡翠深深掩藏其中……恍惚,她见父亲在樟子松林里朝她笑了。
(作者:徐迅,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协常务副主席。著有小说集《某月某日寻访不遇》《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徐迅散文年编〔4卷〕》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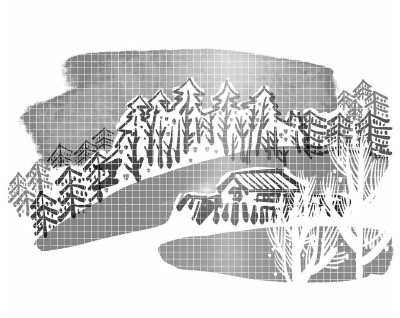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