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有过一些概述,浓缩成一个词,就是“融合”。现代性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严肃小说主题与流行文学元素的融合,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融合。至今我还认为,这个概括也许还是有些道理的。今天,要对2020年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一番概述,却觉得很难。
这难,一是因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分化非常明显,硬要用一两个词语概括,难免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二是因为我本人追踪长篇创作动态十分有限。急速式、恶补式地翻阅了近期影响较大的十多部长篇,似乎又有一些感受可以言说。
对自己生活的大地给予文学上的回报
2020年的长篇小说,营造出十足的世俗生活烟火气。对人间烟火的热衷与描摹,对世俗生活里的欢乐、痛苦与热情、无奈,对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爱情酸甜苦辣的复杂感受,对爱与恨、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构成了众多小说家力图要去表现的生活画卷和逐渐推出的主题。当然,任何时候的小说,只要是现实题材的,所写的无非就是这些生活世相。但生活是由众多部分构成的,对生活的理解、阐释有一百个方向可以进入。在特定时期,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从同一个或相近方向集束式地聚拢,这就是所谓时代风尚吧。小说潮流也是如此。在表现生活的过程中,如此集中对人间烟火的关注,对世俗生活的表现,是2020年长篇小说的突出共性。为了把这种烟火气表达得淋漓尽致,作家们纷纷把地域文化纳入其中,让读者知道,同样是袅袅炊烟,却是从不同的地方升起的。
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是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这是一部献给哈尔滨的倾情之作,是希望写出哈尔滨百姓生活,也能够为哈尔滨百姓接受、认可的小说。这种强烈的地域诉求,本来是属于乡贤文人的创作追求,而不应当是恰好生活在这里,名声早已走向全国甚至世界的作家所专注的。过去是小说中无须强化的地域背景,如今直接走到了前台,成为小说中不容置疑的真实场景。
《烟火漫卷》里的每一章,基本上都是从对哈尔滨城市面貌的描写开始的。迟子建用诗意的语言,在开篇处为哈尔滨描摹了一日之内从清早到黄昏再到深夜的微妙变化,也描摹了这座城市一年四季的异彩纷呈。强调日复一日的生活,就是强调无论冬夏皆如此。而一年四季又各有风姿。小说显然是有预谋地设置了这种更替。上部的第五章开头是哈尔滨的春天,第八章是初夏。下部的第三章写盛夏到初秋,第四章是深秋的景象,第五章是初冬,第六章是隆冬。第八章作为末章,则写了旧历大年的气氛。这些描写必须是明晰、独特的哈尔滨标识才能入画。
在强烈的城市标识之下,在散文化的笔法之后,出场的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各色人物。他们或生于斯长于斯,从未离开过,或是这座城市的闯入者、漂泊者、寄居者。他们相遇相交,共同演绎出一个个一年有四季、一日有昼夜的人间故事。他们身上的故事都不恢宏壮阔,却是每一天必须要过的日子。刘建国、刘骄华兄妹,翁子安、黄娥等外来者,共同演绎了既属于世俗生活中的常态,又充满戏剧性、传奇色彩和情感深度的生活。
真的是无独有偶,这一年,王松出版了一部专写天津地界上传统世俗生活的长篇小说,名叫《烟火》。这是一部试图展现近代以来天津城市文化的小说。百年历史中,既有大的历史风云激荡,更有百姓生活的从容不变。而后者或许正是王松力求要充分展现的。如何把津味儿文化写活,写好,把变与不变写成一体化的生活,让人间烟火弥漫在百年历史中,让天津人也有一部完整呈现自己文化的小说,王松的这一创作理想不可谓不大。
几乎是不约而同,胡学文把地域定义为北方乡村的《有生》,也在2020年推出。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史的长篇小说。一个处在生命垂危状态的老者,一生的职业是接生,迎接超过一万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她似乎掌握着常人读解不到的生命密码。这里呈现的也是百年史,也是地域标识的强化。
这些成熟的作家仿佛同时觉悟到,要对自己生活的土地给予一种文学上的回报,是否写得好自己的土地,这是能否真正拥有读者的根本所在。与二十年前读到的百年家族小说相比,今天的小说家们似乎把表现和回答重大社会问题,融入对世俗生活的展现当中。小说当然要回答历史演进的进程,但也要写生活中的不变,以显示文化自身的韧劲和力量。
2020年,我还读到了滕肖澜描写上海众生相的《心居》,同样是为一个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进行真切描写。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金宇澄的《繁花》之后,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还要再添一把新火,足以见出城市的文化和魅力,正在多侧面地以小说的形式打开。贾平凹的《暂坐》,把西安改叫西京,曲江换名为曲湖,但钟楼、鼓楼、大雁塔、秦岭,这些确凿的地名,早已可知,这又是作家为西安献上的一部“市情报告”。拾云楼也罢,茶庄也罢,都有这座古都在今天流溢出的生活气息,也是对人间烟火的描摹。吴君的《万福》是写深圳的,自然更多一些动荡起伏,王尧的《民谣》、张忌的《南货店》,写南方乡村生活,无论是从记忆中挖掘,还是从现实中提炼,表现的都是人间烟火与历史风云的错综复杂。
人间烟火突然成为小说家们想要表现的对象。从小说表达上可以看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使这些小说天然地具有可靠性和可读性。作家们不是写地方志一样写地域,也不是散文化地一味抒情。小说的故事性,故事的小说性,是他们创作中的自觉追求。对细节的刻画更显精益求精。《烟火漫卷》在故事结构的总体设计上,在情节与情节的环环相扣上,在细节描写的精准上,可以见出迟子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功力。胡学文的《有生》以绵密的意象显示出创作资源的丰沛。可以说,他对生活的熟稔和理解,配得上用这近60万字的叙述。“蚂蚁在窜”,以这个贯穿始终的意象为代表,胡学文对众多人物的塑造用尽了心力。王松也一样体现出沉稳的创作心态。这些长篇小说,多以素描的功底,工笔的力度,全景图的构思,描写着事实上并不清晰,线索极其纷繁、烟火缭绕的世俗生活。
在寻常的日作夜息中探寻不一般的意义和价值
2020年的长篇小说,又体现出另一集中的特点,那就是在世俗烟火的描写中,表现与之本来并不搭调的艺术生活。这真是有意思的现象。
还是先说《烟火漫卷》,尽管其中的主要人物,刘建国是下岗工人,妹妹刘骄华是警察出身,黄娥是进城农民工,与艺术并无关联。然而,音乐,而且是高雅的古典音乐,却在小说里成为另一条重要的线索。很多故事,包括核心情节,都与音乐和音乐厅有关。迟子建以各种方式为这种加入进行了合理解释。哈尔滨的城市气质本来就是以音乐为主打,去不去欣赏,音乐生活都与城市里的每个人有关。在诗意化的城市昼夜与四季变化中,在音乐厅的乐曲声中,出入的又不无刘建国这样的平民百姓。但这就是生活,它们很好糅合在了一起。
王蒙的《笑的风》也写了音乐,古典音乐史上多个响亮名字在小说里闪现。这一年,还有房伟的小说直接就叫《血色莫扎特》,一个“钢琴王子”的另类故事。除了音乐,其他艺术生活也多有进入小说。冯骥才的《艺术家们》,是写画家生活的。同样写到美术的,我还读到了云南作家傅泽刚的《艺术圈》。
不只是音乐和美术,多个艺术领域,多重艺术生活在小说里以各种方式存在着。或台前,或幕后,或是故事主体,或是主体故事的“引子”。李宏伟的《灰衣简史》以影视公司为故事缘起,虽然不是为了艺术而写艺术,那也是起到引子的作用。刘庆邦的《女工绘》,依然是写矿区生活,矿工题材,但这回出现的,是矿区的文艺宣传队,主要工作是唱歌跳舞。王松的《烟火》则把相声文化与天津的民间口语文化进行了某种结合。《暂坐》里有古琴演奏,也有宣纸笔砚,《民谣》里乡村里的戏曲围观,等等。2020年末,在陈彦的《装台》改编成电视剧的热播之际,又读到这么多表现艺术生活的长篇小说,真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这种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世俗话题与艺术话题掺杂在一起,或者以艺术之名展开另外一重生活,或者在表现艺术家们的特异生活时,一样呈现着他们“非艺术”的一面,甚至在极其普通的生活中闪现精神之光的小说创作,在一定时期集中出现,并非完全属于偶然。大家经历了向往物质到向往精神的过程,现在则更愿意辩证地、结合地看待生活了。就像路内的《雾行者》一样,一辆卡车里装载着货物,满中国跑,但这不影响人物在疲惫的间隙谈论高深的文学问题。谈论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讨论乔伊斯、艾略特,话题简直堪比大学里的文学课堂,本来像一部“公路小说”,却融进了许多书斋里的话题,小说家为什么要这样构思作品,耐人寻味。
让生活成为日常,成为它本来的样子,又从这寻常人家的日作夜息中,探寻出不一般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我看到的小说景观。艺术上的本色追求可以从多方面得到印证。钟求是的《等待呼吸》,毛建军的《美顺与长生》,试图让爱情的纠葛限定在“言情小说”范围内,让生活按照本来的样子呈现在小说里,不去刻意拔高此外的意义。张平的《生死守护》,在一以贯之的反腐题材中,展开了一幅众多普通人悲喜生活的图景。吕铮的《三叉戟之纵横四海》,对警察人物的塑造,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和命运沉浮。剑胆琴心兼具,方是小说里的人生世界。
行走在烟火气与艺术氛围之间,带着艺术气质去感受日复一日的生活,小说家还将发现哪些不一样的风景,奏出怎样风格独异的乐章,值得我们在阅读中继续期待。
(作者:阎晶明,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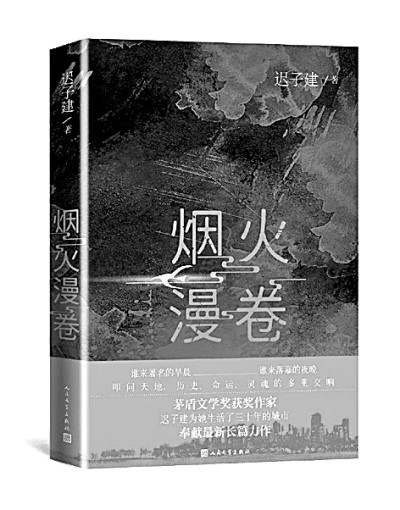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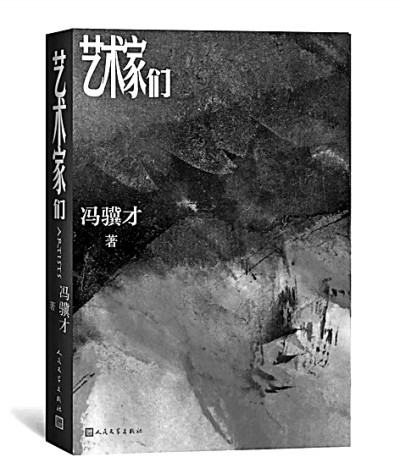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