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边远省份一所高校教书,20世纪80年代,有幸得到来北京大学进修的机会,于是前前后后几十年,结识了北京高校中文系几位师长。虽然我从未敢自称是他们的学生,但先生们的教诲和风采却一刻未能忘,总想付诸笔墨。几位先生的学术成果与思想精髓早有他们的高徒付诸各类报刊,无须我置喙,这里就描几笔侧影吧。
谢冕老师,您咋不老?
几年前的一个正午,中国美术馆十字路口,马路对面一个人正走在通往沙滩方向的五四大街上,红光满面,步履矫健,这不是谢冕老师吗?我很想跑过去与老师打招呼,忽又觉不妥,老师是从一个会议上出来?还是去赶往另一个聚会?看那匆匆的脚步,还是不要打扰了。我遥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突然觉得,也许这独自前行的身影,才是谢冕老师的常态。
我忆起1986年那个春节,正是诗坛“三个崛起”被搅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趁回京探母的机会去拜望谢冕老师,老师说:“这个春节过得很清净。”我愕然无语,又颇能理解地看着谢老师,是啊,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当天空黑云压下时,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自是躲避。于是,谢老师有了难得的清净,躲开喧嚣也躲开了虚伪和繁杂。祸兮福兮?静潭深流,先生的思绪在那一段安静的环境中激烈地碰撞。不久,人们又一次见到了先生智慧的井喷,那从不见疲倦的身影又活跃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和聚会上。他主持了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激活当代文艺批评,这些年,又组织编写了《中国新诗总论》等几套关于百年新诗的丛书,还一连出版了几本著作。
一次会议间隙,几个与会者围着谢老师在花园小径散步,周遭草青树碧,时令不对见不到花。一行人说说笑笑,忽觉有淡淡花香袭来,有人说是栀子花香,有人猜测是茉莉花香,也有人说不对,像玫瑰花香,独谢老师不语。大家东张西望,眼前仍是一片青碧,见不到娇红嫩紫,疑惑间,有敏感者觉得那香氛来自身后,齐转身,落在后面的谢老师忽然伸出手,掌心中,赫然躺着一个小小的香水瓶,众人认出这是宾馆为客人们预备的,笑闹声中,谢老师不无得意地举着这小小的香水瓶转来转去,脸上隐约老顽童的坏笑。一个小物件,便为众人营造出花香四溢的美妙境界,这正是谢老师。处身青年学子间不多言语,总是满怀兴致地看着那些抢着说话的学生,或莞尔首肯,或垂眸凝思,偶尔一句提问,几句解释,三两个字的点燃,便能营造出全新境界。
最早知道谢老师,是看到他和夫人陈素琰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评作家张洁的文章,立刻被充盈于文字中的诗意迷住了,而文中那句“不老的是思想”深印在我的头脑中。当时我以为,写出这样激情与净美文字的,一定是两个浸润在诗歌中的年轻人。后来我去北大进修,得以结识谢老师。那是1984年,论年龄,谢老师和陈老师都已知天命,可我觉得,那篇文章就是他们夫妻二人自身的写照。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眼里,谢冕和陈素琰二位师长几乎没有变样,我心中暗自疑惑:谢冕老师,您咋不老?其实细想想,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所骄傲的,不就是具有高级思维吗?思想不老,人便不老。
见到一篇写谢老师的文章,提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涌现的新作品新思潮新现象,会让研究者应接不暇,而谢老师却选择了这个难度大的专业。评者是在赞美老师的知难而进,我却觉得不止如此。谢冕老师说:“当代文学日新月异,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我以为,谢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生长”的人,他的天性是接近时时出新、不断变化的时代,选择当代文学做研究对象,初心绝不会是困难与否——尽管谢老师并不缺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正如谢老师那篇文章的标题:《在新的崛起面前》,面对一个“新”字,“辛苦”即是享乐。
谢老师,您怎会老?想起您,眼前就会出现诗中描述的“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谢冕《永远的校园》)的模样。一位严谨的学者,一位不知疲倦的思想者,一个谢绝冠冕的老顽童,生命长青。
想起赵祖谟老师,不敢再叫疼
1984年秋,在北京最美的季节,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指导教师是赵祖谟。那个年代的进修生是很幸运的,校方像培养研究生一样,根据进修生自己对研究方向的选择,给每个人都配备指导老师,每周见一两次面,学生汇报读书进展情况,老师加以指导。正式拜访赵老师时我内心忐忑,不知该如何与老师交谈。进得赵老师在北大西门蔚秀园的家,普通两居室,没有特别的装修,落座,一杯清茶,温厚的笑脸,爽朗的话语,顿时让我定下心来。老师了解了我的概况,问我是否给《当代文学研究丛刊》投过一篇评论王安忆小说的文章,我羞赧地低下头,赵老师却马上说:“写得不错,我们准备在第三期发表。”我惊讶地抬头看向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老师鼓励我说:“我们欢迎这种重视文本分析的文章。”后来我又告诉赵老师《文艺报》发表了我的一篇小文,赵老师对我肯定后说:《文艺报》反映了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我希望你能耐下心来,把创刊以来的《文艺报》从头看一遍,这样就能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遗憾的是后来我因种种杂事,无法专心完成老师的指导,但老师对我的鼓励却给了我信心。
1985年秋,国家的一切逐渐走上正轨,全国上下都在奋起直追,以弥补荒废的十年。赵老师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满怀激情,准备全力投入教学及学术研究,为此他做了一个决定:去医院把困扰自己多年的腰椎问题解决。不料手术失误,刚入不惑的赵老师下肢全然失去知觉,而他的爱人张晓老师刚从外地调回北京,唯一的女儿阳阳只有三四岁。轰然一声大山倒塌,未来也许是无边的黑暗,我无法想象那一段老师度过了怎样的日日夜夜。第二年暑期回京,我立刻去拜望赵老师,老师除了不能站起,仍然是一如过往的精神饱满,坐在堆满书籍杂志的书桌前侃侃而谈:热闹的先锋文学、厚重的寻根文学……每提到一篇当时的热门作品,他都能细述情节分析结构臧否人物,这得是多大的阅读量!正是这样“全力投入”工作,使他没有念念于病痛的困扰。那以后,赵老师不仅主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几次修订了北大中文系当代室几位老师合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还坚持坐着轮椅去上课,带出来几届研究生。
我是特别愿意听赵老师讲话的,不论是在课堂上讲课,还是两三人闲聊。老师喜欢讲,他拒绝空泛和虚夸,不去说那些教科书上写就的概念,也很少提抽象的理论,只注重美感与直觉。几十年过去了,退休的我将精力转向了创作,因为信任老师对小说敏锐的感知与独到的眼光,我把自己写的小说拿给老师看,老师对于我那本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给予了肯定,认为细节饱满,地域特色鲜明;但对我特别看重的那本家族历史小说却严厉批评,说我过于拘泥于现实中的人物境况,而忽略了文学的典型性。
为了治疗,赵老师住进了养老院,我们几个当年的进修生准备去看望老师,但每次给老师打电话他都会说路太远,你们也不再年轻,就在电话里聊吧。是啊,我们也不再年轻,但每当我因病痛难忍而质询生命的意义时,耳边就会响起老师那清朗洒脱的声音。这是一个做过八次大手术、每日要靠止疼药维持的八旬老人啊!可他总是用淡定的语气回答对自己病情的询问,仿佛疼痛折磨的不是他自身。而一谈起近时期的小说和一些文学现象,语气变得热络,思路仍是那样清晰,记忆十分扎实。
想到老师,我不敢再叫疼。赵老师不仅给我以学业上的指导,更给了我一重人生的启示:无论身外或身内的顺境与挫折,都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敬畏生命,便坦然地迎接生命的所有。
刘锡庆老师,那宽厚的胸膛
写到赵祖谟老师,自然会想起由赵老师为我引荐的另一位先生,已经离世的刘锡庆老师。刘锡庆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以写作学研究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蜚声国内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不记得是为了什么,赵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去找找师大的刘锡庆老师。”赵老师随即给刘老师打电话介绍了我。我按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刘老师当时在北师大的住处,一座老旧的红砖楼房。师母开了门,厨房似乎是迎着走道,我一进门就看到窄窄的过道对面窗前,半个高大宽厚的背影,似乎在灶前炒菜。我有些意外:这形象与我心中的名校名师似乎不搭界,同时又觉得自己来得真不是时候,便有些尴尬地站在窄小的门厅里。刘老师忙完活走出来,一张笑菩萨的脸,招呼我坐到摆在门厅里的方桌前,翻看我带去的自己的专著与论文。看到《张洁的小说世界》,立刻说:“呃,这本书是你写的?我刚买了一本。”紧接着就说:“你可以给《文学评论》写文章。”我受宠若惊,《文学评论》,多么高大上的杂志,这是搞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期望能够在上面见到自己名字的刊物啊。我讷讷地看着眼前这位初次谋面,高大壮硕又慈眉善目的先生,不知该说什么。刘老师当即给《文学评论》编辑打电话,直截了当说了几句,就把电话递给我。自那以后,我连续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几篇介绍甘肃文学创作的文章,文学界同好关注这个西北偏远省份的文学创作,并认同甘肃作家作品中蕴含的“黄土魂魄”与“天马精神”,刘老师是第一推动人。
前一段从媒体上得知北师大中文系的任洪渊老师也去世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任洪渊以诗名世,后来听说他到了北师大任教,我还颇为惊讶。最近看到任洪渊2018年纪念刘锡庆老师的文章,提到自己当年进北师大得力于刘老师“行事的简洁明快”。刘老师与任洪渊当年曾是北师大同学,但二人并无多少交集,80年代初,任洪渊听到北师大中文系组建当代文学教研室,便动了回母校的心思,可他年过四十,又没有过硬的学历。当他找到负责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刘锡庆老师后,任洪渊写道:“到了他家里,他坐在书桌前浏览我带来的文学期刊。……品评了几句之后,他说出的话语震动了我:你来吧。中文系需要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那还是80年代前期,各高校还没有想到引进作家,刘老师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国内高校教学秩序的看法和学科建设的远见。
这就是刘锡庆老师,一位真正的师长,热情、宽厚,无私地提携后辈,只看作品和成果,从不认关系。每次见老师之前,我总有些紧张,而一看到那宽厚的身影和那张弥勒佛般的笑脸,就会松弛下来。在《散文一样的中文系》中,任洪渊写道:“我第一眼就看到他明朗的面容,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也没有什么要张扬的。他的穿着,那么高大魁梧的身材,把那个年代的蓝色中山正装穿得那么休闲,随意,有如性情散文的笔法,那么无主题的主题,无形式的形式。”诗人的语言,准确地描绘出学生眼中的刘锡庆老师。“坐在锡庆面前,谁都能看到他胸襟的明净……有这样明净胸襟的文人,太少了。”
是的,这就是刘锡庆老师,明朗、明快、明净,那宽厚的胸膛里,装着的是一颗没有瑕疵的心。
(作者:许文郁,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退休教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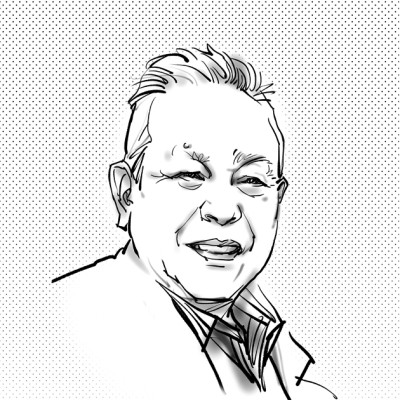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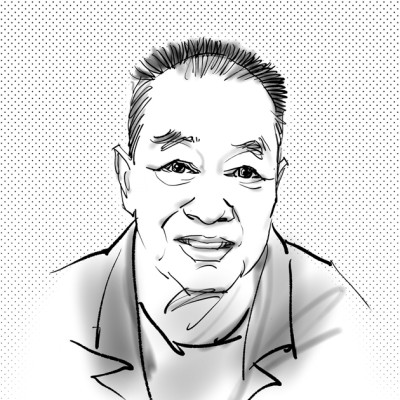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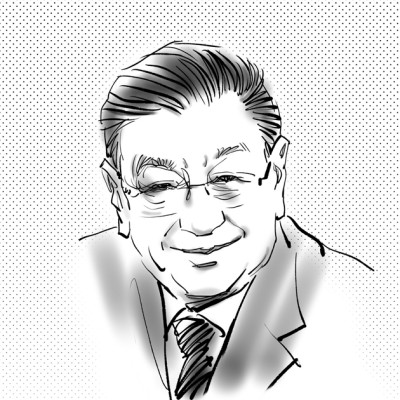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