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周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审美现代性批判》《视觉文化的转向》《文化间的理论旅行》等。近日,周宪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周宪教授带领,李健、周计武、庞弘、童强、殷曼楟、祁林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阶段,视觉文化既是这一转型的产物,也是其见证。本书着重研究了社会变迁与视觉文化的交互关系,当代社会的转变如何催生视觉文化,视觉文化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等问题,同时也涉及视觉文化的各种理论。
日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童强老师和复旦大学艺术设计系汤筠冰老师,就该书内容进行了一场对谈,为读者解读了为什么是“视觉文化”?如何理解“视觉建构”这一概念?以及视觉文化研究的未来究竟如何?等问题。
汤筠冰:《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一书出版了,为什么是“视觉文化”?
童强:这当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现代的生活越来越视觉了的缘故。以前是以语言/话语为中心,现在是以视觉/图像为中心(语言当然还是一个中心),我们身处各种景观、图像的包围之中。所以海德格尔说这个世界是作为图像被我们把握,居伊·德波也深深地感受到现代社会抑制不住的对景观的热情。视觉变得越来越突出,正如本书序言所说,视觉文化已是今天主导性、支配性的文化形态。从大众传播上也能看到这点。大众传播媒介兴起,报纸、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充满了各种视觉形象、视觉符号,人们终于迎来视觉文化的时代。特别是手机与网络几乎彻底改变了视觉形象的生产模式,改变了人与视觉形象、形象传播之间的关系。
汤筠冰:我们的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如何来理解“视觉建构”这一概念?
童强:按照周宪教授的课题设计,我们的视觉文化研究主要贯穿四个概念:形象、视觉表征、视觉性和视觉建构。形象是视觉文化的载体,表征是其表意实践过程,视觉性则是这个过程的特征,最终必然触及视觉主体的建构。这四个概念构成了视觉文化的内在逻辑。具体展开时,我们着重选取了视觉文化领域中的六个不同“扇面”,它们仿佛打开的六扇窗户:大众文化、先锋艺术、草根传媒文化、城市形象、视觉体制和视觉技术。前四个“扇面”属于视觉文化的内容分析,后两个“扇面”是视觉文化制度与技术层面上的分析,透过这些窗户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整体景观。李健撰写的“大众文化表征与视觉建构”一章,是对大众文化非常有趣的研究,他划分的“大时代”“小时代”和“微时代”,分别代表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象学的三个不同阶段。周计武论述的“当代先锋艺术”、庞弘所探讨的“草根传媒文化”,都是与目前的文化生活、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话题。
在四个概念当中,“视觉建构”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复杂。视觉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发的看,而人眼的看,其实并非“自然而然”的看,它总是有一个预设机制在引导。在狮子的眼里,草原上只有可猎杀和不可猎杀两类物种。你看什么,能看什么,如何看,谁来提供给你看(或者不让看),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某种社会结构、机制决定的,颇为复杂。这种结构和机制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是从外部来看视觉建构。从内部来看,视觉活动对人或主体性来说是一种建构。通俗地说,主体性建构就是通过一系列看的过程,把你培养成为社会希望的样子。用书中的表达就是:“视觉文化通过各种可见性符号和形象来建构社会主体,通过视觉实践来塑造人们对社会、文化乃至自我的认知。”社会的主体性建构当然存在多种渠道与方式,但视觉形象的作用更为突出。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四组学生接触同一个讲座的内容,但接收的方式分别是阅读、听讲座、听广播和看电视。通过四组的对比测试发现,效果最好的是看电视,其次是听广播、听讲座,最后是阅读。电视作为一种视觉传媒具有不可比拟的功能。
这里所说的“看电视”就已经涉及“视觉体制”与“视觉技术”。殷曼楟和祁林分别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颇具开拓性的阐述。在阅读时代,还没有发明电视,人们只能是阅读、听讲座。视觉要进入电视时代、影视时代,就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要有电视机的发明,要解决摄像、制作、传输、接收等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同时,电视节目作为产品,它的生产,包括制作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如何制作一个节目,由谁来制作等都涉及一系列社会机制。也就是说,形象的生产是由社会复杂的技术以及体制保障,或者说限定的。
汤筠冰:本课题中你主要讨论城市形象、城市景观,能不能以此为例,来解释视觉建构这个概念?
童强:城市景观的建设,不是拍一部电影那样简单,它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机制和建构过程。它需要实际地建造许多建筑、公共设施等,需要集中大量的物质、人力、财政方面的资源,还需要充分考虑当地固有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我们用30年的时间,在上海浦东的陆家嘴创造出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城市景观,正是通过这一宏大的、高楼林立的视觉形象实现了民族愿望的表达,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中国现代化的象征,我称之为“国家景观”。这是一个真正漫长而复杂的建构(建造)过程,我注意到,视觉建构其中还包括“视点”的建构(建造)。就像黄山上的许多景点,都有一个让人观景拍照的地方,“陆家嘴景观”包括了它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外滩。外滩的观光大道起初只是一个防汛设施,随着“陆家嘴景观”的成形,外滩经过多次改建,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合休闲漫步的滨水观光平台,为“陆家嘴景观”提供了一种既庄严崇高、又轻松浪漫的全景式群体观看方式。这是非常成功的视觉体制化建构的例子。没有一系列复杂的动员体制,就没有“陆家嘴景观”;没有外滩,“陆家嘴景观”不会如此壮观。它为人们提供了中国现代化最直观的视点。你看了,就认同了。
不仅观看,人们还在此拍摄。包括在电影电视、网络报纸以及我们自己在城市各个角落中的留影等等,风景形成二次呈现,景观的景观,建构的建构。这些影像不仅再次认同了这一景观,也确认了这一视点和在此观看的方式。这种观看成为范式。城市看起来就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景观装置”。它不停地制造无穷无尽的影像。我们看到的城市景象,包括媒介制造的各种影像,以及影像的影像。形象会带来更多的形象,我们身处形象的洪流之中。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借用福柯的术语“装置”,对德波的景观社会概念做了进一步引申,把景观社会称之为“景观装置”。阿甘本认为,景观社会是资本主义走向极端的产物。资本变成图像,通过媒体的循环,生成新的增值了的资本,构成了一种“象征秩序”。这正是资本通过图像盘剥我们的过程,不仅是财富,更关键的是掠夺了我们的感受力。沉溺于网络上人为制造的美女影像的男生已经失去对现实中女生的正常男性感受力。《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你仅有的感受力是对抗消费体制的最后防线。从资本到图像、媒介,再到资本的过程,是资本的最后嬗变,其中,交换价值完全遮盖了使用价值,它使实际的生产过程完全虚假化,与其说是生产了一个女包,不如说是生产了一个LV的符号。“景观装置”中的人们已经无法区别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现实的影像。影像已经变成现实,人们依靠影像呼吸。
汤筠冰:视觉文化是今天才有的吗?古代难道就没有视觉,没有视觉文化吗?视觉文化研究的未来究竟如何?
童强:古代当然有视觉,也有各种视觉规训,“非礼勿视”就是一种规训,园林建筑中有许多视觉文化的东西,但总体而言,那时的视觉形象生产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是主人为了建造园林而“顺便”考虑到赏心悦目,而不是今天为了一个景观、形象,“顺便”搭建了一个园林;为了突出现代化,于是创造了摩天大楼群集的景观。贝聿铭苏州博物馆的设计呈现的主要是一个视觉上的园林。形象已经是今天消费和生产的首要因素,设计学的兴盛,正是为增长的消费提供审美的前提。没有这个审美的引导、视觉上的建构(设计),产品就是不存在的,即使真的有一个拎包放在那里。一个女包的视觉形象——即款式,就是它存在的全部理由,结不结实,好不好用,是前消费时代、低端初级产品的问题。物,在这里凝结成一个形象的存在,视觉的存在。
近几十年,视觉文化可以说是人文学科中的显学,它迅速拓展、交叉到哲学、文学、传播学、艺术学等领域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今天的学术热点层出不穷,数字人文研究、数据可视化、听觉文化、声音美学等不断涌现,这多少减弱了视觉文化的关注度。美国著名艺术理论家W.J.T.米切尔于1995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视觉文化的课程时,主张用批判性的语言超越图像的权力,消解对图像魔力的盲目崇拜。这仍然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主旨。这需要我们充分审视视觉形象在历史想象和文化认同中的建构作用,深刻分析现代社会中视觉的经验形态以及话语建构过程。总之,视觉文化研究之路还很漫长。
(作者:童强,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汤筠冰,系复旦大学艺术设计系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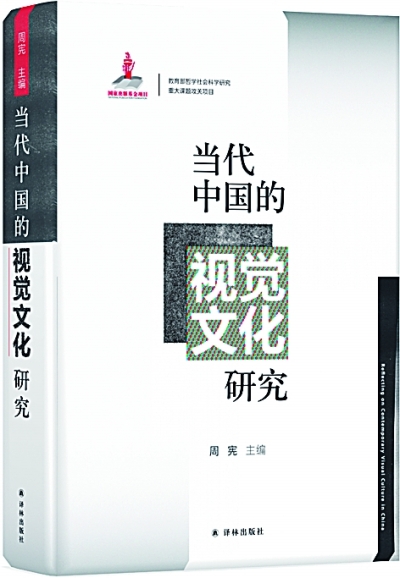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