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先生曾经有二十四字的自评: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先生在艺术领域的成就早为世所瞩目,他笔下的线条沟通古今、熔铸中西而能彰显中国士人清华不滓、简约厚重的精神境界。而作为诗人的范曾,能够“偶为辞章,颇抒己怀”,不但是他对于古典诗文辞章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生动写照,也是一个倡导“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当代国画大师数十年不懈的持守和实践。
范曾先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和消遣,而特于辞章一道,几乎填满其所有的余暇。或画余遣兴,或逆旅遐思,或即事感怀,或吊古鉴今,或诗或联,莫不见真性情,而二三子随之吟咏唱酬,尽欢而散。
先生笔下,古今中外山川风物、花鸟游鳞、人物故事,无非诗料,而向之所作,随手赠人,不存底稿,由此则散佚不可胜计。近年所作,乃有生徒时时记录,往往一夜之间,七唱成焉。兴犹未阑,更相命题作诗钟之戏。夜深力疲,诗思渐淡,忽一妙句出,师生相与欢喜赞叹,倦意顿消。其可掬之痴态,十数年如一日。终至箱箧之积何止千数。
曾有一古人悬联:
妙人儿倪家少女,
欲求其下联而不得,先生于飞机上对之:
悟言者诸法吾心。
在字面上的巧思固如联句所示,可谓联中藏机,增加了作联难度。而更加重要的,乃是此联上下两句中所展现的诗人怀抱。上联可以佛家所讲之“色”(有)概括;下联则可以佛家“空”(无)比方。联语之张力毕显。
一诗钟以“非洲”对“谢灵运”,两事相去万里,毫无关属,先生先出一句:
皮肤尽黑;
以说非洲,似无甚妙处,而下联一出:
智慧同玄。
则有深意在焉:史载东晋大将军谢玄生子谢焕,智障,而谢焕生子谢灵运,绝顶聪明,乃至于谢玄开始妒忌自己的儿子,说:我乃生焕,焕哪得生灵运?区区四字,不但拈出一段事典,更能把其中委曲之意得以尽言。下联“智慧”与“皮肤”相对,一表一里,而“黑”与“玄”同是两种颜色。“玄”还是“谢玄”之“玄”。
先生曾有一诗:
论白描
琤琮夜半隔窗鸣,
迓雪寒梅立娉婷。
总觉胭脂成腐秽,
须教水墨化阴晴。
千岩滴透原无色,
一线穿空若有声。
信是当风吴道子,
古灯如月我高擎。
一部《范曾诗稿》,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对于古风、绝句、律诗、对联、曲等不同体式的准确把握和娴熟运用。在表达不同的情致、不同题材时可以选择相应的体式和韵字。对于律诗,范曾先生素所青睐,曾有贺杜甫《秋兴八首》发表。他以为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格律最严谨、形式最完备的体例。而先生信奉在严格的规矩中,大手笔往往能拓出奇境。倘不是对于古典诗歌语言把握到这样的程度,那对于这一古老形式的任何贬损和顶礼都可以视为一种迷信。是不足为训的。
《论白描》内容固然写了对绘画中白描的感悟,而诗歌的妙处,也正在于若即若离的语言技巧。感觉、视觉和听觉,眼前、过往和将来,都说到了,可又都没有着实,是可视的线条吗?分明又是一种天籁之音。这些纷纭变幻的感受,既是读者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存在,又是具备深刻实践感受的艺术家个人的高峰体验,诗的奥妙尽在这种难以明言之地。
调寄沁园春·杜甫草堂
茅屋犹存,草树斜阳,万里桥西。
念诗坛人老,荒村结舍;蓬门篱在,野叟同卮。
落木无边,长江不尽,多少风烟烽火思。
长安渺,叹乡关日暮,世事如棋。
高吟绝代清奇。是一卷人间哀怨诗。
写石壕翁媪,彻眉酸楚;夔州鼓角,透骨伤悲。
绫烂朱门,肉囤大户,沟壑横陈僵死尸。
长篇在,仰萧条异代,竹帛名垂。
词的写作有不同于诗者,虽不如诗般喷涌而出,汪洋恣肆,须在长短变幻之节奏中曲尽幽微之思致,古人有毕生不作词者如范伯子先生,也有专精于词而诗绩平平者若辛稼轩。而范曾先生则通邮置驿,往来自如,亦可见其胸襟之裕如。
其个人之诗词实践既如上述,则名重当代,为诗坛宿彦所激赏且引为知己者甚夥:
著名诗人叶嘉莹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范曾卷》序中讲:支撑起他的不凡之画骨的,原来正是由于其内心中所蕴含的一份涵养深厚的诗魂,而且无论其所绘者之为诗人与否,其笔墨深处似乎都有着一缕诗魂的回荡。……其所自作之诗篇亦复才气纵横迥出俗尘之外。
范曾先生和诗坛大老周汝昌先生往来唱酬更是作为当代文坛的佳华话为人称道。这一文采风流的古风给处在文化复兴、民族崛起时代的中国平添了一道人文景观,其在全社会所引起的热烈反响昭示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回归。
范曾先生数十年精勤诗教,每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诗作,辄告以“不作苦寒艰涩语”,需“注意心灵之回馈”。不惟雕琢章句,更期煅铸心灵,此盖“温柔敦厚”之传统于人心世道之教化,吐纳“风骚”之辞采、秉承“雅颂”之遗意,正是大诗人范曾先生所以冀望于其学生之所在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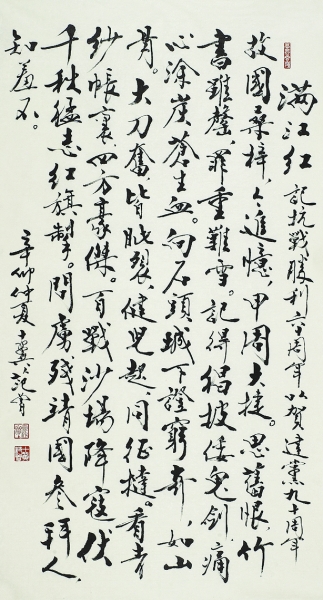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