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文学批评似乎总是一个尴尬的身份或职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听闻圈子里两位老师闹得不愉快,好像就是一个说另一个,当不了作家才写评论的。细想之下,这句话也顶多讥刺了批评家没才华这样的意思。如果是我,我不会在意的。我的才华你哪儿懂。李健吾在他的《咀华集》里,就集中写到过作家对批评家的攻讦,看得我哈哈大笑:本·琼生把批评家说做补锅的,弄出来的毛病比补的还要多,玻特勒(Butler)说做处决才智的法官和没有权利陪审的屠户;斯提耳(Steele)说做最蠢的生物;司威夫特(Swift)说做狗、鼠、黄蜂,最好也不过是学术界的雄蜂;沈司通(Shenstone)说做驴,自己咬够了葡萄,便教人来修剪;彭斯(Burns)说做名誉之路的打劫的强盗;司考特(Scott)幽默地反映着一般的情绪,说做毛毛虫。这些话可比讥刺没才华犀利多了。
批评者也应自我批评,没有谁具备免于批评的豁免权。我对自己的批评在于:目前还无法彻底摆脱名缰利索对我的威逼利诱;自己的学识见解、思想襟怀还需砥砺修炼;人生苦短,我到底是有志于纯理论的探索还是当代批评的经营?也许到最后,我也还没想明白,攸忽人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哀怨的,一代代学人、知识分子,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作家、批评家本质上都不过是要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证明人生一世的价值或意义。假如有的话。历来对卡夫卡的阐释已经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然而在这如海的资料堆里,同为犹太人的本雅明和汉娜·阿伦特的见解最为贴心:本雅明说,只是为了那些无望者,我们才被赋予希望。理解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别的诸多条件外,必须直接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失败者。失败的原因是多样的,我们不禁想说,一旦他明白将以失败告终,凡事他做来都一路顺风,恰似在梦境。每每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便隐隐感到先贤前哲早已在前面为我们蹚出了一条路。寂寞、孤独都是可以化约的代价,只管往下走,也许会遇见同路人,也许也会逐渐走散,但无限延宕的目的地就在前方。
虽然自忖写的每一篇批评都力图真诚、客观,但不给作者分辩的机会、武断地断定我所认为的,就算真诚、客观,对作者而言,完全公平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家不断失去作家的心,一方面也许是没有人愿意听否定性意见,另一个原因难道不是批评家根本不懂作家?可是为什么作家很少替自己辩护?为什么在中国,一种有益的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动总是这么缺乏?要不是相互谩骂,就是表扬集团在作战,而作战的对象为虚无——没有人关心你们自吹自擂相互吹捧。作为批评家的苏珊·桑塔格,自毁长城,提出过“新感性”“感觉美学”,倡议对当代艺术应该去体验而不是解释。有没有人敢说她没才华?《在美国》《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火山情人》等代表作证明着她有没有才华。作为一个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体双面人,桑塔格是如何做到的?写作与批评,有什么必要壁垒森严?人为设置各种球场和游戏规则,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能量、技艺狭獈而已。对专业读者来说,阅读是一种素质底色,她正是在这种阅读锻炼中,变得越来越专业。“而你作为一个作家所积累的东西,则大部分是不明朗和焦虑”(桑塔格)。作为批评家,应充分理解作家的不明朗和焦虑;作为作家,要提供尽可能高的智慧产品,说到底,尤其小说,考验的是作家的叙述智慧而非别的。
对一个批评者来说,最幸福的莫过于,你在故纸堆里发现在灰尘中发光的语言和见解。引为知心之谈,有会心之笑。偶然读到吴小如一段话:近人侈谈欣赏——欣赏之道,支离破碎其病小,隔靴搔痒其病大,笼统言之其病小,矫揉造作其病大。支离破碎是古来考据家旧病,隔靴搔痒则是近来洋状元之新病。旧病是殷鉴,可以一望而改,新病却是传染症候,尽你防得严,却当不得来势凶猛。往往老鸦落在猪身上,见得人家黑,见不得自己黑,便一误再误,不可收拾,欲救其弊而疗其疾,必得读书破万卷。愈读得通乃愈见其方案之灵也。这些见解经住了时间的质疑和批评,穿越到今天,你仍然不能不为他的判断、机智而叹服。
我还有一点需要检讨的是,诚如一百多年前,尼采以疯癲般的夺人心魄的魅力,说出的系列讽刺时代和德国的话,其中有一句:……一旦加入到当代艺术气喘吁吁、神经兮兮的赛跑中去,他们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何尝不是一句至痛的鞭策?我忙于各种赶稿、课题、各种赶场子研讨会……我还能沉着、勇敢吗?
也许我已丧失沉着和勇敢,然而我仍然对批评充满想象和期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要为国民群体创造民族的历史形象和故事;在这其中,没有批评的介入,怎么能想象有创新呢。王尔德说,创造的倾向是重复自己,每一新派的跃起,每一艺术应手的型态,我们全得之于批评的本能。可以说,正是批评的本能,在撬动人类人文学的不断前行。
(作者简介:何英,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曾作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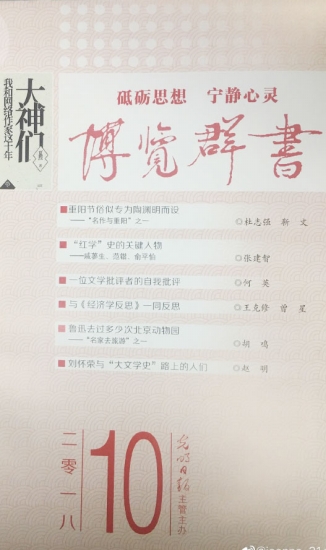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